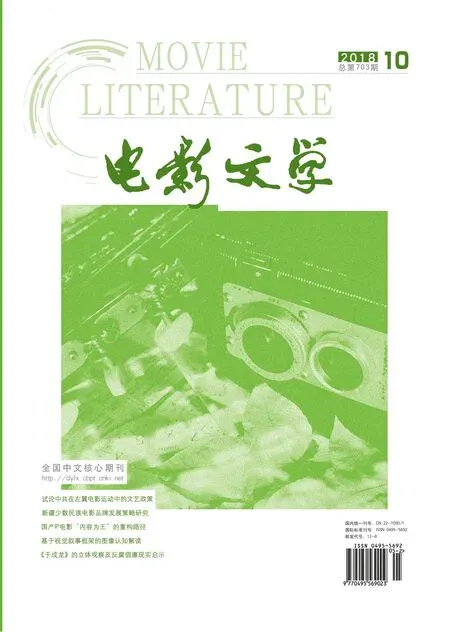英美名著改編電影中的文學精神重構
叢 釗
(吉林醫藥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毫無疑問,電影和文學具有密切、天然的親緣關系,大量電影來自文學名著。而由于英語強勢地位帶來的廣泛受眾以及好萊塢電影產業成熟度的原因,英美名著的影像化可以說是最為頻繁的。
而名著之所以成為名著,很大程度上,除了文本本身的寫作方式、母題選擇以及場景、空間的構造和人物形象令人稱道外,還在于其往往具有一種歧義性和現代性。內容具有開放性的作品在問世后,依然長期得到人們的解讀,不同時代的人均可從中挖掘出對其有意義的文學精神,這是一部作品走向流傳久遠的名著的條件之一。而這種解讀也包括跨媒體的呈現。在電影這門年輕藝術對名著進行改編時,原作的穩態就必須被打破,其文學精神也會在不同程度上被重構。
一、對文本的整合
文學作品的文學精神是被負載在文本之上的。電影在傳遞或改造文學精神的過程中,勢必會整合文本本身。這種整合包括對敘事主干、主要人物的保留,對部分核心情節的突出,對非核心情節的化零為整或刪削等。甚至還有部分電影會直接改動名著的結局。如在亨利·金的《乞力馬扎羅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1952)里,哈里和海倫有情人終成眷屬,同時原著的夢幻感也被現實感所取代。這就往往會招致原作者不滿。海明威就曾公開表示這不是自己寫的《乞力馬扎羅的雪》。正如王安憶曾經表示的:“電影是非常糟糕的東西,電影給我們造成了最淺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電影,使我們對這些名著的印象被電影留下來的印象所替代,而電影告訴我們的通常是一個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電影為了貼合廣大觀眾的心理,往往不得不犧牲文學精神中沉重、壓抑或是晦澀難懂的一面,以讓觀眾能夠充分理解并得到愉悅。前述的《乞力馬扎羅的雪》的大團圓結局就是一例。但這也就意味著,如果電影人能夠放棄淺薄的表達,或是原著的精神表述本身就是易懂、樂觀的,那么在對文本的整合上,電影人就可以不必讓原著的文學精神被商業規則吞噬,讓原著給受眾的印象和電影給觀眾的印象,出現最大限度的重合。以改編自J. K. 羅琳著名魔幻作品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系列電影為例,電影全部保留了原著中的主線情節梗概,如伏地魔借助奇洛教授和密室與哈利展開較量,小天狼星和哈利從誤會到相認,再到因為死亡而分別,伏地魔在三強爭霸賽后復活等,并且使結局嚴格地向著原著的設定走去:伏地魔和哈利展開了最后的對決,就法力而言,哈利無疑不是伏地魔的對手,在鄧布利多的預言中,哈利作為伏地魔的最后一個魂器,也應該與伏地魔同歸于盡,但是最終哈利卻憑借著最簡單的“除你武器”咒語(這個咒語在此也代表了最簡單的,人人都可以學會的愛)殺死了伏地魔而自己安然無恙,整個魔法界回歸了平靜。羅琳在原著中傳遞出來的文學精神是簡單且富有普適意義的,除了奇幻的想象外,羅琳最強調的便是愛和勇氣。哈利雖然法力弱小,卻是愛和勇氣的化身,并且受到眾多愛他的人的庇佑,而伏地魔則喪失人性,濫殺無辜。最后正義是必然會戰勝邪惡的。同樣是奇幻文學改編電影的《指環王》(The
Lord
of
Rings
)系列也同樣如此。與之類似的還有如李安的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Billy
Lynn
’s
Long
Halftime
Walk
,2016),電影改編自本·方丹的同名小說。李安準確地從原著紛繁的文學精神,如反戰、社會貧富分化等中,抓住了最關鍵的一點,即人與人之間交流的無力。電影從比利的視角展開,但是對于其他人來說,每一個人都在這場“中場戰事”中有一個比利的故事,人們只愿意接受一個符合他們利益和期許的比利,來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在中場戰事中撕裂著比利,讓他備感失望,這才是比利最終選擇離開美國和家人回歸九死一生的戰場的根本原因。因為這種對原著精神的理解,李安也保留了原著中的匆匆出場,又沒有返場,本來不適合影視化(因為這種驚鴻一瞥容易對觀眾造成注意力上的分散)的人物,如頁巖氣老板等。二、對人文要素的重組
文學名著之所以能夠給予讀者長期的精神支撐,正是在于其中的人文主義色彩。電影繼承名著對人情感、欲望和意志等抽象概念的關注的同時,往往會對承載這些抽象概念的具象要素進行重組。
例如,在巴茲·魯赫曼的《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Juliet
,1996)中,電影改編自英國文豪威廉·莎士比亞的同名戲劇,但是卻對原著進行了后現代式的改編。不僅愛情悲劇的背景從中世紀的歐洲搬到了一個虛擬的現代時空,且有意保留了全部的古英語對白。而在此之前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11次電影改編中,莎翁的語言都是因為對于觀眾而言不夠自然和生活化被改動了的。這樣一來,電影就實現了對原著的解構。莎翁原來設置了諸多人文要素,如與中世紀緊密相連的貴族生活,維羅納的景物包括特有的建筑、墳墓等疑難意象,被進行了置換,電影中充斥著屬于當代的槍林彈雨、汽車等。人物說著古老的吟游詩人式的臺詞,配合以現代化大都會的環境和道具,畫面更是有著一種華麗怪誕的MV風格,這種重組是令人感到怪異、陌生的,這也是這一版《羅密歐與朱麗葉》毀譽參半的原因之一。但值得一提的是,新的視覺上的觀感和舊的聽覺上的信息接收之間,形成了一種矛盾,而這種矛盾卻是積極而有利的。電影的改編和觀眾的心理預期出現了偏差,而在適應了這種偏差之后,觀眾能夠得到一種信息,電影其實是在用另一種方式來強調莎翁原著的主題,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悲劇宿命并沒有因為被置于另一個環境中而發生改變。陳舊的意識、野蠻的倫理觀念,以及尖銳的社會矛盾,并不僅僅存在于中世紀,以真摯的愛情為代表的人文思想也是長存的,羅密歐和朱麗葉這樣的性情中人在另一個世界中也會收獲愛,但也會因愛而被傷害。這樣一來,原著的人文精神不僅被保留了下來,而且還在其他的“變”中,以“不變”的姿態被凸顯出來。與之類似的還有安德里亞·阿諾德根據艾米麗·勃朗特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
,2011)。相較于原著,電影最直觀的改動就是希斯克利夫從吉卜賽人變成了黑人。這樣一來,希斯克利夫在童年時期受到的歧視就帶有了種族主義的沉重感。原著中呼嘯山莊泥濘污濁、暴風呼嘯、烏云蔽日等地理環境元素被保留了下來,以此來襯托希斯克利夫內心深處的壓抑和憤怒。另外,電影又增加了其他元素。當希斯克利夫在大雨中離開呼嘯山莊后,雨中出現了如蜥蜴、牛羊、鷹等五花八門的,脫離了現實的動物。這些看似不合理的元素實質是在暗示希斯克利夫內心深處的原始欲望,正是他的野性促使他愛上凱瑟琳;同時,這些動物也暗示了希斯克利夫以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生存的思維。電影盡管被詬病為改編得“面目全非”,但勃朗特寄寓在小說中的人文要素,如肯定野性和頑強,緊張、離奇的情緒和氛圍等,都被保留了下來。三、時代精神下的重新詮釋
時代精神與文學精神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名著經歷了時間的檢驗和篩選,而電影則是現時的創作,這也就導致二者往往處于不同的時代,電影往往會賦予原著新的時代精神,這也就造成了文學精神的變動。
霍桑的《紅字》被認為是奠定美國文學基礎的作品之一。早在默片時代,《紅字》就六次被搬上大銀幕。而其中最為著名的莫過于維克多·舍斯特勒姆執導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1926)。盡管人們普遍認為1926年版電影是最忠實于霍桑原著的,但是其實電影還是在不動聲色間悄然重新詮釋了原著的“規訓和懲罰”的文學精神。電影先是增加了早期北美殖民地嚴格的宗教氛圍,用海斯特一個個違反安息日規定,但是完全符合當代人認知的舉動,如追逐小鳥,把衣服晾曬在外面等,來凸顯海斯特是一個活潑的、不受刻板教規束縛的人。而丁梅斯代爾之所以會和海斯特相愛,正是因為對她充滿同情,這也就使得兩人被認定是“通奸”的愛情悲劇更為合理且能打動觀眾。與原著中理應受到懲罰的海斯特不同,電影中的海斯特無疑更為無辜,并且是宗教的犧牲品。這對于當時正處于變革期,宗教的力量越來越微弱,舊道德開始退場的美國社會,無疑是更適應時代的。而人們也認為,海斯特所代表的是新女性、新道德,而這種革新的力量,正是美國精神的一部分。電影表面上是在講述一個愛情悲劇故事,實際上是為美國人提供了一種屬于新時代的體驗視野。又如菲利普·馬丁執導的《東方快車謀殺案》(Poirot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2010),電影改編自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系列”同名小說之一。在此之前,20世紀70年代這部小說已經有了一次極為精彩的,得到克里斯蒂本人首肯的改編。而馬丁的電影則加入了更多關于正義與法律之間關系的內容,如波洛最后無法揭露真相時的落寞,他和德本漢小姐之間的討論等。與推理題材的電影中,偵探往往被塑造為洞悉真相、懲治罪惡的,極具光芒神采的角色不同,這一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增加了波洛乘坐東方快車的前因,并且處處渲染波洛的疲憊和無力,波洛最后沒有說出真相,與其說是主觀認同兇手的做法,倒不如說是一種不得已的、令人失望的妥協。整部電影也氣氛沉重,人人心事重重。在觀眾基本已知道真兇是誰以及兇手所使用的瞞天過海的詭計后,電影的改編或是只能加入與詭計有關的枝蔓(如中日韓三國對東野圭吾《嫌疑人X的獻身》的改編),或是加入有關主題的討論。馬丁的這版電影便選擇了后者。阿加莎在原著中,高舉的是維護正義的精神。美國富商之所以要死,正是因為他踐踏了正義,而兇手們只是在執行法律未能執行的審判和死刑執行。電影保留了這種堅持正義的文學精神,但是對其加入了當代的,在法律逐漸完善、法治精神逐漸深入人心時的思考。電影中的波洛認為,兇手們以維護正義之名而踐踏法律,這樣的正義是被打折扣的,私刑復仇的方式永遠不能指向正義和公允。最終沒有能說出真相,這對于波洛而言是一次極大的挫折。加上登車前處理的軍隊的案件,偵探在電影中是一個被沉重打擊的角色,這可以說是一次相當大膽而成功的重構。文學作品在被改編為電影的過程中,勢必會被電影主創做“加減法”。觀眾盡管得到的依然是“那一個”故事,但是從中獲得的精神體驗、思想啟迪、感官愉悅,乃至情感刺激,卻往往已經不是原著作者主觀上想給予讀者的“那一個”。這種變化正是電影對文學精神的一種重構。電影人為了盡可能地使故事獲得觀眾的理解和認同感,往往會根據時代背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以及目標觀眾群的審美偏好,整合文本,重組要素,甚至是大刀闊斧地對文本進行重新詮釋,從而使電影具有新一層意義,也使得觀眾在有可能已經對敘事有一定了解的情況下,產生新的情感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