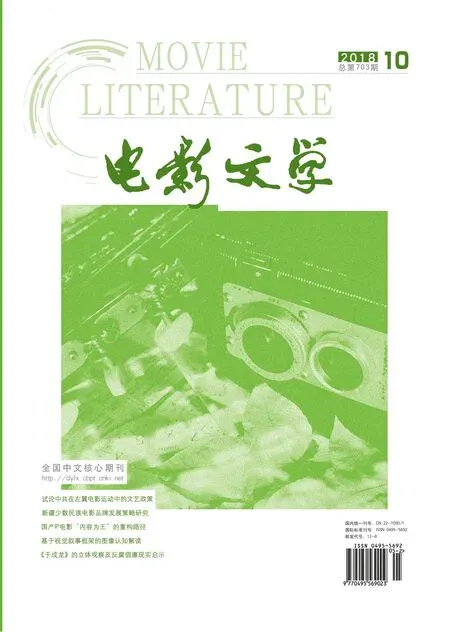當代老年題材電影《冬》的孤獨敘事
莫珊珊
(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廣西 桂林 541001)
2016年7月我國公映了一部青年導演邢健的電影作品《冬》(又名《七天》),影片展出和公映后,在觀眾中出現了較大反響,該片被認為是中國新一代青年導演的佳作,具有較強的藝術探索性。影片全程以黑白的色調和“失語”的形式,講述了一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呈現出一定的實驗精神,在中國新時期以來的老年題材電影中顯得尤為特別,是一部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藝術電影。
一、孤獨與對抗孤獨:對老年個體精神生態的關注
關于電影 《冬》的創作緣起,導演邢健在2016年7月16日南京線上交流時談到,是來自“個人童年內心狀態的寫照”,特別是來自對姥姥、爺爺、奶奶老年生活的感悟:姥姥孀居多年,平時靠抽煙打發時間,有人去看望她時就不停說話;爺爺平時身體比較硬朗,但是在奶奶去世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堅持不下去了,整個人的精神就像被掏空一樣。長輩的老年生活給導演很大的感悟,影片通過主人公七天里發生的故事借以表達老年人的精神孤獨主題。
在惡劣寒冬里的長白山下,住著一位獨來獨往的老人,影片開頭用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紀實化地呈現了老人生活的孤獨狀態:寒風飛雪中,老人在冰窟窿旁獨自垂釣,他用厚實的棉帽包裹著魚缸,自己在寒雪中被凍得瑟瑟發抖;回到家老人簡單應付了晚餐,認真鋪好土炕上的兩床褥子,在其中一個上躺下,一夜未熄燈;吃早飯時,擺好兩套碗筷,自己用一套;第二晚睡覺間,忽然焦躁地起身將床頭的魚缸砸破。這是一位空巢老人,食物的簡單和習慣性失眠表明了他生活質量的低下。他的生活完全是個人化的封閉生活,沒有社會群體活動,處于社會交際和精神交流的隔離狀態,那些活動只有在照片中老人時才能看到。此外,沒有報刊、廣播等媒介,無法獲得對外信息,沒有串門、鄰里閑聊等交流渠道,除了釣魚沒有其他精神舒緩方式。影片中從極寒的冷、料峭的風聲、肆意的雪,到屋內的昏暗與老人的形單影只,凸顯出獨居老人的孤獨,表現出從天冷到心冷的鉆心感,具有一種濃濃的壓抑沉悶的氛圍。影片開頭的場景事無巨細地交代了老人生活的各個環節,在近乎無事的日常流程間,透視出老人生活的機械循環和悲涼。
老人的日常生活是孤獨的,但是在老人生活的常態間又隱藏著他對抗孤獨的一面,從整部影片來看老人的孤獨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狀態:由于伴侶的離世或其他原因造成了他的孤獨,但他又不甘于孤獨,他試圖與孤獨抗衡,希望能獲得繼續生活下去的意義;但他對抗孤獨的努力,有時也會被現實生活的循環所消解,于是老人不斷在孤獨與反孤獨之間游走,對抗著生活的無意義。老人的孤獨是由伴侶的缺失而帶來的,他喪失了伴侶,于是他也始終在尋找伴侶,試圖和某個對象建立起伴侶關系。影片有很多鏡頭聚焦于照片中的一位年輕女人,她應該是老人的妻子或愛人,她的缺席是老人孤獨的源頭,老人在睡覺、進門出門、吃飯等任何時候無不望向她,以期獲得某種安慰。影片中出場的“在場”角色,從最開始的魚,到后來的鳥和孩子,全都承載著老人的伴侶期待,他希望在和他們的關系互動中能獲得精神慰藉,魚、鳥、小孩這些角色對老人都具有慰藉者、拯救者的意義。
老人對待生活的態度也是復雜的,他按部就班地生活,該吃飯就吃飯,該睡覺就睡覺,該釣魚就釣魚,生活雖簡單機械但不茍且,老人甚至在這些生活環節有著極強的“儀式感”,非常認真、虔誠、莊嚴:每晚睡覺前都悉心鋪好兩床床褥,枕頭要拍松,睡醒后再整齊放好;吃飯時擺上兩副碗筷;灶膛里的火持續燃著;屋里收拾得有條不紊,屋前屋后沒有雜亂的堆放。老人對待生活是認真的而不是消極的,在失去伴侶的情況下,在情感孤苦的精神生態危機下,他始終在與生活和時間的機械循環抗爭,試圖找尋活著的意義,讓自己繼續活下去。影片中有一個鏡頭值得注意,老人在風雪中釣魚又放魚,在外人看來是一個奇怪的舉動,有幾個躲在不遠處的孩子在偷偷看著,他們好像不敢也不愿意接近老人,孩子的態度可以解讀成其他人對他的態度,也許老人的奇怪舉動會讓旁人都覺得他有些神經質,但是這個鏡頭恰恰說明,老人試圖以個人化的行為來對抗和消解孤獨,他不在乎外界的看法,也不乞憐外界的安慰幫助,他只需一個人冷漠、執拗而又認真地生活,具有“西西弗斯”般孤獨英雄的色彩。
二、“伴侶”的角色建構及意義
魚、鳥、小孩對老人的拯救意義呈現出對比和遞進關系。魚是老人的生活之伴、消遣之伴。影片最初陪伴老人的是魚,影片里老人在風雪中釣魚的場景很多,釣魚是老人打發時間的最重要途徑。老人望向魚時失神的眼神,將魚釣而放、放而釣的舉動,失眠時忽而起身一把將魚缸打碎,都說明魚對于老人而言僅僅是“在而不全伴”,對老人來說魚必須有,但是具體是哪一條無關緊要,只要有一條能陪伴他就可以了,老人對魚并未傾注太多的情感。
鳥對老人來說,更像家人之伴。鳥和孩子同時出現,但是他們進入老人的精神世界卻不一致,鳥是第二個進入老人生活的。老人看到在雪地里已經奄奄一息的鳥,最初是冷漠離開,后來在回家路上他因體力不支倒在雪里,對鳥產生了憐憫之心,于是將鳥救回了家。鳥在生活中慢慢代替了魚,之前屬于魚的一些特殊待遇轉移到了鳥的身上:之前陪伴在床頭的是魚,后來老人將鳥放在床上;之前老人用帽子為魚遮擋嚴寒,后來帽子成為鳥溫暖的窩;之前老人藏在懷里喂魚的食物,后來老人喂給了鳥。鳥飛走后,老人在山林間急切尋找,當他回到家看到屋檐上搭好的鳥窩,老人的眼神里閃過震驚觸動,他意識到鳥已經把他的家當成了家,接著老人做了一件事情,他將魚活生生切碎了喂給鳥吃。鳥給老人叼回一條蟲子,把鳥窩搬進老人家里,老人和鳥之間像家庭成員一般互動,鳥讓老人感覺到久違的溫暖。鳥相對于魚來說,不只是老人的消遣之伴,而更似家人之伴。
孩子是老人的情之伴、心之伴。與鳥的敘事同時交叉進行的是小孩的故事。孩子之于鳥,和鳥之于魚有著同樣的對比、遞進關系。老人和小孩之間的相處,經歷了從矛盾、對立、消融到和解的過程。老人夜里再次外出尋找失蹤的鳥未果,拖著疲憊的身軀癱倒在床上,孩子到床前為他掃去身上浮雪,繼而又拿食物的舉動融化了老人的心,孩子代替了鳥進入老人的生活。在第六天,老人的生活里第一次出現了爽朗的笑聲,兩人像祖孫一樣親密無間。老人看到孩子對土豆無法下咽,將鳥殺了烤給孩子吃。孩子離開老人的家后,他眼巴巴地在門口守望著,生怕錯過孩子的回來。然而他因為太困靠在屋里睡著,竟然成為永遠的遺憾,老人去追趕孩子時,孩子已經掉到了他平時釣魚的冰窟窿之下。孩子相對于魚和鳥,不止于消遣和陪伴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孩子徹底打開了老人冰封的心,給他帶來了切實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孩子與老人之間已如同親人一般,老人享受著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他壓抑許久的情感需求終于得以補償。
愛人是老人的靈魂之伴、精神之伴。魚、鳥、孩子都是現實在場的,愛人在現實生活中是缺席的,但是她始終是老人的精神寄托,是老人最終的精神歸宿。當孩子遇難后,無助的老人最后一次凝視著照片中的她,鋪好床褥然后默默躺下,臉朝向她的位置。恍惚間她也安然地躺在老人身邊,在她面前老人像一個受盡生活委屈和情感折磨的孩子,老人在她溫柔的陪伴中永遠睡去。影片中老人與魚、鳥、孩子之間的互動,都是他為了化解對愛人的思念,為了對抗孤獨而做出的情感邁步,在所有伴侶都消逝之后,老人選擇皈依在愛人身邊,將自己從現實的孤獨中解脫出來,將靈魂與她永遠一齊安放。
三、紀實化和寓言化融合的孤獨視聽影像
《冬》在影片風格上具有紀實化和寓言化的雙重特征。影片較嚴格地按照七天的線性時間順序推進,具有紀實化特征。影片采用了大量的長鏡頭,克制冷靜地展示出老人日常生活的真實和瑣碎,還原了生活的殘酷與莊嚴。同時影片采用了較多的近景和特寫鏡頭,真實地表現了老人的孤獨情緒。影片在聲音方面,沒有任何人物對白,全程處于一種交流斷裂狀態,強化了孤獨的意味。
寓言化,是指在文藝性作品中創作者在外在故事之下蘊藏著寄托之意,表達創作者的某種認識和感受。電影《冬》具有很強的寓言化特征,在老人找尋伴侶的七天的故事中,老人—魚,老人—鳥,老人—孩子,老人—愛人之間的聯系暗含著地、天、人、心的關系隱喻,又充滿了輪回的內涵,呈現出“試探—替代—突圍—消解”的對抗精神孤獨的內在結構,是一部空巢老人精神危機與突圍的寓言。老人在魚、鳥、孩子的情感上多次發生轉移,從一個伴侶轉到另一個伴侶,老人的情緒從開始的麻木失神,到與鳥相處時的溫熱,再到與孩子相處時的情感狂歡,到最后絕望崩潰,他的情緒變化是正常且合理的。影片通過對老年人精神狀態的展現,表達了對現實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憂慮,具有較濃的人文情懷和理性意識。
由于寓言蘊意的內在性和暗示性,在視聽語言上影片通過一些虛擬性和意象化的情節呈現影片內涵,使影片具有詩意化、夢幻化、超現實的特征。在畫面語言上,全片充滿了中國傳統水墨山水畫之美,構圖簡練卻不空洞,虛實穿插,具有大量的藝術留白,表現出對中國傳統藝術品格的繼承,讓人品味不盡。老人大雪中釣魚的畫面屢屢出現,以一種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悠遠意境詮釋出老人的精神寂寥及對伴侶的渴望。影片中有一些超現實的情節,例如老人假想著與小孩重逢擁抱,表達老人的苦苦思念;小孩遇難后在雪地里漸行漸遠,最后消逝在茫茫大雪中,表現老人的心痛自責;老人最后躺在床上,愛人為他拭去淚水,表現老人對愛人的依戀;從被子里鉆出飛向天際的鳥,喻示著老人的離世,這些超現實情節拓展了影片的情感含量,同時通過非現實場景的營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現實悲劇性,轉化成一種詩意的美。在聲音語言上,雖然全片沒有人物對白,但是屋外的風雪聲、鳥叫聲、老人的呼吸聲、老人極端情緒下的笑聲和哭聲,密切貼合了場景,特別是影片中的背景音樂配合著老人的情緒消長,例如老人失眠時琴聲沉悶頓粗,后節奏逐漸加快,像心煩狀態下想睡又無法入睡的紊亂心理;老人想象和孩子雪中相擁時,音樂舒緩又充滿憐愛,是老人情感思念的高潮;當老人發現孩子遇難時,琴聲高亢嘶啞,似有萬般情緒堵在胸口要噴涌而出,表現老人的崩潰絕望。
四、結 語
電影《冬》聚焦當代老年人的孤獨問題,展現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態,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電影美學上,影片以紀實化和寓言化的視聽語言,既傳達出現實的深沉力度,同時又試圖建立起影片的藝術文化品格,擴大了影片的審美藝術空間,帶有一定的實驗探索精神。在當今電影市場化和商業化浪潮下,《冬》堅持著藝術的追求,不規避社會現實,表達著時代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新一代青年導演對當下中國電影發展現實中表達困境的突圍,是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中一股難能可貴的探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