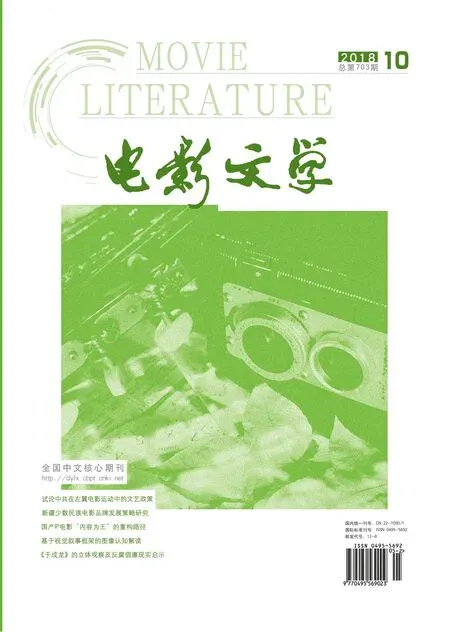中國古代哲學視野下的《大魚海棠》
申艷霞
(西安培華學院 人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5)
梁旋、張春的《大魚海棠》(2016)以動畫的方式為觀眾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意義世界。人們普遍已經注意到了電影在視覺表現上大量運用的東方民俗文化細節,電影中無論是人物細膩的造型設計,抑或是精致的場景制作等,都具有濃郁的中式美學意味。同時,《大魚海棠》留給觀眾的并不僅僅是“意象”,還有屬于華夏文化的“意向”。可以說,《大魚海棠》深受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整個故事,便是主創立足于現代,對中國古代哲學思維的一種理解和闡釋。
一、“齊物”觀
《大魚海棠》中的世界觀與莊子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如鯤的名字來源于《莊子·逍遙游》中的:“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莊子在《逍遙游》《大宗師》等著作中提出了“齊物”的理論,他認為,人并不是獨立于客觀世界之外的,萬物都是由“氣”組成的,它們應該是一體、平等的。在《大魚海棠》中,椿等人的遭際不斷地印證著莊子的“齊物”觀。
首先,《大魚海棠》中人、“其他人”和動植物等之間的相互轉化,是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憚”觀點的體現。電影中所有的人其實都是一條大魚,椿等“其他人”中的少年男女在成人時會化身為魚,去觀察人類世界,而每個人死后,好人會變成一條魚,靈魂被靈婆收起來保管。鯤在死后就變成了一只長著獨角的海豚,椿花費了六個小時才在靈婆的如升樓那里找到了它。而壞人則會變為老鼠,靈魂由鼠婆掌管。椿的奶奶主管百鳥,死后化身為鳳凰,爺爺丿有著治愈萬物的能力,死后化身為海棠樹。椿在被復活之后,失去了“其他人”的身份,成為一個普通人。甚至一個人的年輕與年老、美貌與丑陋之間也是可以轉化的,如衰朽的鼠婆后來拿著鯤的小笛子回到人間后,變為一個年輕的美女等。
其次,“齊物”觀不僅宣告了人和人、人和外物之間互相轉化的可能,也以一種“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的超然觀念模糊了生與死之間的界限,生死都只不過是一種自然的循環往復的過程。這也體現在了《大魚海棠》中。正如爺爺丿承認自己大限已到,在椿說自己舍不得爺爺的時候,爺爺說生死有道,對我們來說,死是永生之門。在爺爺預感自己即將死去時,他對著屋外的鳳凰微笑著平靜地說:“老伴兒,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嗎?”在爺爺死后,鳳凰依偎在了爺爺變成的海棠樹上,死亡只是爺爺奶奶換了一種相聚的方式。在這種坦然面對生死的哲學觀下,爺爺、椿等人才能夠并不將死作為一種終極痛苦,不讓自己成為物質世界的奴隸。如升樓門前的對聯“是色是空,蓮海慈航游六度。不生不滅,香臺慧鏡啟三明”也是這種生死觀的體現。
最后,《大魚海棠》暗示了,也只有在“齊物”觀的影響下,人們才能進入“逍遙游”的境地。“逍遙游”是莊子哲學中對于極為愉悅、美妙的自由之境的藝術性夸張。莊子之所以提出這一概念,是因為他承認,在現實世界中,矛盾沖突是普遍存在的,人在生存中也勢必要面臨各種異己力量的局限。如《大魚海棠》中椿就被告知家里是不能養魚的,她的鯤還一度被母親丟棄,而要養大鯤,她還要遭遇比這更艱難、無奈的境地。而莊子的哲學認為,盡管如此,人依然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即在克服物質生命的有限后,獲得精神生命的無窮,對與物不斷發生阻礙、摩擦關系的現象界進行超越,進入到與“道”發生和諧往復關系的本體界中,這也正是人的崇高之處。從這一點而言,中國先秦時就出現的這種哲學思想與后來康德所提出的人的兩重性是有一定的契合之處的。康德認為,人性是雙重存在的,人一為“現象的人”,一為“本體的人”,前者是服從、受制于客觀世界,自由對于現象的人是無從談起的,但是本體的人卻是擁有自由意志的,即“超脫了整個自然的機械作用的自由和獨立性,而這種自由與獨立性同時還被看作是存在者委身于特殊的、即由他自己的理性所給予的純粹實踐法則的能力,于是屬于感覺世界的個人在同時屬于理智世界的情況下,委質于他自己的人格。在《大魚海棠》中,椿雖然屬于有別于凡人的“其他人”,但是還并不是一個自由的人,她在化身為紅海豚后被漁網困住就是一個明顯的束縛象征。而在她因為爺爺的鼓勵,以“大人者,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舉世譽之而不加勸”的態度留著鯤,經歷了一系列困難,洞見了生存的種種不易,也反思了自己的錯誤,終于決定放棄自己的生命來拯救整個村子里的人,然后再被湫復活以后,她以赤身裸體的形式和鯤一起回歸人間這一現實世界,此時的椿已不再對族人和鯤有所虧欠,也不必再受“其他人”世界的種種桎梏(如提防人類等),而是實現了在命運和感情上的自主,進入到了更加自由的境地,成為一個真正的“大人”。她撫養和保護鯤的過程,是她對自己的人生進行豐富和提升的過程。
二、“陰陽”觀
但是“齊物”觀的統一之下,中國古代哲學還注意到了事物的矛盾對立一面,這也就形成了“陰陽”觀。陰陽的理念最早出現于《易》,是古人對宇宙中某種自然規律的認識,后來也被比附于種種與對立統一相關的社會現象。正如金開誠指出的,傳統的“陰陽”觀包括了三重含義:“一是指陰陽兩種元氣,交媾而成萬物。二是指不同的物性,如向背、明暗、虛實、剛柔、正反、上下、動靜、凹凸,等等。三是指不同的事物,如天地、日月、男女、背腹等(以上指物),以及進退、得失、成敗、增減、生死、消長等(以上指事)。正因為陰陽的‘所指’很寬泛,所以便無處不在。”在《大魚海棠》中,人或事物之間這種陰陽對立關系也是普遍存在的。
兩位主人公椿和湫實際上就是春和秋的對立。正如電影中所引用的《莊子·逍遙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莊子認為,小年與大年是對立的,人們應該有“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判斷,同時,在“大年”中也同樣存在矛盾,如春與秋也是對立的。在電影中,椿繼承的是母親主宰海棠花生長的能力,而其他植物也可以在椿的法力之下被賦予生機。而湫的法力則與椿是有所區別的。在椿奔去渡口的風雨交加之夜,椿經過湫的窗下時湫正在催熟柿子樹,后來他為鯤起名字時,椿催生的花朵又在湫的法力下枯萎。湫代表了成熟與肅殺的秋天,在他死后,他也化身為一堆秋葉。電影中椿意味著對幸福和快樂的追求,椿也有著令人羨慕的完滿家庭,有爺爺奶奶以及疼愛她的父母樹和鳳;而湫則代表了絕對的痛苦,他的家庭只有奶奶作為水族長老,其職責為為“其他人”打開人間通道。湫不斷地為椿犧牲,而椿卻始終沒有接受湫的感情,意味著幸福和痛苦的關系是對立的,但是幸福往往又是建立在經歷過痛苦之上的。從矛盾對立的角度出發,觀眾就能夠理解為何椿自始至終深切地明白湫對她的愛,但是又不斷逃避這種感情,明確地告訴湫“我不屬于你的世界”。春天與秋天注定無法相遇,椿和湫只能分別在不同的世界中掌管萬物的運行,而鯤則是一個能穿越兩個世界的媒介,將椿從湫的身邊帶走,并在未來給予椿幸福。而湫只能承受痛苦,正如他在痛苦至極時說出的真心話:“你以為你接受的是誰的愛?你接受的是一個天神的愛!他將背叛所有的神靈去愛你!為你忍受一切痛苦!以此帶給你全部快樂!”為了忘記痛苦,湫拒絕了孟婆湯而選擇了酒,在醉酒之后,湫的情緒召喚出了狂暴的山洪和呼嘯的大風。也正是因為湫這種與痛苦和死亡息息相關的屬性,靈婆最終選擇讓湫來繼承自己的位置。而椿則因為與鯤的靈魂發生了聯結而可以離開這個世界。與之類似的,椿在完成個人對鯤的報恩,以及維系全村人的平安,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后,也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中,這同樣是陰陽觀的體現。
三、貴德尚群觀
《大魚海棠》的另外一個世界觀來源是《山海經》與《詩經》,電影中如祝融、赤松子等人物,海水淹沒世界,后土修補破裂的天空等,都可以在《山海經》和《詩經》中找到原型,而這使得動畫具有一種中國古代“貴德尚群”的哲學思維。
在《山海經》中,通過“帝”等人物,提出了“德性”的概念,推崇一種公正道義、仁義忠孝的社會秩序,而又是與儒家文化中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理念有一定的重合之處的。在電影中,先是鯤不顧危險跳入漩渦之中解救了被網纏住的椿,隨后椿甘愿付出壽命減半的代價換取鯤的復活,并且隨后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了養大鯤而忍受非議,在得知湫將鯤放入冰層后不顧自身安危跳入冰冷的水中;鯤在發現兩頭蛇有可能傷害椿和湫后,也從水中一躍而起,要與兩頭蛇展開搏斗;而湫則更是多次對椿以命換命,如先是勇斗兩頭蛇,差點被毒蛇咬死,后來更是為了復活椿而也用自己的性命和鼠婆做了交換,甘愿從此作為人間的風雨陪伴椿;爺爺丿則耗盡自己的法力和最后的生命救活了被毒蛇咬傷的湫,椿在看見廷牧等村民被自己連累以后,燃燒自己阻止洪水,已經死去化為海棠樹的爺爺也燃燒起來,祖孫二人化為巨大的從水里站起來的海棠樹,托起了被洪水淹沒的人們等,這些全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德性”。祝融和赤松子以及鳳等人雖然最終并沒有犧牲,但是在洪水來臨之際,他們也是不顧自己的性命去尋找廷牧,阻擋洪水,掩護他人搭起橋梁,等等。這些人所獲得的無上威嚴,并不是因為他們的法力,而是因為他們對他人性命充滿珍惜的道德實踐。同樣,鯤在化身為魚后,盡管擁有獨角,但是無論別人怎樣對待他,他從來都沒有將自己的角作為傷害他人的武器,在椿用死來拯救村民后,鯤明知村民恨極了自己,卻也依然徘徊在椿的身邊不愿意離去,因此,盡管這種“德性”是偏向社會倫理,輕個人意志的,但這里的鯤同樣表現出了一個個體生命善良、重生、報恩的自覺選擇。
如前所述,《大魚海棠》中的“齊物”觀使得人們并不畏懼死亡,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并不重視生命,并不流連于現世生活。相反,《大魚海棠》中的“其他人”也極其注重抵抗天災人禍,注重族群的延續,這反映的是《山海經》乃至中國古代典籍中人們的宗族血統情節與祖宗信仰。不斷挽救他人,甚至犧牲自己以保證集體利益的“德性”延續下來,就是一種“尚群”觀。椿等人生活的,根據福建土家圍樓構建的場所體現出的就是古代先民團結互助、尚群共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農業社會,這種尚群思維和祖先信仰對于社會的穩定和運行有著重要的作用。而“尚群”觀反過來又使得“德性”作為一種集體人格一脈相承,代代相傳。個體要生活在一個社會組織之內,就必須遵從其中的社會倫理,如忠孝仁義,有恩報恩等。
充滿中國古韻的《大魚海棠》在一個生機勃勃、絢麗多姿的奇幻世界的基礎上給觀眾講述了一個感人的故事。在人設、場景和世界觀乃至故事線索等方面,《大魚海棠》都取意于豐富玄奧,研究者代不乏人的中國古代哲學,使得電影擁有了令人深思的精神內涵,以及對觀眾思想持續的影響力,這無疑為國產動畫的發展指出了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