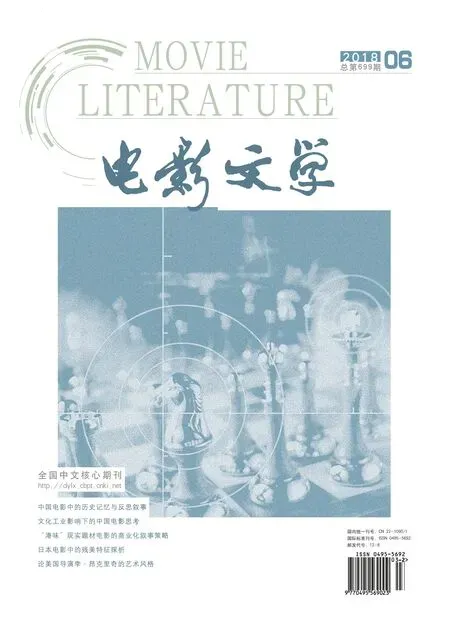當代國產電影的跨文化文本移植
王志麗
(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北京 100042)
電影是一門與跨文化交流關系密切的藝術。不僅各國電影人在創作上的合作日益復雜與密切,全球電影市場漸趨一體化,電影在創作上挖掘與改造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文本,如其他國家的小說、戲劇或民間傳說等,也成為一種常見的創作形態。
盡管中國有著源遠流長、內涵豐富的傳統文化,足夠為國產電影的創作提供文本支持,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電影人將目光對準其他國家的優秀文化資源。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就已經有了根據美國偵探小說《焦頭爛額》改編而成的《車中盜》(1920)。進入到當代以后,跨文化的文本更是成為國產電影重視的故事材料與表現手段,屢屢被移植到本土文化的語境之中。并且在文學之外,電視劇等新型藝術也成為移植文本的源頭。如陳正道的《101次求婚》(2013)就改編自1991年的同名經典日劇。這些移植都給予觀眾有別于欣賞原著的審美感受。
一、視聽元素——符號的文化自覺
電影中的文化表述是一個復雜、多元的過程,它包括對文化外在表征的介紹,如人物的服飾、飲食、語言、人物周圍的建筑等,也包括對深層的文化內核的展示,如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而視聽元素上的跨文化文本移植指的便是在視聽符號上,給予觀眾符合本土文化的大量外在表征,從本土文化中選取合適的,契合整個敘事文本的文化資源,體現出一種文化自覺。早在20世紀40年代吳永剛拍攝《中國白雪公主》(1940)時,電影中出身富裕家庭的白雪等女性身穿旗袍,而七個小矮人則頭戴氈帽,以當時中國礦工的形象來打扮,這便是一種文化符號上的移植。
當代國產電影中,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改編自英國文豪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作品《哈姆雷特》的馮小剛執導的《夜宴》(2006)。我們不難看到,在《夜宴》的整個故事中,雖然在無鸞和婉后、青女等人的關系,以及婉后的野心上做了些微調整,但是在故事的基本矛盾沖突乃至最后的結局上,《夜宴》和《哈姆雷特》的重合度是極高的。原著中,克勞迪斯殺死老哈姆雷特篡位,皇后喬特魯德被迫嫁給克勞迪斯,而奧菲利亞死去,其兄雷歐提斯在與哈姆雷特的決斗中雙雙身亡,皇后也意外身亡。這個故事梗概與《夜宴》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故事中王子被害的過程,暴露出人性在權力、情愛等影響下的弱點與陰暗面,這些也是跨越了時代和地域的,也都為《夜宴》所全部繼承。電影的亮點在于,在馮小剛和葉錦添等人的設計下,電影被加入了大量屬于中國文化的視聽文化符號。
這種視聽文化符號并不僅指的是電影出現了中國五代十國時期的宮殿、服飾等,而是具有“編碼—解碼”意義的,并不只是標明“在中國”的符號。如在視覺符號上,電影設計了極具禪意的伶人舞。無鸞在心愛的女子被父皇娶為皇后之后長久消沉,做出無心權力的姿態,沉迷于林泉之中。身穿白衣,戴著面具優柔緩慢舞蹈,就是無鸞的喜好。身穿白衣、肢體柔軟的伶人是與策馬前來刺殺王子的黑甲,體現了冰冷、生硬肢體語言的刺客形成鮮明對比的。二者的對比既在一開場就表現了無鸞和厲帝的勢不兩立,伶人如提線木偶的動作和面具也暗示了無鸞被動和隱忍的性格。這是對《莎士比亞》中的“戲中戲”的本土化改編。在聽覺符號上,電影設計了《越人歌》來體現青女對無鸞的寂寞絕望的感情。在電影中,無鸞將《越人歌》的典故解釋為王子泛舟,為他打槳的女子因為愛慕他而唱了這首歌。清純而癡情的青女對著《越人歌》的卷軸輕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眼淚掉了下來,最后青女也是在這首歌中戴著無鸞的面具死去。青女深知自己深愛的無鸞愛著的是婉后,而自己的哥哥則對自己有著不倫之戀,無鸞、自己和哥哥三個人都是愛而不得的。
與之類似的還有如臺灣導演王童的《假如我是真的》(1981)來源于沙葉新的同名舞臺劇,而舞臺劇則來源于俄國作家果戈里的《欽差大臣》。電影中主人公李小璋身上的舊軍衣、軍用挎包等,李小璋為了討好周明華的父親而用來裝假酒的茅臺瓶子等,都是已經脫離了《欽差大臣》語境的文化符號,同時也代表了一種權力話語,對于后來李小璋身份的混淆有著一定的伏筆作用。這類“實體形態,轉化成藝術作品中的視覺符號,經過一番符號的‘拆合重組’技術處理后,又疊加進更多的文化指涉”。
二、敘事——本土文化語境的建立
在跨文化的文本移植過程中,為了實現信息、情感傳遞的合理化,一個屬于本土的文化語境的建立是極有必要的。除非劇本的借鑒對象本身就是針對我國文化形態來進行創作的。如區丁平的《南京的基督》(1995)就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同名小說。原著中講述的是一個篤信基督的中國妓女,在江南秦淮河畔的青樓與一位日本作家岡川相愛,最終染上梅毒悲慘死去的故事。電影和原著之間的區別僅僅在于結局。電影不需要重新讓這個故事“中國化”,或是原著本身的文化個性并不明晰,如日本作家西村京太郎的小說《敦厚的詐騙犯》,幾乎全由對話組成,在被沈耀庭改編成《詐騙犯》(1993)后,又被韓國導演吳基賢拍成了《顧客是王》(2006)。在《詐騙犯》中,時代和地點被明確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上海,以使其中的詐騙犯、私家偵探等角色的出現更為合理,而《顧客是王》講述的則是一個當代的故事。可見有的文本本身具有較大的文化適應性。
而大部分的電影則是需要對故事進行重新書寫的。一旦單純為了貼合原著故事而語境無法完全自圓其說,整個故事都會讓觀眾排斥,出現移植的失敗。如早年李晨風根據托爾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改編而成的《春殘夢斷》(1955),就被詬病為整個故事在直到1974年才廢除一夫多妻制的香港不太可能發生,原著的劇情出現了“水土不服”。
而成功的典范則有徐靜蕾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2004),電影改編自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同名小說,這部電影與原著,以及與德裔法籍導演馬克斯·奧菲爾斯根據原著改編成的,屬于好萊塢作品的同名電影也有著明顯的情節上的改動。故事的主干被保留不變,少女愛上了鄰居作家,長大后的她曾和作家歡度了短暫的時光,懷上了作家的孩子,作家離開她后,為了撫養孩子她徹底以賣身為生,后來她又以風塵女子的身份與沒認出她的作家有過一次交往,女子在臨死之前寫信將自己的感情和孩子的身世告訴了作家。
首先,徐靜蕾在設計兩人的離合時,嵌入了20世紀中國風云變化的歷史。如少女正是因為自幼喜愛租住她家房子的作家,發奮讀書,才會考上了北平女子師范大學而重歸北平,繼續她對作家充滿愛意的窺視。而兩個人的第一次身體上的親密接觸來自于當時北平的學生因為日本侵華而上街游行示威,在混亂中作家救下了少女,得到了少女以身相報。而兩人的分離也正是因為七七事變發生,作家要去宛平做采訪,這在當時的背景下無疑是生死未卜的,而作家的形象也更為高大,少女寧可人生被毀也要生下孩子的行為也就更為合理。而此后作家與已經淪為交際花的女子相遇并且與她歡度一宵,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全民狂歡氛圍。
其次,電影在故事上做出了一定增刪,以使敘事更加流暢自然。如在小說中,13歲的女孩因為喜歡作家而親吻他的門把手,并偷藏他的雪茄煙頭,這在電影中被刪去,因為這些較為狂熱、露骨的行為不符合一位在北平被母親嚴格管教下成長起來的女孩的愛意萌動的表現。又如電影增加了一段情節,在兩人發生了關系后,作家要前去宛平幾天,少女拿起一個蘋果給作家咬了一口,自己咬著蘋果目送他離開。而后來這個蘋果干枯地被放在窗臺上,一是提醒觀眾作家已經走了不只幾天,二是暗示了兩人的愛情也像蘋果一樣很快變質枯萎了。
三、精神——本國文化意識與體系的代入
在電影的深層結構上,國產電影有必要在敘事中代入屬于本土的文化精神,如信仰體系、生活方式、價值觀等,讓其參與到地方形象或中式結構性社會背景的建設中來。
例如,許秦豪導演的《危險關系》改編自法國放蕩主義作家拉克洛的書信體同名小說,電影中的人物關系基本與原著相符。謝易梵(瓦爾蒙子爵)在情人莫婕妤(侯爵夫人梅特伊)的慫恿下,先是勾引了少女貝貝(塞西爾),隨后又去勾引少婦杜芬玉(杜薇夫人),結果卻發現自己愛上了杜芬玉,最終被貝貝的戀人殺死。在原有文本中,一個充滿了性、謊言、危險的故事是與法國大革命背景下舊貴族們腐敗、墮落的生活方式有關的。在電影中,故事背景被設置在20世紀30年代高度西化的上海,日軍槍炮日益迫近,而亂世中的人們則用奢華的生活來麻痹自己。原著中的王公貴族被改為花花公子與交際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更容易獲得觀眾的信服。而一種屬于中國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的批判意識,也在這些所謂的上流人士、名門淑媛追趕時髦、紙醉金迷的生活中傳遞了出來。主人公們用謊言和欺騙來維持自己的社交圈子,殊不知在亡國大難之下他們欺騙的都是自己。謝易梵最后在街頭被刺殺,就與日軍侵華有關。
又如李少紅的《血色清晨》(1990),整個故事顯然來自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小說《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只是故事背景轉移到了一個偏僻閉塞的村落,購買妻子的人則從在“金錢上游泳”的富翁巴亞多·圣·羅曼變為僅僅是一個村里萬元戶的張強國。這也就使得“殺人預告”從富翁的霸道變為村民的蒙昧。同樣是對愚昧無知的封建禮教和私刑仇殺行為進行批判,《血色清晨》中帶給觀眾的是一個全方位的中式落后文化體系,如城鄉差異下打工者的心態,大眾重男輕女的心態,違背女性意愿的換婚陋習,國人對“面子”的畸形重視,以及官僚制度下計劃生育政策的濫用,村長在村里仗勢欺人的行為,以及村民們普遍淡泊的法制觀念等,這些無不讓觀眾觸目驚心。可以說,李少紅在《血色清晨》中,體現出了對于中國和拉美社會文化差異的精準把握。
綜上所述,當代國產電影繼承了早年國產電影對跨文化傳播的重視,在將異質文化文本引入自己的創作中來時,完成了復雜而卓有成效的移植過程。這種移植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上,分別是直觀元素上視聽符號上的文化自覺,在敘事上建立適應本土文化語境的語境,以及在電影的深層結構上,提供給觀眾一個屬于本土的文化體系、道德價值標準等,促進了優質文化文本的傳播。電影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有著跨文化傳播需要的動態系統,隨著媒介生態環境以及電影在傳播渠道上的日益完好,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的交流勢必日益密切,這種跨文化文本移植還將繼續出現在國產電影以及外國電影之中,如馬丁·斯科塞斯攬獲第79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的《無間道風云》(The
Departed
,2006)便是對我國香港電影《無間道》(2002)的一次移植。可以說,這是中國電影對全球多元文化格局的一種有益的參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