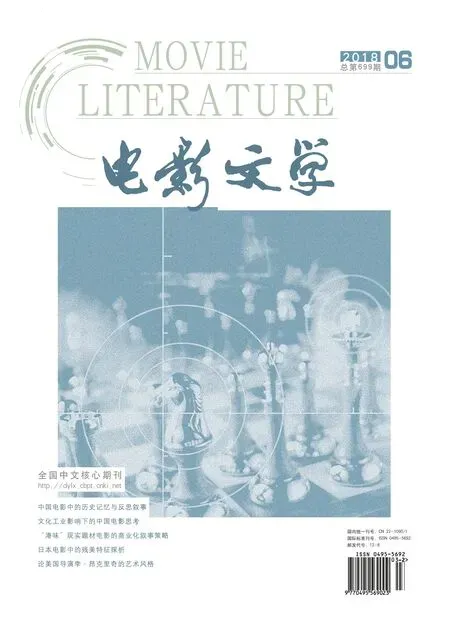擁抱在愛的荒原
1.臥室 晨
田衛東睜開眼睛,看了下時間,墻上的鐘表顯示6點30分。
田衛東用手揉了揉眼睛,坐起來,打了個哈欠。起床,穿衣服,穿鞋子的時候一不小心把腳邊的垃圾簍踢倒了。他從門后拿來了掃把和簸箕,把廢紙團掃了起來,站起身來的時候,田衛東扶了扶自己的腰,皺了皺眉頭。
桌面上擺放著寫好的書法大字“生生不息”,字體是楷書,很好看。
田衛東拿起書法大字看了下,然后搖了搖頭,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把寫好的大字揉成了紙團,丟到了腳邊的垃圾簍,結果又丟到了垃圾簍的外面,田衛東正要彎下腰去撿,扶了扶自己的腰。拿起腳邊的掃把和簸箕,紙團掃進了簸箕,把簸箕里的紙團丟進了垃圾簍。
2.側室 晨
田衛東進來,屋內光線很暗。田衛東走到窗戶邊,伸手拉開窗簾,強烈的光照進房間,屋子瞬間變得明亮起來,田衛東用手擋了擋眼睛。
屋內的桌子上放著一個香爐,香爐里還有插著三支香的根部,根部下面是厚厚的香灰,香爐上方的墻壁上掛著一張遺像。
田衛東的手拉開桌子的抽屜,打開了香盒,從里面抽出三支香,拿起桌子上的打火機,點燃香,放下打火機,用手輕輕地把香甩了甩,頓時煙霧繚繞。他把香插在遺像前的香爐里,靜靜地看著遺像中的人。
遺像中的人是一位老太太。
田衛東的嘴角微動,微笑著說:“老伴兒啊,你的夢我收到了,我今天想回去看看,快20年沒回去了吧,今個兒帶著你一起。”
3.臥室 晨
田衛東進來,把床上的被子疊了疊,放在了床的里側,又來到衣柜前,打開衣柜。
衣柜里零零散散地掛著幾件衣服,衣服不多,但是很整齊。
田衛東從衣柜里拿出來幾件衣服,扔到床上。從衣柜下方的抽屜里拿出來一個手提袋,關上抽屜和衣柜門,把扔在床上的衣服認真地疊了疊,一起放在了拿出來的手提袋里,然后拎起袋子。
4.側室 晨
田衛東進來,把裝了衣服的手提袋放在腳邊,伸手摘下老太太的遺像,拉開了桌子的抽屜,從里面拿出來一條白色的手帕,將遺像輕輕地擦了擦,在擦到遺像上老太太的眼睛的時候,田衛東笑了笑:“小時候你就愛笑,到老了還是在笑,你這都笑了一輩子了,誰也沒有你過得開心啊!哎,要不是因為那條鯽魚,你,哎。”
田衛東把手帕抖了抖,然后折疊好了,放回了抽屜里,關上抽屜,拎起來腳邊的手提袋,把遺像往自己的胸口處貼了帖,閉上了眼睛。最后把遺像裝在早已收拾好的手提袋里,和自己的衣服放在一起。
5.門外 晨
田衛東走出門,關門,鎖門,又拿手晃了晃門環。
6.小區 日
田衛東拎著袋子,從樓里出來,風很大,田衛東把外套的拉鏈拉上,拿著袋子的手攥了攥,走出小區。
7.大巴車上 日
田衛東坐在大巴車的前排靠近窗戶的位置,車上播放著一首曲子《常回家看看》。車上的乘客不多,零零散散的,大概只有五六個人。在田衛東斜前方坐著一對兒青年男女,大約20多歲,兩個人說說笑笑的。田衛東看到這兩個人,笑了笑,把臉轉向了窗外。
8.田野 日
一望無際的田野,金燦燦的油菜花,筆直的公路兩旁,綠樹成蔭,大巴車在公路上行駛。
田衛東畫外音:“大巴車飛奔在我回家的路上,已經很久沒回來了,常回家看看的歌聲,敲擊著我的心靈,怦然心動,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常回家看看。”
9.巴清河畔 外
村頭一座長長的橋,一條悠悠的河,河水緩緩地流向遠方。
河的旁邊有一個大石頭,石頭上三個紅色大字“南坪村”。
大巴車駛來。
田衛東畫外音:“這里便是巴清河了,久違了,我的老戰友。”
10.南坪村頭 日
字幕:1963年。
四個孩子,迎面跑過來,兩個男生、兩個女生。
田衛東跑得比較快,在最前面,后面三個孩子跟不上。
王丫丫:“衛東哥,你別跑這么快啊,你等等我們幾個。”
田衛東停下來,回過身來,看著他們三個,兩只手扶住膝蓋,彎下身子,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你們,你們倒是快點啊,上學要遲到了。”
宋楚媛:“衛東叔兒,你別跑了,等等我們。我,我是真的跑不動了,累死我了。”
田躍進:“是啊,衛東,你看楚媛都快跑不動了,別跑了,別跑了。再說了,老師就是你爸爸,你著啥急。你等會兒我,我都快要趕不上你了。”
田衛東:“哥,你快點。我遲到的話,我爸回家打我。”說完又跑了起來。
三個小朋友趕緊追,宋楚媛一個踉蹌,摔倒了,坐在地上哭了起來。
田躍進和王丫丫趕緊去扶宋楚媛,宋楚媛疼得哇哇大哭。
田衛東趕緊從前面跑回來,蹲在宋楚媛的身邊,擦了下自己額頭上的汗:“楚媛,你摔哪兒了,疼不?”
宋楚媛:“我,我腳疼。”
王丫丫脫掉宋楚媛的襪子,看到宋楚媛腳踝腫了一個大包。
田衛東用手碰了下宋楚媛腫脹的腳踝。
宋楚媛:“疼,衛東叔兒。”
田躍進:“衛東,都賴你,你要是不跑那么快的話,楚媛也不能摔傷。”
宋楚媛趕緊擦了擦眼淚:“躍進叔兒,沒事,不賴衛東叔兒,我,我現在不疼了。”
田衛東:“楚媛,是我不好。我背你去村兒那頭老根兒叔的醫務室吧。”
宋楚媛:“你不去上學了?”
田衛東:“不去了,我爸回去打我,就讓他打吧,我可抗打嘞。”
王丫丫:“走走走,咱們都去,要挨打的話,咱們一起挨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宋楚媛:“丫丫姑,你也陪我去嗎?”
王丫丫用力地點了點頭。
田衛東蹲到宋楚媛的面前,背對著宋楚媛:“楚媛,上來吧,我背著你。”
田躍進拍了下田衛東的肩膀:“算了,這里我最大,是大哥,我來背吧。”彎下腰來。
王丫丫扶著宋楚媛,爬上了田躍進的背。
四個人往回走。
出片名:擁抱在愛的荒原。
11.田衛東家 黃昏
田衛東進院。
田衛東的父親田伯勛從堂屋里出來:“今個兒你上哪兒玩去了?沒去上學。”
田衛東:“今個兒我去上學了。”
田伯勛:“胡說,我一直在學校,咋沒看見你嘞?”
田衛東:“我和堂哥、丫丫,還有楚媛一起去嘞,去的路上,楚媛把腳給崴了,我和堂哥還有丫丫,陪她去咱村兒西頭老根兒叔兒的醫務室了。”
田伯勛:“真的?”
田衛東:“嗯,真的。”
田伯勛:“現在咋樣了,楚媛的腳還疼不?”
田衛東:“她現在還在老根兒叔的醫務室,我待會兒就過去看看她。”
田伯勛:“楚媛比你小三歲哩,你多讓著點她,別欺負人家。她大老遠在咱們村兒上學,得多幫她,知道嗎?”
田衛東:“嗯,我知道了。”
田伯勛嘆了一口氣。
田衛東母親:“行了,你倆快過來吃飯吧。”從廚房里端碗筷進了堂屋。
田衛東和田伯勛也進了堂屋。
12.田衛東家門外 黃昏
田躍進、宋楚媛、王丫丫來到了田衛東家門口。
田躍進背著宋楚媛:“二叔,在家嗎?”
田衛東母親走出來,看到門外的三個孩子:“是你們幾個啊。找衛東嗎?咋了?”
王丫丫:“嬸子,我們來找勛叔兒。”
田衛東母親:“進來說。”
13.田衛東家 黃昏
幾個人來到屋里,看到還在吃飯的田伯勛和田衛東。
宋楚媛:“勛爺爺,我們來跟你說,今天衛東叔兒沒去上課,是……”
田伯勛搶先說了一句:“是陪著你去老根兒醫務室了,是不?”
宋楚媛:“啊?爺爺,你都知道了啊。那你沒打衛東叔兒吧?”說話越說聲音越小。
田伯勛笑了下:“好啊。你們來找我就是說這事兒?在你們這群小娃娃眼里,我就這么不講理嗎?嗯?”
三個小朋友都笑起來。
田衛東母親:“這能怪誰?還不都怪你,整天拉著個臉,孩子們見了你就害怕。”
田伯勛:“我是老師,不嚴肅,以后怎么管教他們幾個毛孩子。”
田衛東母親轉身看宋楚媛:“楚媛,咋樣了?現在腳還疼不?”
宋楚媛:“奶奶,不疼了,嘻嘻。”
田伯勛拿起桌子上的旱煙袋,抽了一口,吐出一團白煙來:“楚媛受傷了,這幾天就別去上學了,就在家里養著吧,等好了再去上學。”
宋楚媛:“伯勛爺爺,不用。我的腳已經不疼了,不耽誤去上學。”
田伯勛點了點頭,看著田衛東:“那以后就衛東負責背著楚媛去上學吧。”
宋楚媛咧開嘴笑了。
田躍進:“叔兒,不用,我來背楚媛就行,我們四個里面,我最大,我背吧。”
田伯勛:“嗯,也好。”看著四個孩子,點了點頭。
14.南坪村 黃昏
字幕:1973年。
天下著大雨,19歲的田衛東光著上身,從村前的橋上跑著向自己家。
15.田衛東家院子 黃昏
田衛東渾身被雨水淋透,汗衫提在手里,剛進院子,就看到院子里的柴火垛上面蓋著的塑料布被風吹起來了,嘩啦嘩啦地響,塑料布下面的柴火已經被雨水打濕了大半。田衛東把提在手上的汗衫圍在脖子間,然后跑過去,蓋好塑料布,把墻邊的鐵鍬拿過來,壓在了塑料布上,把圍在脖子間的汗衫解下來,拿在手上,轉身跑進了堂屋。
16.田衛東家堂屋 黃昏
田衛東跑進來,坐在大板凳上。
父親赤腳坐在堂屋里僅有的一把椅子上抽著旱煙,母親踮著小腳從廚房出來,往堂屋里端飯。
老兩口子見兒子回來,兩張核桃皮皺臉立刻笑起來。
田伯勛立刻湊到煤油燈前,用小指頭上那個長指甲打掉了一朵燈花,堂屋里面立刻亮堂了許多。
田衛東母親看著田衛東,接過田衛東提在手上的汗衫:“衛東啊,淋壞了不?趕緊去里屋,把衣裳換了,過來吃飯。今個兒給你做了你愛吃的玉米面糊糊。”
田衛東:“嗯。”走進堂屋里間。
田衛東畫外音:“19歲,我走出高中校園,那是‘文革’后期,因為早幾年我父親被劃為‘右派’,我受到了影響,無法推薦讀大學,便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知識青年返鄉勞動。”
17. 南坪村 黃昏
雨后,一條彎彎的彩虹掛在天邊。
18.巴青河畔 日
田衛東坐在岸邊,看著滾滾而去的河水。
田衛東畫外音:“落后貧窮的鄉村,我難以適應,甚至無法接受。無聊之余,村頭巴清河畔便成了我散心的去處,夏日我常常孤寂地坐在河岸上,享受著那柔和的清風。巴清河是我們村的母親河,一直流平,不能蓄存,旱澇由它,冬去春來,黃土野草,大田上不得豐收。”
19.王丫丫家院外 晨
田伯勛來到王丫丫家的院門前:“丫丫,在家嗎?”
屋里回應:“在呢,誰呀?”
已經18歲的王丫丫從屋里出來:“是勛叔兒啊,啥事啊?快屋里坐吧。”
田伯勛一只手拿著旱煙袋,另外一只手背在身后,進院。
20.王丫丫家 晨
兩人來到屋里。
王丫丫:“勛叔兒,您坐。”
田伯勛坐在椅子上。
王丫丫給田伯勛倒了杯茶后,也坐在了板凳上:“勛叔兒啊,大清早的,啥事啊?”
田伯勛抽了一口旱煙,田伯勛支支吾吾沒有說話,又嘆了一口氣。
王丫丫看看田伯勛:“勛叔兒啊,到底咋了啊?這都鄉里鄉親的,有啥不能說的,您說吧,丫丫聽著呢。”
田伯勛:“哎。是關于你衛東哥的事兒。”
王丫丫站了起來,目不轉睛地看著田伯勛:“衛東哥?俺衛東哥咋了呀?”
田伯勛噗嗤一聲笑了:“娃娃,你咋比我還激動嘞?”
王丫丫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坐在凳子上。
田伯勛:“早幾年,叔被劃成了‘大右派’,拖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后腿。可是這事兒跟你衛東哥也沒關系啊。今年,他自從高中畢業以后,因為我的成分不好,他沒辦法推薦上大學。這段日子一直愁眉苦臉的,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我這個做長輩兒的心里也是著急。丫丫啊,你跟衛東最要好,你們從小一起長大,他打小就比較愛聽你的話,你們年輕人吶,也能說到一塊兒去。我尋思著,你幫我勸勸他,讓他想開點。無論咋樣,這日子還得過啊,你說是不?”
王丫丫:“嗯,勛叔,鬧了半天,您說的是這事兒啊。勛叔,我知道衛東哥心里委屈。叔,您還別說,這個事兒啊,我還真往心里去了。我昨天已經跟村里的其他幾個年輕人商量過了,打算今晚開個動員會,我們要把衛東哥的積極性給調動起來。我打小也是您看著長大的,您和嬸兒是疼我哩,我都知道。您放心吧,衛東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
田伯勛:“娃娃,叔兒知道你心眼兒好哩。叔兒謝謝你了。”
王丫丫:“叔,您咋這個客氣哩。我還記得小時候,我和衛東哥一塊去上學,您是老師,您沒少照顧我。”
田伯勛點了點頭。
王丫丫:“勛叔,這個事兒,交給我,你就放心吧。”王丫丫拍了幾下自己的胸膛。
田伯勛:“好孩子,得嘞,那叔就走了啊。”
王丫丫:“叔,你來的真是時候,我這兒剛做好飯,您擱這兒吃點吧。”
田伯勛:“不了,娃娃,我走了,你嬸子也做好飯了,等著我回去吃哩。”起身走了。
王丫丫:“那行,叔,您慢走。”
21.王丫丫家院子 晨
田伯勛出了堂屋,看到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樹,他抬頭看了下枝繁葉茂的大槐樹,大槐樹的樹葉子間隙之間露出的太陽光,晃得他直眨眼睛。他拿著自己的旱煙袋,背著手,走出了院子。
22.南坪村 黃昏
晚霞在天上紅彤彤的,渲染得整個天空都是紅色。太陽落山,暮色降臨。南坪村很安靜。
村里家家戶戶煙囪里開始冒炊煙,開始準備晚飯,遠處傳來幾聲狗叫。
23.田衛東家 夜
堂屋里,田家三口人在吃飯。
田衛東幾大口就吃完了,他咀嚼著嘴里的食物,擱下碗筷,對還在吃飯的父母說:“爹、娘,我去丫丫家一趟,有點兒事。晚會兒再回來。”
田伯勛在一旁滿意地點點頭:“行,去吧,去吧。”
田衛東母親:“披上點汗衫,外面涼哩。”
田衛東:“嗯。”進里間拿了一件汗衫,走了出去。
田衛東母親:“他這是要干啥去呀?”
田伯勛放下筷子,拿起桌邊的旱煙袋,抽了一口,吐出一大團白煙:“自然是大事。”
田衛東母親看了下田伯勛,撇了撇嘴:“你是不是知道啊?你知道,你不告訴我?”
田伯勛:“哈哈哈,你就看著吧,咱們衛東要爭氣哩,咱們這南坪村也要變天哩。”
田衛東:“小娃娃能干成啥事兒?”
田伯勛:“你這個人真是迂腐!小娃娃咋了啊!當年毛主席也不就是小娃娃嘛,人家讀書的時候,就立志,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不后來才有的一番事業,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老蔣打跑了,要不然這新中國咋來的?你別小看小娃娃,小娃娃的力量大著哩。”
田衛東母親笑了起來:“一說起事兒來,你就一套一套的,省得別人不知道你讀過兩年書咋嘞!衛東的事兒啊,你愛說不說,不管大事小事都行,反正只要是好事就中。”
田伯勛笑了笑,自顧自地抽起煙來,抽了一口旱煙,吐出一大團的白煙來。
田衛東母親收拾好桌上的碗筷,把碗筷往廚房里面端。
24.南坪村 夜
月亮很大很圓,月光很亮,月光下的村莊不是很暗。
不遠處傳來幾聲狗叫和人走路的聲音。
巴清河的河水靜靜地流淌。
25.王丫丫家 夜
一起來的有全村的20來歲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一共是36個人,滿滿當當地站在王丫丫家的院子里。
王丫丫:“今天咱們生產隊的年輕力壯的,我都叫來了,有點事要跟大家伙兒商量。咱們開個會,今個兒咱們得好好研究下村里的出路。”
眾人言論紛紛。
“什么出路?”
“要干啥呀?”
“怎么個意思?”
王丫丫:“我們商量了,咱們成立個南坪村青年突擊隊,平坡開地。衛東哥,你們男的多分兩個班,我們女孩子組成一個班,我們的鐵姑娘班和你們男的,見個高低怎么樣?”
任巧玲:“對,就是,我們要跟你們打擂臺,看看誰最厲害!”
鄭鐵柱站起身來,走到任巧玲身邊,用手比劃了下身高,任巧玲只到鄭鐵柱肩膀的位置:“切,這就是差距!你說誰厲害?再說了,你們一群女娃娃,能干什么啊?”
任巧玲狠狠地掐了鄭鐵柱胳臂一下,鄭鐵柱疼得“哎呦”了一聲。
宋楚媛沖著鄭鐵柱喊了一句:“你們能干什么,我們就能干什么,不要小看了我們這半邊天的力量。姐妹們,你們說是不是啊?”
其他姑娘七嘴八舌。
“就是,就是。”
“對,不能被他們男的看扁了。”
“你們男的,是不是不敢比試?”
“要我看是他們男的不敢比試怯場了吧?”
“對對對,就是!”
“哈哈哈哈。”
鄭鐵柱:“得得得,姑奶奶們,我錯了,我錯了還不行嘛。你們婦女最厲害,行了吧。哎呦喂,任巧玲,你下次下手輕點,疼死我了。”揉著自己被任巧玲掐了的胳臂。
大家看著鄭鐵柱揉著自己的胳臂齜牙咧嘴的模樣,都哈哈起來。
田衛東:“好。那我們以后就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志同道合的知己!”
大家伙兒把手圍在一起,喊了一聲“嘿”。
聲音很響,王丫丫家的狗正趴在門沿兒,被嚇了一大跳,“汪汪汪”地叫。
眾人聽到之后,再次哈哈大笑起來。
26.巴清河畔 日
生產隊孫大飛和36個青年人聚集在巴青河畔,田衛東在孫大飛面前比劃著什么,手勢指著巴清河的對岸。
巴清河的對岸是一片荒野。
田衛東畫外音:“第二天,我們到隊里請纓,講了我們的想法,把屬于我們南坪村轄區的近百畝河坡于今冬明春開墾平整,變成可耕地擴大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種植,增加社員收入,得到了生產大隊隊長的支持。”
27.田間 日
田間豎起一桿大旗“青年突擊隊”,勞動號子回蕩起來。
田衛東挽起袖子和褲管,光著腳丫子推著架子車,架子車上面拉的是挖出來的土,鄭鐵柱幫著用鐵鍬抵住架子車的車尾處,彎下腰來使勁兒往前推。
其他的男孩子有的光著膀子用鐵鍬翻地,有的拉著架子車往外拉土。
拉架子車的,兩個人一組,一個負責往前拉,另一個幫著往前推。
女孩子統一盤起頭發,彎起腰來,播種。
王丫丫、宋楚媛和男生一起翻地。
鄭鐵柱走到任巧玲面前,和任巧玲一起翻地。
任巧玲看了鄭鐵柱一眼,眼睛落在鄭鐵柱的胳臂上:“喂,你的胳臂,還疼不?”
鄭鐵柱:“嘿,這么沒禮貌!誰叫喂啊?我沒名字啊?”
任巧玲:“鄭鐵柱!給你好臉了,是不?”
鄭鐵柱:“嘿嘿,你要早這么客氣,我不就回答了嘛。胳臂不疼了,已經好了。”
任巧玲:“啊?已經好了啊?沒想到好得這么快,哈哈,下次我得狠狠地掐,讓你十天半個月動彈不了,哼。”
鄭鐵柱:“得得得,姑奶奶,我惹不起還躲不起嘛。”
宋楚媛笑了笑,對著任巧玲說話:“哈哈,巧玲,你就別逗他了,看他怪可憐的。”
鄭鐵柱:“還是楚媛疼我。”
宋楚媛:“呸,誰心疼你,我是心疼巧玲的手。”
大家伙兒哈哈大笑起來。
28.巴青河畔 日
巴清河河水流得很急。
河邊的樹上落著一個鳥巢,母鳥從遠處飛過來,巢里的兩只小鳥張開嘴巴。母鳥把嘴里的蟲子喂給小鳥。
母鳥和小鳥“嘰嘰喳喳”地叫得很歡。
29.田間 黃昏
男女青年坐在一起吃飯,大家伙兒高興地開起玩笑。
任巧玲:“衛東哥,你咋不找個對象嘞?你看你這個年齡的,都成家了呢。”
鄭鐵柱突然緊張地看著任巧玲。
田衛東:“男子漢大丈夫,先立業后成家。”
任巧玲:“衛東哥,你別瞎說了。我看你啊,是早就有相好的了,是不?”
大家伙兒起哄。
“啊?真假?”
“誰呀?”
任巧玲:“遠在天邊……”走到王丫丫旁邊,“近在眼前。”
鄭鐵柱的表情明顯放松了些。
大家伙兒跟著起哄。
“丫丫和衛東哥啊?”
“啥時候的事兒啊?”
“好好好……”
王丫丫羞紅了臉,拍了任巧玲一下:“哎呀,巧玲,你別瞎說。”
田衛東:“巧玲,你這是聽誰說的嘞?”
任巧玲:“這還用誰說啊?你干活兒的時候,那個眼神兒都快飛到丫丫姐身上去了,哈哈哈哈。”
大家伙兒也都笑起來。
田衛東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一瞥眼,看到王丫丫正看著他呢。
宋楚媛看了下兩個人,離開了。
大家伙兒對于宋楚媛的離開沒有在意,只有田躍進看到了,他慢慢跟了過去。
30.巴清河畔 黃昏
宋楚媛來到巴清河邊,靜靜地看著河水,然后哭了起來。
田躍進看到宋楚媛哭了,急忙走上來:“楚媛,你咋了?”
宋楚媛連忙擦了擦眼淚:“躍進叔,沒,我沒事。”扯著自己的衣角。
田躍進:“楚媛,你的心思我懂。你雖然不是南坪村的,但是咱們從小一起長大,輩分上你管我叫叔,年齡上,我是大哥。從小到大,你的心思,我都懂哩。”
宋楚媛看了下田躍進,沒有說話,把頭又轉向了巴清河。
田躍進也轉向了巴清河:“楚媛,衛東是我堂弟,都是自家人,有啥事兒都可以說開。我知道,他喜歡丫丫,雖然他沒跟我說過,可是從小到大,我都知道。楚媛,我知道你也喜歡,喜歡……”
宋楚媛用雙手抱住了自己的肩膀,蹲下身來:“躍進叔,你別說了。”
田躍進蹲下身子:“楚媛,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我想跟你說,無論到啥時候,我都陪著你。”
宋楚媛看了下田躍進,看到田躍進的眼睛里流出兩行淚來。
宋楚媛:“謝謝你,躍進叔。”站起身走了。
田躍進一個人站在河邊,看到腳下有一塊土疙瘩,彎下腰來,撿起來,丟到了巴青河里,巴清河水面上濺起一大片水花。
31.田間 日
田里的禾苗長起來了。
青年突擊隊的勞動號子,又回蕩起來。
32.田間 日
男青年光著膀子,在田間收割麥子。
田衛東把上衣搭在肩膀上,褲子已經被汗水浸濕了一大半,割麥子。
鐵姑娘班的女青年把麥秸稈收拾起來,用架子車往外拉。
33.麥場 日
金燦燦的麥粒在場里脫收,宋楚媛揚起麥粒,大家把麥粒全部攤在麥場里,晾曬,大家伙兒都格外地開心。
34.南坪村大會場 日
“勞模大會”的大字掛在會場上。
田衛東和王丫丫站在臺上,身戴大紅花,下面的群眾一直在鼓掌。
田衛東畫外音:“我們懂了什么是創業,我們光榮地完成了造田計劃,荒坡變成了寶地,旱澇都可以保收,干部社員拍手稱贊,我被評為全鄉知識青年帶頭人,王丫丫也被評為勞模和鐵姑娘班長的美譽,并在全鄉,各個大隊做巡回演講以示表彰,我們好像帶上了光環。”
35.南坪村生產隊大院 夜
青年突擊隊成員在場,大家伙兒都坐在院里。
田衛東:“同志們,咱們的初步計劃已見成效,下一步,咱們種點其它的,大家伙兒有啥建議盡管提,都獻言獻策,怎么樣?”
王丫丫:“我們生產隊沒種過花生,咱們這次種點花生吧。”
王建國:“既然是開山,我覺得咱們重點樹苗啊,一來呢可以綠化,二來呢樹成材之后,可以賣錢。”
鄭鐵柱:“對呀,炒出來的熟花生,也是很香的嘞。”
任巧玲:“你就知道吃!”
鄭鐵柱:“你就知道擠兌我!”
鐵姑娘班的姑娘們哈哈大笑起來。
田衛東:“我覺得可以,而且啊,咱們在樹苗林子里,種上油菜花,金燦燦的,那多喜人。”
宋楚媛:“種這些都不成問題,關鍵是水源。要開的山,在村后,一擔子一擔子挑水的話,得多麻煩啊。”
田衛東:“楚媛,你和我想到一塊兒去了。我現在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王丫丫:“啥想法?”
田衛東:“巴清河!”
鄭鐵柱:“衛東哥,你該不會是要挖河吧?”
田衛東站起身來:“對!”
鄭鐵柱也站起身來:“可是,衛東哥,巴清河在村前,開的山在村后啊!”
人群開始議論起來。
“這個工程量太大了吧。”
“估計咱們所有的人一起挖,挖到明年也挖不完呢。”
“是啊,而且巴清河是祖祖輩輩的老河,挖支流的話,村兒里的老人會同意嗎?”
田衛東看到大家說得挺熱鬧,拍了拍手:“我知道,大家伙兒在顧慮什么,這些顧慮我都想過。人要喝水,莊稼和樹苗也要喝水,我們一擔子一擔子地挑水,更是麻煩。巴清河既然是母親河,就是要為后輩兒孫謀福祉的。咱們的引流不能太大,引出去一條小支流就可以,既能保證村后用水的需求,又不能讓上游枯竭。所以,咱們得好好規劃下路線。”
王建國:“這,這能行嗎?”
王丫丫站起身來:“衛東哥,我支持你。”
宋楚媛也站起身來:“衛東叔,我也支持你。”
鐵姑娘班的姐妹們都站起來。
任巧玲:“丫丫班長,我們姐妹們都支持。”
王建國站起來:“我不同意,這條河是祖祖輩輩的母親河,不能動!”
王丫丫看了下王建國,然后走到王建國身邊,拍了下王建國的肩膀:“建國,你說黃河是不是母親河?”
王建國停頓了下:“當然是,黃河自古就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是……”
王丫丫打斷了王建國的話:“對呀,連黃河那么龐大的母親河都能開發支流,為啥咱們的巴清河就不能嘞?”
王建國不說話了。
田躍進也站起來:“我覺得可行。我同意。”
田衛東:“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事業做得那么好,都是大家的功勞。我田衛東在兄弟姐妹們面前起個誓,如果出了問題,我一個人擔著。”
王建國走到田衛東面前:“衛東兄弟,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同意,我同意。”
田衛東拍了拍王建國的肩膀。
鄭鐵柱:“衛東哥,出了問題,咱們共同承擔,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大家伙兒說,是不是啊?”
大家:“對!”
36.南坪村后的荒野 晨
青年突擊隊開始勞作,勞動號子再次響起來。
37.巴青河畔 日
青年們拿著勞動工具,有拿鋤頭的,有拿耙子的,有拿鐵鍬的,還有拉架子車的。
田衛東拿著鐵鍬挖地,脖子間系了一條毛巾。
任巧玲和宋楚媛拉過來架子車,王建國和鄭鐵柱往車子上面裝土。車子滿了之后,王建國和鄭鐵柱幫著把車子推起來,然后任巧玲拉架子車,宋楚媛把鐵鍬插在車子上的泥土里,手推著鐵鍬把兒,用力往前推。
其他的人也都這樣干活。
挖土,裝土,拉土。
38.南坪村村后 日
青年突擊隊在干活。
田衛東和王建國一起,站在挖好的河溝里,往上面扔土。
這時候,任巧玲看了下村兒里的方向,轉過身來對人群喊了一聲:“大飛叔兒來了。”
大家伙兒往回看,遠遠地看到生產隊隊長孫大飛往這邊趕來。
大家放下手里的活迎了上去。
孫大飛來到人群中:“怎么樣了?同志們!”
田衛東:“大飛叔兒,我們這就快完工了。”
孫大飛:“你們挖了兩個月了,辛苦了啊。來,算上我一份,鐵鍬給我一把!”
鄭鐵柱把自己的鐵鍬給了孫大飛。
孫大飛和大家伙兒一起挖河開渠。
39.荒野 日
大家伙兒深翻土地,改造土壤。
王建國擼了下袖子:“咱們得讓全鄉富起來!”
40.荒野 黃昏
字幕:三年后。
樹苗已經長大,樹下更是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41.巴清河畔 夜
田衛東和王丫丫走來。
王丫丫看著靜靜的河流,跳起舞來。
一會兒,王丫丫邀請田衛東跳舞,兩個跳了一會兒,面對面停下。
王丫丫:“哥,你今年23了,我也21了,在家里像你我這般年齡的人大都已經定親了,今天有媒人去我家了,安排明天相親,你咋想的?”
田衛東看了下王丫丫:“丫丫,你咋想的?”
王丫丫臉紅了,害羞地低下了頭,然后昂起臉來:“哥,我非你不嫁!”
巴清河水靜靜地流淌。
田衛東畫外音:“其實我深知丫丫對我的感情,只是我家的成分不好,不敢與王丫丫談親事。這個晚上,我和王丫丫互訴衷腸,彼此定下交好誓約。”
不遠處的大樹后面,有一個人目睹了這一切。
42.田衛東家門口 日
孫大飛敲門:“衛東,衛東在家嗎?”
田衛東從屋里出來:“誰呀?孫叔啊,來,屋里坐。”
43.田衛東家 日
田衛東:“孫叔兒啊,啥事啊?”
孫大飛:“哎,衛東啊,你讓我怎么跟你說啊,哎。”
田衛東:“孫叔兒,您是我的長輩,有啥事,您就直接說吧。”
孫大飛:“衛東啊,叔兒知道你有能耐,有出息哩,但是你要相信,無論發生啥事,組織上都是在考驗你,你都不要鬧情緒。”
田衛東:“孫叔兒,到底啥事啊,這么嚴重。”
孫大飛:“昨天下午吶,我去鄉里開會,王丫丫被提升為鄉里的生產隊婦聯主任了……”
田衛東:“孫叔兒,這是好事啊!我這就去告訴丫丫去,讓她也高興高興。”站起來要走。
孫大飛攔住他,把他摁在凳子上:“衛東,你等下,你別著急。我跟你說,現在丫丫已經知道了這個事情了,我要說的不是丫丫的這個事兒,是關于你的事兒。”
田衛東:“我?關于的我事兒?我咋啦呀?”
孫大飛猶豫了一下,田衛東目不轉睛地看著孫大飛。
孫大飛:“鄉里決定,把你的青年突擊隊隊長和勞動模范撤掉,并且解散你們的青年突擊隊。”
田衛東猛然站起身來:“啊?為啥呀!為啥呀解散我的青年突擊隊啊?孫叔兒,您也知道我們青年突擊隊這幾年為咱們村兒、為咱們生產隊辦了多少實事啊,這到底是為啥呀?為啥要解散我們的青年突擊隊啊!”
孫大飛嘆了口氣。
田衛東看了一下孫大飛,沒有說話,用手捶了一下桌子。
孫大飛:“我知道,我知道,這些我都知道,這幾年吶,你們這些年輕人挖河開渠,種莊稼,栽樹苗,你們青年突擊隊做的這些事情我都看在眼里,青年突擊隊的名頭打的響著嘞。咱們生產隊在全鄉的評比都是一等一的成績,你們青年突擊隊功不可沒。哎,世風日下,解散這支隊伍,是鄉里的意見,我也沒辦法。開會的時候,我也向鄉里表了態,替你們說了很多公道話,沒轍啊。而且,名單已經公示了,張貼在村里十字路口的宣傳欄了。”
田衛東要往外走:“好,我現在就去鄉里評評理,這是憑什么呀!”
孫大飛:“衛東,你別激動,你先坐下。”
孫大飛拉著田衛東坐下:“衛東,你有情緒,叔兒能理解。你聽我說,鄉里準備提拔社會中堅力量,你和王丫丫是咱們生產隊的推薦人選,可是啊,這隊里也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啊。咱們南坪村生產隊只是個生產隊,這十幾個生產隊組成一個大隊,大隊書記才是一把手哩,是生產大隊里另外一個干部怕你以后啊爭了他的權,就去鄉里告了你的狀,說你根不紅苗不正,‘右派’子弟,怎么能擔任社會主義接班人。所以啊,鄉里研究了一下,這才這么決定的。”
田衛東又一次站起來:“孫叔,我父親是‘右派’,可是我不是啊。那些人是在嚼舌頭根兒,你看不出來嗎?虧你還是咱們生產隊的干部,我看你也是昏庸無能!”
孫大飛站起身來:“你這娃娃,這是咋說話嘞。我和你父親是平輩,輩分上你得管我叫叔,你咋能這么跟我說話嘞?”
田衛東:“身為干部,不能公平公正,憑什么讓人尊重你。”
孫大飛:“簡直不像話,簡直不像話!”
田衛東:“怎么?難道我說得不對嗎?”
孫大飛:“娃娃,我都40多歲了,我孫大飛做事向來是光明磊落,我既然是咱們南坪村生產隊的隊長,就得做到一心為人民。娃娃,這是鄉里的決定,不是我個人的決定,你就不能冷靜下來,好好想想下一步該怎么做嗎?你在這兒沖我發火,能解決個啥問題嘞!”
田衛東看了孫大飛一眼,然后,沖出了屋。
44.田衛東家院子 日
田衛東從堂屋門外抓住一把鐵鍬,把鐵鍬重重地往墻上一摔,鐵鍬上遺落的泥巴被崩掉了,稀里嘩啦地往地上落。田衛東握緊了手上的鐵鍬就往外沖,牙齒咬得“咯吱咯吱”地響。
孫大飛看到田衛東拿著鐵鍬往外沖,急忙跑到院子里,拉住了田衛東:“衛東,孩子,你這是要干啥去!”
田衛東對孫大飛大聲吼叫:“你盡管一心為你的人民去好了,我的事兒不用你管了。還有,今天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是誰干的!我現在就去找他評評理,讓全村兒男女老少都給我評評理,這是憑啥!”
孫大飛:“衛東!你這哪里是去評理,你這架勢分明是打架去!”
田衛東:“打架!打架怎么了!我倒要看看,這世上還有沒有王法了。憑什么這么對我,我到底做啥傷天害理的事兒了?”使勁兒地掙開了孫大飛,大步往外走。
孫大飛在后面追,喘著粗氣,喊著:“衛東,你回來,回來!衛東!”
45.南坪村十字路口 日
田衛東一路小跑來到路口處,把鐵鍬放下,對著天空喊:“我田衛東做事向來問心無愧,憑什么這樣對我!”
田衛東嘶吼著,拿起來手上的鐵鍬,砸向十字路口的宣傳欄。木質的宣傳欄被砸碎了,上面的貼的紅紙公示紙掉下來,上面寫著“關于田衛東同志的處分”。田衛東并沒有停下,繼續用鐵鍬砸宣傳欄,宣傳欄被砸得一大塊一大塊的,丟到地上。
村民們聽到動靜出了門來,看到了路口廣場正在砸東西的田衛東,也都圍了過來。
李大媽:“衛東,你這是咋了呀這是?”
王建國走了過來,看了下地上宣傳欄上面的字兒:“衛東哥,這是為啥呀!憑什么解散咱們!”
田衛東:“憑什么?憑他是大隊干部,憑他是根紅苗正的黨員,看不上群眾!”
王建國:“簡直欺人太甚!”
趙志國:“衛東,你別著急。叔不識字,上面寫的啥啊?”
鄭鐵柱走了過來:“叔,上面說要解散我們青年突擊隊,撤了衛東哥的勞模。還有,上面說衛東哥是‘右派’分子,不能做社會主義接班人。”
趙志國:“啊?咋會這樣啊?你們不是干得好好的嘛,這咋突然就全變了。”
孫大飛這才跟了上來,上氣不接下氣。
趙志國:“他孫叔,這事兒你知道嗎?”
孫大飛:“我知道。”
趙志國正要說話,被身后的趙大嬸扯了幾下衣角,趙志國沒再說話了。
孫大飛來到田衛東面前:“衛東啊,有啥事咱們回去說嘞,別在這兒說,影響多不好。”
王建國:“孫叔,你這是啥話!有啥事就是要當著全村兒的父老鄉親說個明白。”
鄭鐵柱:“就是,就是,有啥事不能藏著掖著。”
孫大飛:“你們有情緒,我理解,我是咱們生產隊的干部,維護咱們生產隊的利益是我的責任和義務。可是啊,這生產隊只是十里八村生產大隊的一部分,在上面還有鄉里嘞。這個處分是上面的決定,我也是沒辦法。發脾氣解決不了問題,現在我們回去好好商量商量這咋解決。王建國、鄭鐵柱,走,咱們回去,回去說哈,走走走。”對著王建國和鄭鐵柱揮揮手,然后又看一下圍觀的人群,“行了,散了吧,散了吧,都散了吧。”
王建國:“衛東哥,走。我倒要看看,他咋解決。”
人群散開了。
46.南坪村村里 日
孫大飛拉著田衛東往前走,鄭鐵柱幫著田衛東拿著鐵鍬,把鐵鍬扛在了肩膀頭兒上,王建國跟在后面。
47.巴清河畔 日
巴清河的河水流得很急。
48.田間 日
田衛東的父親和母親在田間鋤地。
李大媽跑過來,一路跑著一路喊著:“嫂子,嫂子,別鋤地了,嫂子,快回去。”
田衛東的父親和母親停住手。
田衛東母親:“他李嬸兒啊,咋了這是,著急忙慌的?”
李大媽來到田衛東的父母面前,兩只手扶住膝蓋,彎下身子,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快,快,快回去,你們家衛東,衛東,出事兒!”
田衛東父親和母親:“咋了!”
李大媽:“因為,因為……”大口地喘氣。
田衛東母親:“到底咋了,你看你這急人勁兒的。”
李大媽:“我聽孫大飛說了,說了,說是鄉里,要撤了衛東的勞模,解散,解散他們的青年突擊隊,衛東不干了,在十字路口拿著鐵鍬砸了宣傳欄,嚷嚷著呢,剛被勸回去。你們快回去看看吧。”
田衛東父親和母親拿起鋤頭就往南坪村的方向走。
李大媽后面喊他倆:“你倆慢點,等等我。”
49.巴青河畔 日
田衛東父親、母親和李大媽急忙往回趕。
巴清河的橋面很窄,田衛東父親沒看清楚腳下,腳下一滑,摔了一跤,差點掉進河里。田衛東的母親趕緊把他拉起來。
田衛東父親腳摔傷了,疼得齜牙咧嘴,用手上的鋤頭拄著地,一瘸一拐地往前繼續走。
50.田衛東家 日
孫大飛、田衛東、鄭鐵柱、王建國正在田衛東家的院子里。
鄭鐵柱從屋里拿出來幾個凳子來,讓大家伙兒坐下。
孫大飛:“衛東,你別犯渾,這事兒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兒,你要是不滿意,可以往鄉里反映,我只是奉勸你一句,別引火燒身。”
鄭鐵柱:“孫叔,這就是你說的來家里說事兒?你這不是欺負人嘛!”
孫大飛嘆了口氣。
王建國看了一下孫大飛,站起身來,指著孫大飛:“孫叔,我們不惹事兒,但是我們也不怕事。你不要覺得你是咱們南坪村生產隊隊長就可以隨便欺負人,現在是人民當家做主,不是舊社會的官僚主義!”
走到家門前的田伯勛看到了這一幕:“建國,怎么跟你叔說話呢?”
孫大飛看到院門外田衛東的父親、母親還有李大媽進來。
鄭鐵柱迎上去:“勛伯伯、大娘,你們可回來了,快勸勸衛東哥吧。”
田伯勛把手上的鋤頭放在腳邊。
田衛東看到父親:“爹,你是‘右派’,憑什么我要受影響!因為你,我不能推薦上大學。現在又是因為你,我被處分。現在,你滿意了不?你高興了不?”
孫大飛:“衛東!你怎么能這么說你爹呢!”
田伯勛瘸著腿來到田衛東面前:“孩子,是爹不好,是爹不好,是爹耽誤了你的前程。”說完,打了自己一巴掌。
田衛東母親趕緊拉住田伯勛,對田衛東說:“兒啊,這事兒不能怨你爹。你爹天天就跟我念叨著你越來越出息了,越來越好了。剛才你爹聽說你的事兒,在回來的的路上,還摔了一跤,差點掉到巴清河。”
田伯勛:“他娘,你別說了。”
田衛東看到田伯勛腫脹的左腳,流下淚來,”撲通“一聲跪在了田伯勛的面前,嚎啕大哭。
孫大飛蹲下身來,拍了拍田衛東的肩膀:“衛東,人民內部矛盾當屬于人民內部解決,現在我們解決不了,所以,我明天再去鄉里,給你討回個公道。”站起身往外走。
田衛東趕緊站起身來,拉住孫大飛:“孫叔,別,我不能害了你。命,這是命,這是我的命!”
孫大飛嘆了口氣,走了出去。
王建國和鄭鐵柱走到田衛東旁邊。
王建國:“衛東兄弟,看開些。”
鄭鐵柱:“衛東哥,你好好的,以后有啥事兒,你盡管跟我說,我鄭鐵柱能幫上忙的,我絕不含糊。”
田衛東擦了擦眼淚,拍了下兩個人的肩膀,點了點頭。
王建國看了下坐在凳子上的田伯勛夫婦:“勛叔、嬸子,我們先走了。”
田衛東的母親:“走吧,孩子,謝謝你們了。”
王建國和鄭鐵柱走出了田衛東家的院門。
51.南坪村 日
鄭鐵柱走在村路上,看到對面走過來的任巧玲,任巧玲手里拿著根棍子,氣勢洶洶。
鄭鐵柱攔下任巧玲:“巧玲,你這是干啥去?”
任巧玲:“我剛聽說衛東哥的事兒,憑啥這樣子對我們。孫大飛現在是不是在衛東哥家?我要去找孫大飛,看我不打死他。”說著就往前面走。
鄭鐵柱拉住任巧玲:“孫大飛沒在衛東哥家,已經走了。我剛打那兒回來。”
任巧玲:“那我去他家,我今天不打的他大口大口地吐黃水,我就不干了。”
鄭鐵柱又拉住任巧玲:“巧玲,你冷靜一下,沖動解決不了問題。”
任巧玲:“鄭鐵柱,你是不是慫了?你還是個男人不?受這么大的委屈,你不去報仇?”
鄭鐵柱:“我怎么不是男人了,我這是在心疼你,看不出來嗎?你是不是傻,你這么過去,萬一和孫大飛打起來,你能打過他?萬一他打了你,我不得心疼死!”
任巧玲愣住了,看了一下鄭鐵柱:“鐵柱,你,你說啥?”
鄭鐵柱:“巧玲,你說衛東哥出了這么大的事兒,而且咱們青年突擊隊也解散了,以后我見你,肯定不如以前方便了,那咋整?”
任巧玲看了鄭鐵柱一眼,臉很紅,低了下頭,然后又昂起頭來,用棍子戳了戳鄭鐵柱:“誰要和你見面,想什么呢你?”
鄭鐵柱:“巧玲,俺,俺,俺稀罕你,你稀罕俺不?”他不敢看任巧玲,把臉別過去,看著腳下的地。
任巧玲看了鄭鐵柱的神態,“噗嗤”一聲笑了:“鄭鐵柱,你害臊了?你說你還是個大老爺們不?我都沒害臊,你害臊個啥呀?”
鄭鐵柱轉過臉來,認真地看了下任巧玲,然后一下子抱住任巧玲。任巧玲被嚇了一跳,手懸起來,拿著棍子的那只手松開了,棍子掉在地上,砸到了鄭鐵柱的腳。鄭鐵柱“哎呦”一聲慘叫,松開了抱住任巧玲的手,蹲下來,坐在地上,抱著自己的腳。
任巧玲:“鐵柱,你,你,你沒事吧?”
鄭鐵柱:“哎呦,疼!疼,估計腳斷了!你說我遇到你怎么那么倒霉,先是胳臂后是腳,再下一次,是不是就要一命嗚呼了,哎呦!”
任巧玲趕緊蹲下來。
任巧玲:“啊?我看看,我看看。”去脫鄭鐵柱的鞋子。
這時候,鄭鐵柱裂開嘴笑了。
任巧玲打了鄭鐵柱一下:“你可真是討厭!”站起身,跑了。
鄭鐵柱站起身來,一瘸一拐地去追任巧玲。
52.巴清河 夜
田衛東站在巴清河岸,眺望遠方。
王丫丫從遠處走過來,站在田衛東的身后:“哥,你的事兒我聽說了,你別難過了。哥,你知道鵝卵是你怎么形成的嗎?就是長久的時間,磨盡棱角,最后圓滑。哥,你有最好的群眾基礎和良好的口碑,你要相信自己,無論到什么時候,我永遠跟隨你。”
田衛東轉過身來:“丫丫,你不要說了,你有能力,有前途,哥祝福你,咱們分手吧。我注定不能給你一生幸福。”
王丫丫聽了之后,瘋了一般地撕打田衛東,田衛東就站在原地,未掙脫,任憑王丫丫撕打。
王丫丫停止了撕打,抱緊了田衛東:“哥,今夜我是你的,我給你一切,夠了吧!”抱住田衛東。
田衛東:“丫丫,你知道,哥不是這樣的人。”
王丫丫哭著蹲下來,用手抱著自己的肩膀。
田衛東走到巴清河邊,拿起腳邊一塊土疙瘩,使勁兒往河里丟下。
53.田衛東家 夜
田伯勛坐在椅子上抽著旱煙,田衛東的母親坐在桌邊的凳子上,不停地嘆氣。
田衛東母親:“你說,這咋整啊?這以后日子咋過嘞?”
田伯勛嘆了一口氣,看了下桌子上跳躍著火光的煤油燈,沒有說話。
過了一會兒,田伯勛站了起來:“明天,我要去趟鄉里,我去為衛東討個說法去。”
田衛東母親:“你去?你去了不是更麻煩哩。孫大飛要去,衛東都攔下了,你就別跟著添亂了。”
田伯勛癱坐在椅子上,長嘆了一口氣。
田衛東母親:“本來啊,我這些日子就在想衛東的親事。他和丫丫,從小一起長大,這事兒不能老這么耽誤著。這下倒好,沒希望了。”
田伯勛:“我去找丫丫爹說去。”
田衛東母親:“丫丫爹,老王頭是個啥樣的人,你還不知道?嫌貧愛富的勢利眼兒,現在這個節骨眼兒去說這事,人家能同意?”
田伯勛:“哎,是我害的啊,這一切都賴我。”
田衛東母親流下淚來:“老頭子,你別這么說了。”嘆了一口氣,“年輕人的事兒讓他們自己解決去吧。要怪,只能怪咱們沒這個福氣,不能娶到丫丫這么好的兒媳婦兒,哎。”
田伯勛:“丫丫,是個好姑娘啊,哎。”把旱煙袋丟在了桌子上。
54.巴清河 晨
田衛東睜開眼睛,看了下灰蒙蒙的天空,回頭看了下坐在身邊的王丫丫,說:“丫丫,你快些回去吧,以后不要見我,你好好上班。”說完,田衛東站起身走了,頭也沒回。
背后的王丫丫大哭起來。
田衛東依然沒回頭。
55. 南坪村 日
王大嬸:“你聽說了嗎?田伯勛的兒子被撤職了,那個青年突擊隊被解散了。”
李大嬸:“知道,知道,這事兒能瞞得住嘛。要我說是活該,‘右派’子弟就應該打倒。”
趙大叔:“話不能這么說嘛,田伯勛他家的那小子,就是衛東那個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長得又精神,干起活兒來也不含糊,哎,可惜啊。”
劉大媽:“是啊,是啊。”
56.田衛東家 日
田衛東光著膀子,躺在床上。
田衛東母親把飯端進來,看了下桌子上,早飯并未動過。
田衛東母親:“衛東,你這都兩天沒吃飯了,再好的身體也不能這樣啊。”
田衛東:“娘,我吃不下。”
田衛東母親流下淚來:“娘知道你心里難過,可是這不是法子。你說,你想咋辦,人得活著,日子得過啊。以后的路,你想怎么走,你跟娘說,咱得走下去。”
田伯勛抽著旱煙,手上拿著東西,進來:“我給你帶來了幾本書,還有些報紙。”把東西放在了桌子上,“爹知道,你是個有能力、愛學習、聰明智慧的年輕人,爹從小就看好你。是爹耽誤了你的前程。孩子,憑著你的智慧,做點現實的選擇,男人就應該能屈能伸,想好,爹支持你。”
田衛東的父母離開了房間。
田衛東一個人躺在床上,看著房間的頂棚,流下淚來,攥緊了拳頭。
57.田衛東家 日
田衛東站在院里,對著正要出去的父母:“爹娘,我想好了,我要學裁縫。”
田衛東父親和母親都開心地笑了。
田衛東母親:“好好好,有個正經手藝就好,好啊。”
田衛東:“我要做就做這十里八村最好的裁縫師,趕明個兒,你們的衣裳,都是我來做。”
田衛東母親流下淚來:“好啊,娘等著你的新衣裳,只是縫紉機咋辦,上哪兒買去?他爹,你有啥法子?”
田伯勛對田衛東說:“明個兒叫你堂哥幫你,在家后宅地上挑成材的樹苗,刨十來棵,賣了吧。”
田衛東:“嗯。”
58.田衛東家宅地 日
田衛東和堂哥田躍進來到宅地的樹林里,從這頭轉到那頭,把之前栽的樹看了一遍。
田躍進:“兄弟,想開些,日子慢慢就會好的,哥信你哩。”
田衛東:“哥,我想好了,我以后會努力的。”
田躍進:“好,哥支持你,咱們刨樹吧。”
兄弟倆開始刨樹。
59.田衛東家宅地 晨
樹下,田衛東哥倆往架子車上裝樹苗。
大路上,王建國走過來:“躍進哥,衛東哥,我昨天打這兒經過就看到你倆在這兒刨樹,刨這些樹干啥使啊?”
田躍進和田衛東看到王建國過來,擦了下額頭上的汗。
田衛東:“拉到集市上去賣。”
王建國:“這是要干啥呀。”
田躍進:“你衛東哥要做裁縫師,賣樹要買縫紉機哩。”
“衛東哥,這是好事兒啊,我幫你。”王建國擼胳膊、挽袖子就把架子車拉在跟前兒。
三個人刨了10棵樹苗,王建國和田躍進裝車,田衛東拉車。
60.巴清河 晨
三人來到橋邊。
田衛東回過頭:“建國,你回去吧,我和我哥去就得了。”
田躍進:“是啊,建國,你回去吧,大熱天的。”
王建國:“那行,那我先回去了。”轉身回村兒了。
哥倆兒繼續拉著車子往前走。
田衛東:“哥,咱們去濟陽的集市吧。”
田躍進:“啊?就近的集市是營口,咋去濟陽嘞?”
田衛東:“營口的集市是近,可是集市小。咱們這些樹,得趕兩三個集市。濟陽的集市大,估計一個集市就賣完了。”
田躍進:“那成,走,趕快。”
哥倆兒繼續拉著車子往前走,速度明顯比剛才快了很多。
61.濟陽集市 日
集市上人來人往,大部分都是小商小販。田衛東哥倆兒把架子車放在街邊。
田躍進:“兄弟,哥知道你臉皮薄,哥來吆喝。”
田衛東:“誰說的。咱倆較量較量,看看誰的嗓門大。”
田躍進笑了起來:“好,咱來比試比試。”
哥倆兒一聲比一聲高的吆喝。
不斷地有人過來談價還價。
62.濟陽集市 日
田衛東和田躍進的攤兒上就剩下兩棵樹了。
這時候,來了一個老大娘:“小伙子,這樹苗,咋賣嘞?”
田躍進:“大娘,七塊錢一棵。”
老大娘:“你這兩棵,我都要了。能便宜點不?”
田衛東:“大娘,倆一起,13塊錢。”
老大娘:“倆一起,12塊,行不?”
田衛東停頓了下:“中,中。”
老大娘從褲子口袋里拿出一個塑料袋子來,把塑料袋打開了,里面卷著錢,從里面數出來12塊錢,遞給田衛東。
田衛東看著老大娘只身一人,問道:“大娘,您一個人來趕集市啊?”
老大娘:“是啊。”
田衛東:“大娘,這樹不好拿,我們兄弟倆給您送家去吧。”
老大娘:“太麻煩了,我家在濟陽那兒,很遠哩。我今個就是過來趕個集市,沒想買什么大件的東西,看到你們的樹苗這么好,不買可惜了的。”
田衛東:“大娘,您家在濟陽啊?順道兒。我們回去要路過,正好送您。”
老大娘:“啊?這話可怎么說得是,小伙子,謝謝你們。”
哥倆兒讓老大娘坐在架子車上,車上還有兩棵樹苗。
三人離開了集市。
63.田衛東家 夜
田衛東和田躍進在堂屋坐著。
田衛東母親把飯端進來,放在桌上:“你倆快吃飯吧,累了一天了。”
田衛東和田躍進狼吞虎咽地吃起來。
64.田衛東家院子 夜
田伯勛從外面回來,進院,看到架子車在院里,上面空空的。
進屋。
65.田衛東家 夜
田伯勛進屋,看見兄弟倆在吃飯,便問道:“咋樣啊今天,怎么個行情,賣了多少錢?”
田躍進:“叔兒,都賣完了。每棵樹大概賣了六七塊錢,整個集市下來,賣了得有六七十塊錢吧。”
田衛東:“爹,縫紉機得100來塊,剩下的錢咋辦?”
田伯勛:“哎,這樣,我明天去我學校會計處預借點工資,湊上應該就夠了。”
66.南坪村 晨
雞鳴,炊煙裊裊。
67.田衛東家 晨
院里,田衛東在做木匠活,做案桌。
有人敲院門:“衛東兄弟,開門吶。”
田衛東開門。
王建國和鄭鐵柱抬了一架縫紉機進院。
田伯勛從外面進來,看到田衛東在做條案,說:“我把工資預借了些,讓你舅整來了購物券,給你把縫紉機買來了。還有……”從懷里掏出來幾本書,“這是幾本兒裁剪類的書,你舅舅讓我給你捎回來的。”
鄭鐵柱:“勛叔兒,衛東可真有個讀書樣兒,干啥非要做裁縫吶,哎,可惜。”
王建國用手捅了捅鄭鐵柱,對田伯勛說:“裁縫挺好,裁縫挺好,衛東肯定是咱們鄉里一等一的裁縫師。”
大家伙兒哈哈大笑起來。
68.田衛東家 日
田衛東在條案子上忙活,把舊衣服拆了,按照它的制作流程,慢慢學習。
69.田衛東家 日
宋楚媛站在門外:“衛東叔。”
屋里回應:“楚媛嗎?”
70.田衛東家 日
宋楚媛進屋:“咦,叔,你咋知道是我?”
田衛東:“聽聲音就知道是你。我大你3歲,咱們從小一塊長大,你的聲音我再聽不出來,可還行?楚媛啊,大老遠,你咋來了?”
宋楚媛笑了:“哈哈,我就不能來啊?我看看秀才是怎么做裁縫的。”拿起案桌上的衣裳,左右看了下,“衛東叔,這些你改制的?”
田衛東:“是啊,咋了?”
宋楚媛:“不孬,不孬。趕明兒個你幫我整套衣裳唄。”
田衛東:“好。我這還沒學成呢,學成了給你做件。”
宋楚媛拿起條案上的幾本《紅廣播》雜志:“衛東叔,你也看這個雜志啊。我也看,我雖然是初中畢業,但是也喜歡看書。哎,對了,差點把正事給忘了,衛東叔,我這次來是給你當學徒的。”
田衛東詫異地看了宋楚媛一眼:“我說楚媛,我自己都是個半成品,你給我當學徒,豈不是屈才了。”
宋楚媛把《紅廣播》放在條案上:“衛東叔,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看你,咋這么瞧不上自個兒。我跟你說,這十里八村的,我就佩服你,要不是我伯勛爺爺被劃為‘右派’,你也不至于……”停頓了一下,“可是啊,咱們的青年突擊隊的名號打的響著哩。我跟姥姥說了,跟你當學徒,一來呢,是幫襯著你,二來呢,我自己學個一技之長,也挺好啊。衛東叔,你不打算留下個徒弟嗎?”
田衛東笑了。
71.田衛東家 日
田躍進進了院子:“衛東,衛東,我借你的家鋤頭。”
宋楚媛從屋里出來:“躍進叔,咋了呀?”
田躍進看到宋楚媛在這兒,驚訝地看了下:“楚媛,你咋在這兒嘞?”
宋楚媛:“我來給衛東叔兒當學徒,哈哈。”
田躍進:“哦,好啊。”轉身離開了院子。
宋楚媛在后面喊他:“躍進叔兒,躍進叔兒,你不要鋤頭了?”
田躍進沒聽到,一直走出了院門。
72.公路 日
字幕:兩年之后。
筆直的公路,公路兩旁都是綠蔭蔭的樹。
郵遞員騎著自行車從公路右側走過。
73.白沙鄉鄉政府大院 日
郵遞員騎著自行車進了院子,他來到王丫丫辦公室的門口:“王丫丫同志,你的郵件。”
74.鄉政府辦公室 日
王丫丫在寫東西,聽見喊聲,從辦公桌里側走出來。
75.鄉政府大院 日
王丫丫從郵遞員手里接過郵件。
郵遞員:“王丫丫同志啊,這兩年你都在訂閱這個雜志,上面有你寫的文章嗎?”
王丫丫笑了下:“沒有,里面有一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寫的文章。”把兩本雜志拿在手里,上面寫著刊物的名字《紅廣播》。
王丫丫:“謝謝你了。”
郵遞員:“不客氣。”騎著車子走了。
76.鄉政府辦公室 日
王丫丫打開雜志的目錄,看到一篇文章,馬上翻到那一頁,文章的題目是《青梅沒有竹馬》,作者是默金。
王丫丫看著看著,合上了刊物,閉上眼睛想了片刻,馬上拿起桌旁邊的剪刀,把文章剪下來。然后從抽屜里拿出一本大大厚厚的一個本子,又拿出膠水。把裁剪的文章貼了上去。王丫丫把大厚本從前往后看,所有的文章都是默金寫的。
王丫丫撫摸這本子,把本子貼在胸口,閉上眼睛,流下淚來。
77.南坪村 日
趙大媽:“老田家的衛東啊,手藝還真是不一樣哩,你看我這身衣裳,多好看呢。”
“我看看。”李大嬸用手摸摸布料,看看款式,“嘖嘖嘖,不孬,不孬。”
劉大媽:“要不改天,咱們也去看看,讓衛東給俺也整件好看的衣裳。”
大家伙兒笑了起來。
78.田衛東家 日
天下著小雨。
田衛東在屋里條案上剪裁布料,宋楚媛幫忙把碎布頭整理下。
宋楚媛:“衛東叔,咱們家的衣裳真的是越做越好了,這鄉里誰家需要做新衣裳的都來咱這兒了。衛東叔,你很優秀,嘻嘻。”
田衛東看了一下宋楚媛:“就你嘴甜,你也有功。”
宋楚媛深深地打了個哈欠。
田衛東:“楚媛,你咋了?我看著你咋這么困的樣子?”
宋楚媛:“能不困嘛,昨天俺妗子家的母豬生崽兒了,我跟著一起忙活大半夜,昨天晚上沒睡好。”
田衛東:“你咋不早說嘞,你去休息一會兒吧,我一個人就行。去隔壁我房間,你在那兒睡一會兒吧。”
宋楚媛:“行,那我就不客氣了,真的是困死我了。”
79.田衛東房間 日
宋楚媛進來,躺在床上就要睡覺,覺得枕頭底下硌得慌,抬開了枕頭,什么也沒有,但是看到有東西凸起來一部分。
宋楚媛掀開褥子,看到一個長方形的小盒子,就隨手把小盒子拿出來放在桌子上。結果沒放牢,盒子從桌子上掉下來了。盒子蓋摔開了,里面的東西撒了出來。
盒子里面是好幾張紅紙,宋楚媛打開紅紙,上面都是小學的時候貼在宣傳欄里面田衛東和王丫丫表揚報,還有兩年前田衛東和王丫丫被評為勞模胸前佩戴的大紅花,還有一張王丫丫的照片。
宋楚媛看著這些東西,流出淚來。
這時候,外面傳來王丫丫的聲音:“楚媛,你叔在家沒?”
宋楚媛擦了擦眼淚,趕緊收拾盒子,把盒子裝好,還放在了褥子下面。
收拾完了之后,宋楚媛還看了下床鋪,離開了房間。
80.田衛東家 日
宋楚媛走出房門,看到王丫丫穿著雨衣,走進院門。
宋楚媛:“姑,你咋來了,快屋里坐吧,下著雨嘞。”
81.田衛東家 日
宋楚媛和王丫丫一起進了堂屋。
宋楚媛:“姑,你那么忙,村里鄉里的,咋稀罕來這兒了?”
王丫丫進了屋,把雨衣脫下來,掛在門沿兒上,然后坐在凳子上。
田衛東:“丫丫,你要做衣裳啊?”
宋楚媛:“衛東叔,丫丫姑姑穿的全是成衣名牌,咱們做的是給普通老百姓穿的,姑姑的衣服,咱們做不來的,嘻嘻。”
王丫丫:“楚媛,跟你叔兒學縫紉,還學會口才了?這么嘴尖舌快。咦?楚媛,你這是咋了,眼睛咋這么紅嘞?”
宋楚媛趕緊擦了擦眼睛:“沒咋,沒咋,就是昨天沒睡好,這會兒正犯困嘞。”
田衛東:“丫丫,光臨寒舍,想必是有事兒吧。”
王丫丫:“哥,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從挎包里掏出幾本小書:“衛東哥,這是幾本《紅廣播》雜志,你應該熟悉,這里有你發表的文章。”
田衛東正要去接手,卻被宋楚媛搶了去。
宋楚媛:“姑,你騙人,哪篇文章是衛東叔寫的?這《紅廣播》我也看過,沒見過俺叔的名字啊?”
王丫丫:“楚媛,了解你叔的人是我,最懂你叔的人還是我。”
宋楚媛生氣了,撅起嘴:“姑姑,兩年多了,你跟俺叔見過幾次面?說過幾次話?我看你是當了官,不認識俺叔了。我聽說你倆當年還海誓山盟的愛過,后來你直上青云,俺叔下來了,你就不要俺叔,你靠譜嗎?”
田衛東:“楚媛,你閉嘴。哪有你小孩子的事兒,好好干你的活,無教養。”
宋楚媛哭了:“叔,我就是看不慣這么不負責任的人。”
田衛東:“你要是還當我是你叔,你就別說了。”
宋楚媛站起身來:“好,我不說,我走,行了吧。”跑出門。
王丫丫站起身來:“楚媛,楚媛,你回來。”
田衛東:“她就是這脾氣,小孩子似的。現在外面雨也停了,沒事,別擔心她。”
王丫丫:“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書中那個叫默金的作者就是你,默金是你的筆名。”
田衛東很驚訝,看著王丫丫:“你咋知道嘞?”
王丫丫:“你是和我分手之后才用的這個名字。其實,我當初并不知道你寫了稿子,也不知道默金是你。當我無意間讀到你的第一篇文章時,我就吃驚地斷言,此文一定出自你的筆下。因為我太了解你了,文如其人,你慣用的語言,句子的編排,文中能感受得到你這幾年深沉落魄的心情。我了解你,你的筆名,默金,沉默的金子之意,我是知道的。”
田衛東:“丫丫,我……”
王丫丫:“衛東哥,今個兒晚上,老時間老地點,我有事兒跟你商量。”拿起雨衣便走出房門。
82.南坪村 日
宋楚媛一路哭著一路跑著。
田躍進正出家門,看到宋楚媛從自家門口跑過去,問道:“楚媛,楚媛,你干啥去?”
宋楚媛自顧自地往前跑,田躍進在后面跟著。
宋楚媛來到巴清河邊,看著巴清河的河水很急。宋楚媛擦了擦眼淚,回過身來,剛下完雨,腳下的地很濕。宋楚媛腳下一滑,一下子掉到了河里。
剛剛跟上來的田躍進看到楚媛跌落在河里了,大叫了一聲:“楚媛!”大步跑過去,跳進河里,游到宋楚媛身邊,右手抱起宋楚媛,左手打著水,往岸邊游。
水很急,田躍進用力游著,宋楚媛抓住河邊的稻草根部,慢慢拖著身體,爬上了岸。田躍進也抓住草根正準備上岸,草根已經松動了,田躍進抓了空,田躍進再次滑到河里。
宋楚媛在岸上哭,邊哭邊喊:“躍進叔!躍進叔!”
田躍進被河水往前沖,沖到了巴清河橋,田躍進一把抓住橋欄桿。
宋楚媛趕緊跑過去,趴在橋上,把手伸向了田躍進:“躍進叔,拉住我的手,我拉你上來。”
田躍進一只手拉住宋楚媛的手,另一只手抓住橋邊,兩只腳使勁兒往上躥,這才上來。
兩個人癱坐在橋上。
宋楚媛一直在哭:“躍進叔,是我不好,是我害的你。”
田躍進往宋楚媛身邊靠了靠,擦了擦宋楚媛的眼淚,看到宋楚媛的身體在抖,便說:“沒事,你沒事就好。咱們趕緊回去,這秋后的河水可涼哩,別感冒了。”拉宋楚媛起來。
宋楚媛站起身來:“謝謝躍進叔。”她的聲音越來越小,暈倒在田躍進肩膀上。
田躍進:“楚媛,楚媛。”用手貼了一下宋楚媛的額頭,“好燙!楚媛,咱們現在就去醫務室。”抱起宋楚媛往村兒里跑。
83.老根叔家醫務室 日
田躍進抱著宋楚媛進來:“根叔,楚媛發燒了,您快給看看吧。”
老根兒走過來,探了下宋楚媛的額頭,又看了下他倆的身上:“你倆咋了這是?咋渾身濕透?”
田躍進:“掉巴清河里了,秋水涼,她被凍著了。”
老根兒沖著側室喊:“他嬸兒,你來,你來。”
老根嬸子從里面走了出來:“咋了?”看到倆人渾身濕漉漉的,“這是咋了?孩子。”
老根兒看了下老根兒嬸兒:“你快找幾件你的干凈衣裳,給楚媛孩子換上。躍進,這邊交給我和你嬸兒了,你趕緊回家換身衣裳再來,我看你也是冷得發抖。”
田躍進:“好嘞,那我先把楚媛放在這兒了。”
老根兒嬸兒:“躍進,你把她抱到我房間里來,我給她換衣裳。”
田躍進抱著宋楚媛進了老根兒嬸兒的側室,出來時說:“叔,嬸兒,我回家了,一會兒再來。”
老根叔:“好。”
田躍進出了房間。
根叔兒:“哎,又是一對兒有情人啊。”
老根兒嬸兒:“哎,只可惜,這女娃娃心不在躍進身上啊。行了,你快出去吧,我給孩子換衣裳。換完衣裳,你再給打吊瓶。”
老根叔兒也出去了。
84.巴清河 夜
田衛東來到河邊,仰望星空。
田衛東畫外音:“巴清河,我久違的圣地,這里埋葬著我的夢,刻下了切膚的記憶。從家到這里,只有百十來米,可是這兩年多來,卻未踏進半步。”
巴清河河水靜靜流淌著。
王丫丫走了過來。
兩人相見,靜默了一會兒。
王丫丫先打破了尷尬的局面,大方地挽起田衛東的胳臂:“哥,兩三年了,沒生我的氣吧?這兩年多的時間,我也難熬,常常半夜里哭醒。是我在有意躲著你,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讓你的自尊提升,你才能背水一戰,起死回生。你是一個成功者,從哪里跌倒就能才哪里爬起來。你找到了你的立足點,這就是能者的表現。現在的你,口碑不錯,無人不夸你手藝好,樂于助人,這不是表現出來了嘛。”
田衛東一直靜靜地聽著,兩人在河邊溜達著。
王丫丫:“去年,看到你寫的第一篇文章《夜間的槍聲》的時候,你知道我的心情嗎?我簡直太激動了。我把你寫的那些文章向我的同事、領導推薦,無人不道其好。我知道默金是你,從那以后,每期我都要看一下有沒有你的文章。但凡有你的作品,我都收藏了。哥,我想問你件事兒。”
田衛東:“什么事兒?你說吧。”
王丫丫:“你都24了,為啥不定親呢?”
田衛東:“丫丫,你有對象了嗎?”
王丫丫:“應該說是莫須有。”
田衛東:“什么意思?”
王丫丫:“就是有了,在我心里。沒有,就是沒有領證。沒有領證的話,從法律上來講,就是不屬于我的。我娘也常常嘮叨我,說我挑三揀四的。其實不然,雖然有幾個條件不錯的,各個方面也是無可挑剔,就是喜歡不起來。有時候,我真的很擔心我會被別人娶了去。說到底,我心里還是只有你,哥,你現在能接受我嗎?”
田衛東:“不可以。我也正好要跟你說一下,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找個合適的人家,嫁了吧。我們倆是不可能的。”
王丫丫委屈地想哭:“為啥呀?”
田衛東:“你看,我一個大老爺們,在家做家務,奶孩子。你去上班,開會,應酬。我想過,與其以后情不相向,不如就此罷了。此舉,不是不愛,而是對愛的負責,因為愛你,才要離開你。”
王丫丫:“你口是心非!你這些違心的話說給別人信,說給我,我不信!你是怕你家庭成分對吧,勛叔兒是‘右派’分子,你怕連累我對吧?就你也算老爺們兒嗎,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你就是慫人一個。”
田衛東:“丫丫,你別說了。”
王丫丫:“我就要說,你聽說我,我不怕,我真的不怕這些。我保證能做一個好妻子。三條腿的蛤蟆找不到,兩條腿的男人有的是,這么多年了,我為什么非你不嫁,你揣著明白裝糊涂,是吧?”
田衛東:“丫丫,兩年前,是我拒絕了你,我改變了我的生活理念,決定不再為仕途奔波,不想倒在潮頭上,做無謂的犧牲品。我只想做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用自己的一點知識和手藝,養家糊口,就夠了。你不是說我沒對象嗎?我告訴你,宋楚媛,就是我理想的一個。”
王丫丫瘋了一般,朝著田衛東吼道:“你胡說!你覺得我會信你的屁話!你能做出這種事兒嗎?你是她師父,輩分上叫你叔,你下得了手?”
田衛東:“我和宋楚媛并非近親,她是鄰村的姑娘。還有,輩分和年齡是排除愛的理由嗎?不合法嗎?”
王丫丫:“你,你不要自欺欺人了!我知道你心里還愛著我,我了解你的德行,就因為你有一顆干凈的心。我知道你拿楚媛當擋箭牌。我要的就是你,只要你不結婚,我就不會放棄。”
田衛東不語。
王丫丫平靜了下情緒:“還有件事兒,是我必須要給你傳達的。鄉黨委研究決定,由分團委和婦聯辦聯合主辦的周刊《致富報》,準備讓你擔任主編,我們婦聯是半個主辦方,我又是婦聯主任。哥,我現在鄭重地請你出來幫我,支持我的工作,好嗎?”
田衛東:“丫丫,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沒有官僚主義,我也知道你懂我,只是我是一個沉淪者、失敗者,有嚴重的‘右派’色彩,你就讓我做一個自由職業者吧,別再讓我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了,好嗎?”
王丫丫:“悲哀,真是悲哀。我原以為我心中的那個田衛東是很了不起的,不成想卻只有一戰之能,輸了就一蹶不振。18歲的你,真的一去不復返了。你成不了斗士,更成不了英烈,你就是個懦夫,你是逃兵,你真的讓我看不起。”
王丫丫揚長而去,留下田衛東一個人。
85.田衛東房間 夜
田衛東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耳邊一直在回響著王丫丫的那幾句話“18歲的你,真的一去不復返了。你成不了斗士,更成不了英烈,你就是個懦夫,你是逃兵,你真的讓我看不起。”
田衛東房間的桌子上放著盞煤油燈,燈捻處在火中一閃一閃,微弱的光映在田衛東的臉上,忽明忽暗。
86.田衛東家 晨
王丫丫進院,田衛東正在院里晾布匹。
王丫丫:“說吧,是做戰死的烈士,還是做脫逃的士兵,要么跟我去鄉里,要么閉門不出,老死不相往來。一輩子栽幾個跟頭,又能咋地,至少我是你的朋友,這輩子就是玩,我也會陪你玩到最后。別娘們唧唧的,給個痛快話。”
田衛東點了點頭。
王丫丫的臉露出了笑容。
87.宋楚媛家門口 黃昏
宋楚媛家的狗趴在門沿上,看著外面。
從外面過來另外一只狗,臥在了它的旁邊,兩只狗依偎在一起。
88.宋楚媛家 黃昏
宋楚媛躺在床上蓋著被子,額頭上敷著疊好的白毛巾,還在昏迷,田躍進守在一旁。
宋楚媛眼睛動了動,睜開眼睛。
田躍進:“楚媛,你醒了。”
宋楚媛:“我怎么在家,我……噢,對了,我想起來了,我掉河里了。躍進叔,你救了我。你沒事吧?”
田躍進:“楚媛,我沒事。你昏迷了快一天一夜了,你姥姥和你姥爺都下地干活兒了,他們讓我來照顧你。”
宋楚媛:“嗯,謝謝你。”
田躍進笑了。
89.白沙鄉鄉政府大院 黃昏
田衛東和王丫丫兩個人騎著自行車來到門口。
鄉黨委丁書記見到王丫丫進來,忙問:“王丫丫同志,你把默金帶來了嗎?”
王丫丫指了一下身后的田衛東:“丁書記,人我給你帶來了,就是他。這是我發小,默金,本名是田衛東。”
田衛東和丁書記握了手。
丁書記:“嗯,小伙子長得挺精神的嘛。你的事兒我聽王丫丫同志說了,來辦公室談吧。”
丁書記、田衛東和王丫丫一起進了辦公室。
90.白沙鄉鄉政府招待所 夜
餐廳的大堂里圓圓的桌前坐了十多個人,都是鄉政府的工作人員,大家伙兒有說有笑。
丁書記站起身來:“今天的宴會有兩個意思,一是《致富報》要辦了,縣里很是重視,所以團委和婦聯的任務很重啊。而且,既然辦了,就必須要辦好,辦出質量,讓它確確實實能喚起老百姓致富的勁頭兒,要幫老百姓找路子,想點子,抓好典型,以點帶面。但不能吹牛。讓老百姓愿意看,愿意讀,要有吸引力,老百姓的支持就是動力。資料來源由團委和婦聯主辦征稿,鄉政府所有工作人員,人人有責,個個有份。至于撰稿,默金,你是主編。你是咱們鄉優秀的青年,你們青年突擊隊的事兒我也聽說了,你父親是咱們鄉鎮的老師,你的文章,我看過,有個性,機極具表現力,邏輯性也比較強。相信你,能把咱們的《致富報》辦好。”舉起酒杯。
丁書記:“來吧,同志們,為了咱們的《致富報》早出刊物,干杯。”
落杯后,王丫丫為全體就坐的斟滿了酒。
丁書記看了下田衛東和王丫丫:“今天宴席的第二重意思,今天就讓我當一回土皇上,賜婚王丫丫和默金。”
田衛東吃驚地看了一下丁書記。
丁書記:“默金,你別意外,兩年前的事情,我都聽說了,其實當年在擬定的名單里就有你,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吧,不說這個了。這兩年來,王丫丫一直在等你,為你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之前也問過王丫丫,她就是非你不嫁。今天是有點唐突,有點包辦婚姻,甚至有點官僚主義,未經雙方二老同意,不過,我想他們也應該會同意的。我這也是頭一回做媒,今天在座的領導都是證婚人,希望你們幸福,多為鄉里做貢獻,來,干杯。”
田衛東看到王丫丫眼睛里閃閃發亮,兩行熱淚流下,對王丫丫點了下頭:“謝謝,謝謝丁書記、各位領導還有丫丫。”
在大家伙兒的歡聲笑語中,田衛東連喝了幾杯。
91.宋楚媛家 日
宋楚媛躺在床上。
田躍進端著湯藥進來:“楚媛,來,把藥喝了。”
宋楚媛:“我不想喝,太苦了。”
田躍進:“苦也得喝,良藥苦口利于病。”
宋楚媛看著田躍進:“好吧,我喝,我喝。”
宋楚媛接過藥碗,手沒端穩,田躍進趕緊接住,差點撒了。
田躍進:“好家伙,得虧我及時,要不然不就撒到床上了!我來喂你吧。”
宋楚媛點了點頭。
田躍進端著藥碗,用湯勺喂宋楚媛喝藥。
宋楚媛喝藥的時候,臉很紅。
92.白沙鄉鄉政府招待所 日
田衛東酒醒來,發現自己躺在旅館的客房里,外衣已被脫了,白色的背心穿在身上。
王丫丫坐在桌前看書,聽到田衛東醒來的聲音,走到床邊:“哥,你終于醒了。餓不餓?想吃點什么,去食堂給你帶過來。還有,你去衛生間洗個澡,一身酒氣。”
田衛東:“丫丫,沒事,我不餓,我先去洗澡。”
王丫丫盯著田衛東一直看著。
田衛東沒動。
王丫丫:“怎么,你還害羞了?別不好意思了,脫掉衣服,用浴巾裹著便是。”背過去,走到桌前看書。
田衛東進了衛生間。
93.白沙鄉鄉政府招待所 日
田衛東仍躺在床上,他已經換上衣服。
衛生間里傳來王丫丫的聲音:“哥,把你的那件浴巾遞過來。”把衛生間的門閃開半邊。
田衛東別過臉遞過去浴巾。
王丫丫笑了起來:“我有那么可怕嗎?你都不敢看我?”
田衛東這才回過頭來看了一眼王丫丫,眼前站著王丫丫側著的裸體。
田衛東看直了眼,喉結處動了動,又愣了一下神,說:“那個,丫丫,給你浴巾。”
田衛東迅速轉過了腦袋,緊張地躺回床上。
過了一會兒,王丫丫裹著浴巾從衛生間出來,坐在床邊:“視我體也,夫也。田衛東,今后,我就是你的了。明天,咱們回村,告知爹娘,然后咱們找個時間把證領了,你看行嗎?”
田衛東:“好,都聽你的。”
王丫丫躺在田衛東身邊,田衛東繃著臉,不敢碰身邊的王丫丫。
王丫丫看到田衛東這副樣子,不高興地說:“我有那么可怕嗎?你都不敢看我?”
田衛東嘴角笑了笑,撲了上去,田衛東吻了下王丫丫。
王丫丫笑了:“原來你也是個爺們兒,六年了,我一直懷疑你有沒有男人的功能。好啦,演習結束,真槍實彈的話,留到新婚之夜吧,不然我算什么新娘。”從床上起來,“我去食堂打飯。”說完出去了。
躺在床上的田衛東傻傻地看著王丫丫出了門。
94.鄉政府丁書記辦公室 日
字幕:兩個月后。
田衛東和王丫丫站在了辦公桌前。
丁書記:“好啊,哈哈。果然不負眾望,這第一期刊物出版了,題目也響亮,嗯,《大步流星奔小康》。我剛看了下內容,不錯,印發到鄉政府各個單位和部門吧,還有各個村組、生產隊。對了,這都兩個月了,咋又沒動靜了,你倆準備啥時候結婚啊?”
田衛東咧開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田衛東:“正準備跟您說呢,下個月初八。”
丁書記:“好啊,你倆這杯喜酒啊,我是喝定了。”
95.田衛東家 日
小院張燈結彩,裝飾一新,紅綢子和紅燈籠掛滿了院子,宋楚媛和田躍進忙著貼紅雙喜。
這時候,一群小姑娘圍擁王丫丫到門口,帶頭的姑娘嚷嚷起來。
任巧玲:“新郎官呢,新郎官,給我出來,有了新娘,就把我們都給忘了是不是!”
青年突擊隊鐵姑娘班的全體隊員擁著王丫丫沖到了院子。
田衛東對姑娘們一邊發喜糖,一邊道謝。
任巧玲吃著喜糖,來到田躍進和宋楚媛身后,對著人群說話:“今天衛東和丫丫大婚。我說,躍進哥和楚媛,你倆,啥時候辦事啊,啊?”
人群中開始喧鬧起來。
“對呀,你倆啥時候辦事啊?”
“結婚的時候,可不能忘了哥幾個哈!”
田躍進和宋楚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田躍進看了下鄭鐵柱:“各位,我和楚媛結婚的時候,肯定邀請各位喝喜酒。不過,我和楚媛不重要,我說鐵柱兄弟,你和巧玲的事兒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伙兒說是不是啊?”
大家顯得十分意外。
“啊?什么?”
“他倆啥時候走到一起的?”
王建國用手戳了戳身邊的鄭鐵柱:“可以呀,兄弟,你倆隱藏的夠深的啊!”
鄭鐵柱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走到任巧玲面前,牽起任巧玲的手,舉起來:“今年過年,結婚!”
大家伙兒開始起哄,鼓掌。
任巧玲:“等會兒,我都快忘了正事了。今天是衛東哥和丫丫姐大婚,躍進哥,你老是偷換什么話題。”
大家伙兒哈哈大笑起來。
任巧玲咳了咳,清了清嗓子:“有請青年突擊隊隊長田衛東和鐵姑娘班班長王丫丫,門外迎客,姑娘們隨同前往。”
大家伙兒簇擁著新郎新娘來到院門外。
96.田衛東家門口 日
院門外,一隊男一隊女站在門外兩側,排列整齊,男列中站在最后一個的一人舉起了“青年突擊隊”的紅旗。
任巧玲:“青年突擊隊36名隊員,集合完畢,同志們,勞工號子響起來呦。”
在大家伙兒的歌聲中,田衛東和王丫丫一起流下淚來。
歌聲完畢之后。
任巧玲:“有請新郎新娘移步巴清河,鑼鼓隊,起行了。”
97.巴清河邊 日
田衛東和王丫丫被大家伙兒帶到這里。
王丫丫被姐妹們圍了起來,一會兒,散開后,王丫丫穿上了姐妹們為她準備的婚紗。
一切準備就緒后,新郎新娘上了大家伙兒為他們準備的送親船。
勞工號子再次響起來,新郎新娘在歌聲中,伴著巴清河的流水,劃動了船槳……
98.城市 日外
字幕:2001年。
整齊的樓房,車水馬龍的大街,川流不息的車輛。
街邊懸掛巨幅條幅:熱烈祝賀北京申奧成功!
99.居民小區 日
樓下幾個老太太在練習太極劍。
在隊伍前的一個老太太,收起劍:“得了,咱今個兒,就先練到這兒吧。”我們看得出,這是年老的王丫丫。
其他老太太也收起了劍,散了。
王丫丫拿著劍上了樓。
100.田衛東家 晨
王丫丫進屋,把劍放在門后,看到田衛東在客廳里看相框里的照片。
王丫丫:“你啊,一天天的,就看個沒完。”
田衛東:“這些照片,都是回憶啊。哎,你看,鐵柱那時候多年輕啊,現在這病那病的,哎。”
王丫丫:“行了,你慢慢看吧。我去買菜了,你想吃什么菜,我買回來。”
田衛東:“惦記你燒的鯽魚湯了。”
王丫丫:“好,我去買去。對了,周末回去看看吧,我想念巴清河了。”
田衛東:“我也是,想回去了。”
王丫丫從門后拿了菜籃子走了。
101.菜市場 晨
王丫丫買了蘿卜、白菜、五花肉,來到生鮮區一個魚攤兒前,看了下池子里的魚:“有鯽魚嗎?”
魚販:“大姐,今天沒鯽魚了。昨天因為下雨,進城區的路被沖斷了。要是買的話,得去東城區菜市場買,那兒才有呢。”
王丫丫看了看其他攤兒的魚池子:“好吧,謝謝你了。”
102.公交車站 晨
公交車進站,公交車的車頭上顯示著“前往東城區方向”。
王丫丫上了公交車。
103.東城區菜市場 晨
王丫丫拎著一個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裝著水和兩條鯽魚,往菜市場外面走。
王丫丫走到街邊,突然后面過來一輛車,把王丫丫撞倒在地。
血流了很多,塑料袋里面的鯽魚摔了出來,魚在地上一跳一跳。
這時候,天下起雨來。
104.南坪村巴清河 日
字幕:2014年。
田衛東抱著王丫丫的遺像站在河邊,河水很安靜,河邊的野花,開得很好……
(劇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