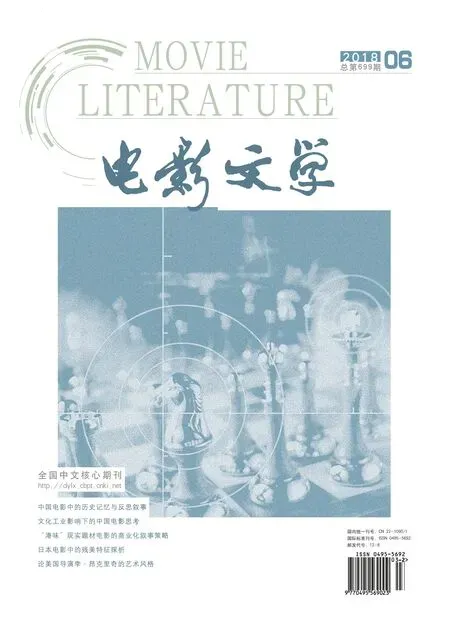電影《梵高:畫語人生》的藝術美學評析
楊 寧 楊云飛
(1.東北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2.吉林動畫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當代商業電影的發展促使以視覺傳達為目標的美學文化掌握了話語權,商業大片的視覺轟炸令觀眾疲憊不堪,內容空洞的商業電影令觀眾逐漸開始關注人文性較強的紀錄片。紀錄片可以說是與電影藝術同步誕生的,早在1895年路易·盧米埃爾創作的世界上第一部電影《工廠大門》,就是采用偷拍的方式創作的紀錄片,記錄下了自然的生活化的真實。當代紀錄片已有了多元化的表現方式,而非僅有簡單的、如盧米埃爾“偷拍”式的客觀記錄形式。搬演是紀錄片的創作表現方式之一,由于這種方式的演繹色彩而并不被人們廣泛推崇,常常被認為是破壞了紀錄片的“真實”。然而,對于傳記類紀錄片來說,搬演雖然對紀錄片真實性的破壞使其飽受詬病,卻可以通過演員的表演令影片更生動,消除紀錄片的“沉悶”之感,還原不可能重現的歷史與事實。紀錄片《梵高:畫語人生》就是在搬演的基礎上,在鏡頭剪輯、畫面構圖等鏡頭語言方面巧妙地利用了故事片的表現方式,生成了不僅限于“真實美學”的多重藝術美學特征,讓觀眾走進瘋狂天才文森特·威廉·梵高的傳奇人生。
一、真實與搬演的美學兩難
電影藝術創作是從簡單的、單純的記錄開始的,即我們完全可以將紀錄片的誕生看作是電影藝術的開端,如標志著電影藝術誕生的《工廠大門》和《火車進站》都是紀錄片性質的影像記錄。“記錄”與“真實”是紀錄片的代名詞,還原事實的真相,記錄事件發生的過程是紀錄片的首要功能,如《工廠大門》正是路易·盧米埃爾用偷拍的方式記錄下的內容。紀錄片記錄真實也創造“真實”,永遠在真實的記錄中尋找情感與藝術的張力。對于紀錄片的創作標準與美學表達方向,自20世紀50年代末期的紀錄片運動就開始爭論不休,電影人分成觀點截然相反的兩個派別——真實電影派和直接電影派。“真實電影派”認為紀錄片導演可以參與到紀錄片的敘事過程當中,將其思想與觀點融入其中,進而為了達到一定的敘事效果而做出一定的“演繹”;“直接電影派”則認為紀錄片應當保持客觀的觀察視角,導演的思想觀點要與紀錄片的敘事劃清界限,讓事件按照自身發展過程自然被記錄下來,不應當為了導演個人觀點的表達而犧牲掉紀錄片的真實美學,剝奪觀眾從真實中獲得審美體驗的權利。
然而,根據紀錄片不同的內容類別,我們發現旁觀鏡頭與客觀視角是很難在紀錄片的創作中實現的,紀錄片在創作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會加入創作者的思想和觀點。尤其是在紀錄片搬演的過程當中,導演的觀點和演員的觀點都會影響到紀錄片的敘事表達。長期以來,搬演并不被紀錄片導演廣泛應用,甚至始終是被極端排斥的創作方式,因為搬演會嚴重影響到紀錄片的核心美學——真實,僅有在再現歷史故事遇到障礙時,為了能夠讓影片更生動,觀眾理解更容易,才會在尊重歷史與事實的基礎上讓演員搬演。
荷蘭后印象派畫家文森特·梵高是紀錄片創作的絕佳對象,他的短暫、精彩且瘋狂的一生有著太多值得記錄和挖掘的故事內容,關于文森特·梵高的傳奇人生至今都沒有一個被完全認可的說法,甚至有人認為文森特·梵高過于瘋狂,我們是無法去真正理解一個瘋子究竟在想些什么的。文森特·梵高的故事在民間流傳的過程中難免會失真,然而他留下來的美術作品,以及他寫給弟弟提奧的大量信件卻是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2010年,導演安得烈·赫頓用搬演的形式再現了文森特·梵高的傳奇人生,拍攝了紀錄片《梵高:畫語人生》,以梵高留在世上的902封信,還有他的眾多素描手稿和繪畫作品為基礎,用梵高在信中自己說過的話作為演員的臺詞,重現梵高瘋狂的傳奇人生。在此之前就已經有多部關于文森特·梵高的傳記紀錄片,有些專門針對梵高在與高更爭吵后的割耳之謎,還有專門針對梵高的油畫作品進行研究的紀錄片,等等。然而,在導演安得烈·赫頓執導的這部《梵高:畫語人生》當中,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飾演的梵高極具銀幕魅力和感染力,觀眾能夠透過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極具個人魅力的表演感受到梵高在與弟弟提奧的書信往來中,寫下的自己當時的心境和情感,梵高的個人形象在本尼迪克特的搬演中從未如此立體而豐滿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二、人物與鏡頭的對話互動
搬演的弊端顯而易見,由于其中的演繹成分,即便是在尊重事實的前提下,也無法消除對于紀錄片真實性的消解。紀錄片《梵高:畫語人生》正是因為基于文森特·梵高的902封信和大量畫作提取的故事內容,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尋找演員搬演,而是每位演員都是獨立演出,片中沒有演員和演員之間的對話存在,也沒有演員之間的表演互動,演員的臺詞都是來自于文森特·梵高的書信內容。于是,我們看到影片人物,尤其是文森特·梵高的自言自語、與鏡頭對話,甚至與空間之外的對象隔空對話。這些完全符合人物之間的書信溝通背景,只不過他們將彼此的書信內容口述出來,并演繹了當時寫信時候的情境。因此,在紀錄片《梵高:畫語人生》當中,鏡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已經不僅僅是記錄的功能,在記錄的過程中產生了無意識,甚至成為人物的一面鏡子。
通常來說,在電影拍攝過程中,演員是要忽略鏡頭的存在的,只有極少數的情況需要演員直視鏡頭,因為演員如果目光跟鏡頭接觸,觀眾旁觀者的身份就會被消解,在演員注視鏡頭的過程當中與觀眾產生互動和聯系,演員對鏡頭的關注會立刻讓觀眾從故事氛圍中跳脫出來,意識到他們是在演戲。而在影片《梵高:畫語人生》當中,演員與鏡頭的對話、互動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符合他們彼此之間只存在書信聯系;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讓觀眾否定其演繹的成分,從搬演的狀態中跳脫出來,產生一種真實記錄的錯覺。
因此,演員與鏡頭之間架設了一種互動關系,但是這種互動關系呈現出一種鏡像關系。這種搬演方式消解了演員在彼此互動過程中的戲劇化的演繹,制造了一種疏離感,形成了一種私密視角,從另一種角度制造了紀實感與真實感。
同時,片中人物與鏡頭的互動也突出強調了人物的個性和形象,尤其是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飾演的梵高,他的孤獨、抑郁、狂躁、傲慢、熱情、感性和瘋狂統統呈現在觀眾面前。影片將梵高和弟弟提奧之間的信件,從平面轉向立體,梵高面對鏡頭獨白的內容也就是他寫給提奧的書信內容。人們從梵高朗讀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他寫信時候的表情和情緒,可以看到當時的梵高是一種怎樣的精神狀態,梵高流轉在不同的場景環境當中,觀眾在不知不覺當中也與梵高一同經歷了他的命運變遷過程。可以說,梵高寫給提奧的每封信背后都代表了他不同人生階段以及經歷的不同事件,平面的書信轉化為立體的影像的同時,觀眾對梵高本人的人生也有了一個更加鮮活的印象。于是,在不同的年紀、不同的人生階段,梵高為何會有那樣的思想變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拿起畫筆作畫,每幅畫都有著什么樣的創作背景一目了然。換種角度來看,影片《梵高:畫語人生》的搬演方式幫助觀眾建立了一種別樣的真實,讓神秘的梵高看起來與觀眾更加靠近,他的個人形象也有了溫度。
三、鏡頭畫面中的作者視點
紀錄片的核心是記錄真實,追求真實也是創造一部紀錄片的唯一藝術標尺。21世紀的紀錄片創作在大眾文化的影響下產生了新的審美嬗變,曾經紀錄片常常與“冷冰冰”“嚴肅”“沉悶”等相對負面的詞匯相聯系,人們寧愿用一個半小時去看一部喜劇也不愿意花費一個小時看一部紀錄片。然而,大眾文化的興起與視覺時代的來臨,雖然讓當代成為娛樂至上的時代,人們熱衷于視覺圖像帶來的直觀感受,傾向于更直接的感官刺激。紀錄片并沒有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銷聲匿跡,而是逐漸轉變了美學范式與創作思路,將冷冰冰的記錄變成了有溫度的講述,將宏大的故事的規格縮小,讓故事中的人成為絕對的主角。如風靡一時的《舌尖上的中國》,突破了傳統介紹中國美食文化的紀錄片的思維定式,將不同地域的美食與當地人相互勾連,讓人的故事成為影片的主角,美食在故事的鋪陳當中飽含情感,讓紀錄片滿溢著濃濃的人情味兒。《舌尖上的中國》的成功也印證了當代觀眾對于人文主義的心理傾向和情感訴求,在物質泛濫、情感貶值、娛樂至上的當代,貼近人們內心的、有溫度的故事才能夠觸動觀眾。但是,從紀錄片創作范疇來看,《舌尖上的中國》并不是一部完全的“直接電影”,更像是一部“真實電影”,導演在拍攝的過程中依然融入了個人情感和觀點,將不同的人物故事與地方美食建立聯系的時候,就已經先入為主地植入了相對應的價值觀,也同時期待觀眾能夠感受并理解其中的價值觀。在價值觀念的引導下,影片的畫面構圖、畫面色彩等鏡頭語言也變得具有指向性和目的性。
紀錄片《梵高:畫語人生》的鏡頭語言在搬演的作用下,也同樣無法保持客觀,反而導演安得烈·赫頓讓影片的鏡頭語言更加戲劇性,更具指向性和隱喻性,在還原梵高書信“真實”背景的名義下,精心打造了梵高生活過的一個個場景。影片用倒敘的方式,首先交代了梵高在1888年12月23日晚精神崩潰,親手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并將它送給了經常光顧的一名妓女。影片在表現這段至關重要的情節時,用一種作者電影的創作方式進行了鏡頭畫面的設計安排,用符號性的事物填充畫面,用以交代環境氛圍和人物心境,如室內向外拍攝的窗外的鐵柵欄將畫面分割成若干部分,同時在鏡頭對焦的過程中賦予鏡頭主觀能動性,讓觀眾產生參與感;又如,鏡頭將精神病院里的枯樹枝納入畫面,且填滿整個畫面,表明環境的蕭條肅殺,并用凌亂的樹枝隱喻此時梵高的精神錯亂。隨后,頭上綁著繃帶、身穿病號服的梵高進入畫面,畫面通過一扇門的關閉表明了此時梵高的肉體禁錮、精神崩潰的狀態,此時的畫面也與梵高的個人境遇相吻合——幾乎被灰暗的冷色調覆蓋,看不到一絲明亮的顏色。為了突出梵高精神的不穩定和身體的脆弱,影片用大特寫的方式將鏡頭近距離聚焦于梵高的面部,在他朗讀自己給提奧的書信內容時,觀眾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他的表情,以感受他崩潰的精神世界。
影片在后面的畫面構圖與色彩設計上,都將梵高的書信和繪畫納入參考的范圍,在人生不如意時的灰暗色調,在創作巔峰時期的明亮顏色,這些無不蘊含了導演的作者思想與創作意圖,輔助觀眾對于梵高瘋狂而精彩的傳奇人生有一個更直接的感受。
四、結 語
電影《梵高:畫語人生》雖然采用搬演的方式,從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影片作為一部紀錄片的真實性,但是梵高的個人形象也第一次在紀錄片當中無比鮮活地呈現在觀眾面前。為了與創作素材與創作背景相一致,影片讓每個演員都獨立于畫面當中,透過與鏡頭的對話塑造人物、推進故事的發展,這不免也是從另外一個層面建立了一種帶有“作者電影”色彩的真實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