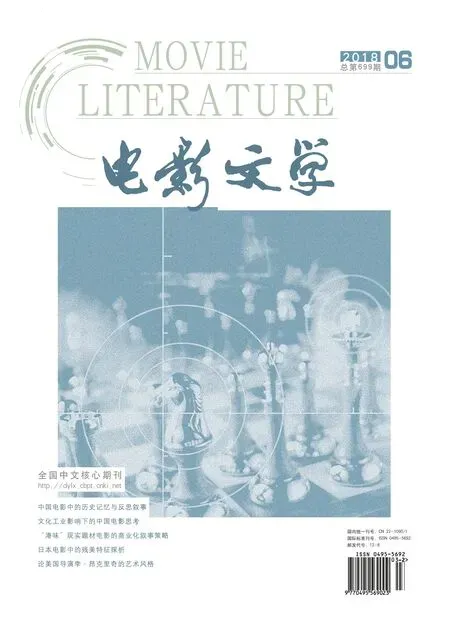觀眾本體與美國懸疑電影的類型化敘事
錢 璐
(江西警察學院,江西 南昌 330103)
美國電影可以說經歷了一個較為復雜且曲折的發展歷程,而最終以類型化在商業電影時代在世界電影市場站穩了腳跟,并且幾乎成為世界電影生產和產業運作通行規律的話事人。這是與美國電影始終將觀眾的審美期待與觀賞快感,置于主流商業電影考慮的第一位的觀眾本體意識分不開的。
在美國的諸多類型片中,懸疑電影可謂是長期以來一直都保持著較高藝術評價與票房回饋的一類。就懸疑電影而言,美國電影也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類型化機制,包括以觀眾為本體的類型化敘事。如果說其他國家的電影人對于類型化的制度、技術等層面的模仿是較為簡易的話,那么要想因襲美國懸疑片的類型化敘事則殊非易事。而美國的電影人自己也在類型化取得成功后,不斷在原有框架下進行調整和創新,甚至有挑戰類型化敘事的嘗試。
一、觀眾本體論與電影類型化
美國電影在類型化上的完善,本質上就是一種觀眾本體論的結果。所謂觀眾本體,即將觀眾視為電影制作、發行以及放映各階段的核心,一切工作圍繞著爭取觀眾、滿足觀眾這一消費者來展開,觀眾本體論認為,觀眾是實現電影自身“造血”的關鍵。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電影產業是個系統工程……好萊塢生產的不僅是電影,更重要的是品牌,從宣傳、發行、放映到后續產品的開發,這種品牌戰略貫穿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始終。”中國電影人敏銳地看到,在美國電影中,觀眾有著怎樣的消費心理是為生產者所關注的,觀眾作為電影產業的終端,直接決定了電影品牌的培育,觀眾的審美品位和審美習慣,關系著整個的電影生態環境。這就使得美國電影人在創作之前,就會對影片的定位有著某種具有前瞻性的判斷。
在懸疑電影的創作上也是如此。懸疑電影的受眾往往來自于懸疑小說的愛好者,對于懸疑故事,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定的主流價值觀念和審美心態。相對于小說而言,電影的拍攝要集中更多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同時觀影也無法像閱讀那樣進行回溯式、暫停式的思索,這也意味著要放棄更多的個人體驗表達,而更多地迎合觀眾的觀賞快感和接受能力。
二、美國懸疑電影類型化敘事
(一)基本懸念的設置
懸念無疑是懸疑電影的核心。在懸疑電影的敘事中,懸念是吸引并保持觀眾注意力的重中之重。“在上演一出戲給觀眾看時,首先要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并使他們保持對演出的注意力愈久愈好。只有做到了這基本的一點,才能實現更為崇高和遠大的目標……因此要造成一種興趣和懸念,這是一切戲劇結構的基礎。”一部懸疑電影情節的展開,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懸念進行的。例如,在詹姆斯·曼高德的《致命ID》(Identity
,2003)中,最基本的懸念就是“兇手是誰”。十個身份各異、經歷不同的人機緣巧合地在一個風雨大作的夜里住進了一家汽車旅館,隨后就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更為詭異的是,他們死亡的順序都與自己的門牌號有關。從常理推斷,兇手無疑應該在還活著的人當中,然而案情卻沒這么簡單,兇手先偽造了自己的死亡,擺脫了他人對自己的懷疑。這一懸念靈感顯然來自英國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無人生還》,而又加入了人格分裂這一理論,對阿加莎原有的敘事進行了開拓。此外,在懸疑電影中,懸念還必須是連續性的,觀眾在敘事者的引導之下,逐步獲得線索,或被逐步帶到一個復雜的情境當中,并接受新的疑問的出現以及對舊的疑問的解答。例如,在馬丁·斯科塞斯的《禁閉島》(Shutter
Island
,2010)中,泰迪的查案過程實際上是一次對自我身份的發現過程,只是他這次在醫生引導下的自我認識以失敗告終了。觀眾追隨泰迪走上孤島深處時,會不斷地發現疑點,如蕾切爾房間的鞋子、反應奇怪的護士等,其中有事物懸念、推論懸念、行為懸念等,而這些懸念都在電影的后部或結尾處得到了解答。觀眾不斷地深入心理情境之中。(二)類型化元素的加入
類型化元素對于類型片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公式化的故事情節,如英雄救美;臉譜化的人物,如勇敢的西部牛仔,乃至符號化的影像,如蒼涼的西部小鎮等。在懸疑電影中,公式化的故事情節即為案件、謎題的發生、勘察和破解,臉譜化的人物則有智慧的偵探型人物,柔弱的受害者,喪心病狂、圖謀不軌的作案者等,而符號化的影像則包括與案情有關的密室、荒野或公路,包括一些與宗教、邪教相關的神秘主義內容等。這些都是已經被驗證為會觸動觀眾緊張感的敘事元素。例如,在伊恩·索夫特雷的《萬能鑰匙》(The
Skeleton
Key
,2005)中,卡羅琳在去維奧萊特的大房子工作后很快就發現了種種詭異之處,這里似乎在進行著某種奇怪的宗教儀式。卡羅琳在自己的調查之后認為老太太維奧萊特可能是一個控制了老頭本的惡毒婦人,她為了救本而用自己學習到的法術來保護自己。結果最后真相大白,原來維奧萊特和本是男女巫師,分別想通過與年輕的卡羅琳和律師盧克交換身體實現永生,而卡羅琳施展的所謂“法術”實際上正墜入巫師彀中。試圖查案的卡羅琳兼任了偵探和受害者的角色,而電影中大量圖解式的符號,如陰森的大屋、萬能鑰匙、宗教儀式等,更是增加了敘事的驚悚與神秘。(三)密閉空間
打造密閉空間也是美國懸疑電影在敘事時給觀眾制造緊張感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斯坦利·庫布里克的《閃靈》(The
Shining
,1980)中,主人公杰克一家三口在冬季大雪封山的時刻住在山頂酒店,面對任何事件都無法獲得外界的援助。而這座酒店在1970年曾經發生過上任管理員砍死妻兒并開槍自殺的慘劇,這一故事深刻地影響了杰克的心理,而心態發生變化的杰克又影響了家人,以至于一家陷入越來越可怕的境地。而隨著通信技術的發達,單純的“密室”式密閉空間無疑已經不合時宜。美國懸疑電影又開始尋求制造一種心靈上的密閉空間。如佐米·希爾拉的《孤兒怨》(Orphan
,2009)中,凱特一家之所以會陷入險境,其住處偏僻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們并沒有被切斷與外界的聯系。關鍵在于曾經的流產讓凱特的心靈產生了陰影,夫婦之間也出現了隔閡,親女是聾啞人,兒子則心中有愧而不敢對父母說實話,一家人無法正常交流,以致出現了一種類似人人被禁閉的互通信息的局限性。三、類型化下的新變
如果說類型化意味著一種穩定、固定的創作傾向,那么觀眾本體的創作理念則意味著變動、變化。觀眾的審美心理機制不僅不是一成不變的,且幾乎可以說是時刻處于流動狀態中的。在類型片塑造著觀眾的審美時,觀眾受整體文化環境而改變了的思維也在動搖著電影的套路。這也就使得有著商業需求的類型片基本上都是處于一種尋找某種變與不變的平衡狀態中的。
例如,被認為是懸疑電影大師的希區柯克可以說是美國懸疑電影類型化的鼻祖。他的《驚魂記》(Psycho
,1960)稱得上是美國懸疑電影的開山之作。希區柯克開創性地運用了弗洛伊德創建的精神分析法,對人們的精神世界進行深入開掘。如在《驚魂記》中,盜取公款的瑪麗安在逃亡途中在一家汽車旅館的浴室為人殺害,隨后她的姐姐、男友等有關人士都接受了警方的調查。而在電影結尾,真相大白時觀眾才知道,殺死瑪麗安的正是看起來正派善良的旅館老板諾曼。更為可怕的是,在電影中出現的諾曼母親實際上早已化為干尸,諾曼是一個精神分裂的病人,觀眾所看到的諾安母親實際上是諾曼人格分裂的產物,也正是這種人格分裂讓他殺死了瑪麗安。在《驚魂記》之后,希區柯克所開創的這種敘事模式基本上都被其他導演沿襲著。在事件激發起觀眾的恐懼、緊張等情緒后,最終一定會指向一個確定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往往就是案情的水落石出。由于案件得到解決往往也就意味著兇手被繩之以法,引發觀眾恐懼的事件到此告一段落,觀眾重新回歸到具有安全感的心態中,情緒在此得到充分的釋放。然而,我們只要對20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以來的美國懸疑電影進行梳理就不難發現,一直有電影人試圖突破希區柯克等前輩創立下的這種有始有終式的類型化敘事。甚至如果我們將目光放得更遠,就會發現包括加拿大、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懸疑電影,如《恐怖游輪》等也紛紛嘗試開放性結局或者不完美的結局,這顯然與觀眾的觀賞期待發生了變化是分不開的。部分電影人憑借著其天才的對敘事的把控,使電影不僅走向了成功,更是走向了經典。例如,在喬納森·戴米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中,作為綁架殺人案兇手的野牛比爾被FBI特工克拉麗斯擊斃了,但是精神病學家,在電影中同樣犯下命案的漢尼拔博士則越獄成功,成為FBI新的敵人,也成為社會治安的隱患。整部電影的敘事主線表面上看是克拉麗斯對野牛比爾一案的偵破,但是事實上則是克拉麗斯對自己心中“尖叫的羔羊”這一心魔的破解。真兇究竟如何被捕等傳統懸疑片慣常使用的核心懸念反而被淡化了。《沉默的羔羊》中最終漢尼拔脫逃的結局也為續集的拍攝留下了余地,但續作并非戴米在拍攝伊始就考慮的問題。而部分懸疑電影則是在籌備電影時就有視觀眾反饋拍攝續集的考量,如克里斯托弗·岡斯根據游戲改編而成的《寂靜嶺》(Silent
Hill
,2006)中,電影并沒有給予觀眾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跟隨羅絲回到家中的小女孩其實不是羅絲的女兒莎倫,而是阿萊莎。而阿萊莎是擁有穿越于三個世界的特殊能力的。因此,盡管羅絲自以為自己回到了家,但是她和丈夫實際上處于兩個平行世界中,無法看到彼此。阿萊莎用這樣的方式實現自己獨占羅絲母愛的目的。當敘事進行到這里時,整個寂靜嶺的冒險故事既告一段落,又有了往下延續的可能。還有一部分不甘于被類型化束縛、才華橫溢的導演,甚至會對懸疑電影的敘事做出革命性的顛覆。這其中最經典的便是克里斯托弗·諾蘭的《記憶碎片》(Memento
,2000),相比起其他懸疑電影使用順序的方式對真相抽絲剝繭,《記憶碎片》則從頭到尾使用了倒敘的方式,使整部電影的敘事顯得支離破碎,觀眾完全進入到主人公萊納德記憶喪失的痛苦之中,從而理解萊納德為何不得不不斷確定自己的身份,并用自欺的方式來給自己尋找活下去的勇氣。同樣,《記憶碎片》的結局也是開放式的,盡管諾蘭在最后似乎對謎底進行了揭示,但是電影依然有另一種演繹的可能性。這也就使得電影能夠為觀眾長久地記住、討論。類型化是當前主流的電影工業模式形態,美國最早在電影的類型化方面進行了實踐與探索。在懸疑電影這方面,美國電影在高度重視觀眾的觀影趣味、觀影心理的情況下,以觀眾為本體建立起了懸疑電影的類型化敘事,保證了美國懸疑電影長期以來在世界范圍內較為成功的商業化運作。而另一方面,電影人也會對懸疑電影的類型化敘事進行適度的創新或翻新,電影的商業性、藝術性、受眾的大眾性以及導演的藝術個性等,也在此得到碰撞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