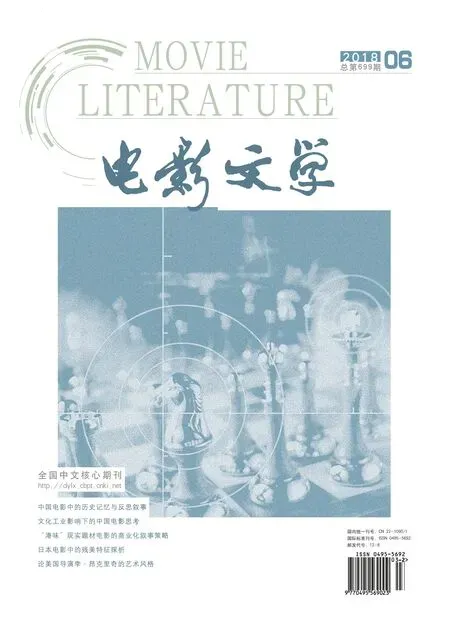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天才少女》的倫理敘事解讀
胡艷娟
(內蒙古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10)
電影是反映社會生活與人類情感的藝術,人類的道德現象與倫理困惑當然也是電影中重要的社會內容。“‘倫理敘事’……是捕捉、分析倫理元素,即‘關于倫理的敘事’,是挖掘小說主題學的內在深層倫理核心。”馬克·韋布的《天才少女》(Gifted
,2017)以一個溫情的故事探討了倫理秩序和倫理社會意識。一、具有復雜性和豐富性的教育倫理
社會教育倫理是應用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對教育倫理的敘事性呈現則是倫理敘事的一部分。《天才少女》的敘事從瑪麗第一天上霍華德學校開始,她在課堂上的過人表現也開啟了全片的矛盾。可以說,教育倫理是《天才少女》的第一重倫理敘事。教育是人的基本權益,它關系著人發展中的可能性、可塑性。瑪麗抵制走入學校,并非她厭倦教育,而是她更喜歡舅舅弗蘭克給予她的教育。而弗蘭克則明白,人的生長和發展是離不開教育和社會的,人要想實現自身的可能性,獲得良好、主動的生命發展,必須有健康的社交關系。這也正是弗蘭克和好心的鄰居羅伯塔之間的區別。一貫寵愛瑪麗的羅伯塔認為瑪麗去到學校不會開心,因為她的智力水平遠遠高于同儕。而弗蘭克則認為瑪麗應該擁有正常的教育生活。正如羅伯特所預料的,學校中的種種令瑪麗極為不適應,一方面是知識教授上,在瑪麗已經學習了高等數學的時候,學校還在教授一年級的簡單加減法運算;另一方面則是在紀律上,瑪麗難以適應學校為了管理方便而設置的種種紀律,如說話前必須舉手,每天必須和其他同學一起拖聲拖氣地對邦妮說“老師早上好”等。于是她在學校中處處表現得格格不入,如公然頂撞老師邦妮,當著校長的面讓校長打電話給弗蘭克接她回家等。在瑪麗出手打傷一個12歲的男生后,學校提出將瑪麗送到培養天才兒童的橡樹教育中心。這遭到了弗蘭克的拒絕。弗蘭克作為瑪麗的監護人,是最關注瑪麗的基本生存處境的人,也處于教育倫理的旋渦中。弗蘭克試圖將問題解決于讓瑪麗受到普通教育生活這一范疇中。因此弗蘭克告訴瑪麗,她必須意識到,她必須去上學,正如自己盡管不喜歡修船的工作但還是必須每天上班。
事實上,弗蘭克所采取的解決方式是來源于他的“個人經驗”。即幼年時,他是家里被視作“普通兒童”培養起來的,姐姐戴安作為“天才兒童”在分去了大部分母親的關愛以外,也替他承擔了母親給予的壓力,即使是在日后弗蘭克成為波士頓大學的哲學教授,他在母親伊芙琳的眼中依然是一個庸庸碌碌的“虛弱者”,和他的父親一樣。在戴安自殺后,弗蘭克顯然不愿意再讓瑪麗成為第二個戴安,于是他希望給予瑪麗的是作為普通人的生存際遇。而學校、伊芙琳甚至包括瑪麗后來進入的寄養家庭,他們對瑪麗的教育計劃則出自“公共價值”,代表的是一種大眾趣味,響應的是一種夾雜了名利的召喚。即當瑪麗被確認為是一個天才兒童,尤其是一個千萬分之一的天才之后,她就自動喪失了作為普通兒童的成長權力,她的潛能應該得到充分的發掘,從而對人類做出貢獻。
整部電影的敘事主線便是一次又一次關于瑪麗撫養權的法庭對峙。從雙方律師的唇槍舌劍中,觀眾不難看出,電影是傾向于弗蘭克一方的。但教育倫理的復雜性也意味著,問題絕不是非此即彼的。電影從多個側面表現了弗蘭克個人生活也存在諸多問題。他辭去教授職務搬家到海邊選擇成為一名修船工,這可以視作是他個人向普通人生活的積極靠攏。然而他經濟困頓,無法滿足給瑪麗買鋼琴的需求,無法建立起個人感情生活,以至于每周六都流連于酒吧,甚至曾經對一個醉鬼有過暴力行為等。也正是上述種種原因讓法庭最終沒有支持弗蘭克繼續撫養瑪麗的主張。《天才少女》提出一個觀點,即教育是存在悖論的,當當事人意識到何為最適合自己的受教育方式時,他們已經在他人給自己安排好的教育之路上走得太遠。戴安的悲劇無疑已經證明伊芙琳的“囚禁式”教育方式是問題重重的,天才成為戴安沉重的負擔和痛苦,她無法由衷地做一個兒童。然而如若戴安或瑪麗被以弗蘭克那樣的,無視天分的方式培養長大,成為一個僅僅相對于旁人優秀一些的普通人,她們又有可能將后悔童年時個人的潛力沒有得到應有的開發,沒有在監護人給予的壓力下得到高強度的訓練以至于自己的“天才”被辜負了。這種矛盾反映了教育倫理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所在。
二、悖謬錯亂的親子倫理
電影在制造矛盾沖突上的敘事策略,便是展現一種悖謬、錯亂的親子倫理關系,弗蘭克所要做的正是避免瑪麗陷入這種倫理關系中,觀眾也自然而然在情節的推進中一直保持著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關心。
在《天才少女》中,親子倫理關系早已偏離了愛與撫養的正常軌道,呈現出一種令人觸目驚心的變態。首先,隨著邦妮的調查以及庭審的進行,六歲半就已經顯示出過人智慧的瑪麗的真實身世被揭開:弗蘭克是瑪麗的舅舅,而她的生母是著名的天才女數學家,被人們寄予厚望能證明一項世紀難題的戴安·艾德勒,而她的生父則從來沒有承擔過作為一個父親的職責,甚至即使一直住在一個城市,這位父親也從來沒有上門看過瑪麗一眼,不知道瑪麗的中間名,他甚至沒有上網搜索一下自己的女兒。而這一代的親子倫理悲劇是由上一代親子倫理的扭曲造成的。
出身英國的伊芙琳是一個嚴苛、有條不紊而難以取悅的母親,她本人也極具數學天賦,但是在結婚生子后,她的科研事業遭受了一定影響,因此她將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在發現女兒戴安是數學天才后,她對于戴安作為個體存在的價值就定位在了成為數學家上,甚至最后具體到了“證明納維斯—托克方程”這一項事業上。從法庭雙方的論辯來看,伊芙琳顯然剝奪了戴安應有的社交,如從來沒有參加過女童子軍,17歲時喜歡鄰家的男孩,和對方私奔到佛蒙特去滑雪,結果伊芙琳卻控告對方綁架戴安,導致戴安一度嘗試自殺等。面對弗蘭克一方的律師詢問伊芙琳是否知道戴安還有什么其他愛好時,伊芙琳堅定不移地聲稱戴安唯一的愛好就是數學。除此之外,在電影中出現的所有戴安的照片,無不都是短發形象,這暗示著伊芙琳對她的一種抹殺性別意識的控制。
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很難想象戴安擁有怎樣的孝親情懷。一方面生父在自己不滿十歲時去世,繼父則為母親看不起,父性崇拜對于戴安來說顯然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母親在某種程度上將自己當成了實現名利的工具,戴安所感受到的來自于母親的愛和接納是有條件的,即建立在自己是天才的基礎上的,血緣親情被一種畸形的管束進行了極端化的切割。也正是由于缺少了正常的社交教育,戴安未婚先孕。這種行為違背了一貫喜歡支配戴安的伊芙琳的意愿,于是伊芙琳放棄了戴安。戴安遭受了愛情和親情的雙重拋棄,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心靈創傷。出于一種絕望心態,她在自殺前帶著女兒瑪麗找到弟弟弗蘭克,而弗蘭克急于出門約會。弗蘭克未曾想到回來時姐姐已自殺。殺死戴安的很大程度上便是倫理困境。
而單純通過庭辯來讓看似振振有詞,實則理屈的伊芙琳暴露自己在母女關系上的殘忍并非電影倫理敘事的全部。《天才少女》以“納維斯—托克方程”問題的解決為這段悖謬親子倫理畫上了句號,也實現了敘事上的高潮。之前電影已經通過伊芙琳帶瑪麗參觀學校時的介紹等鋪墊介紹了“納維斯—托克方程”,并借伊芙琳之口表示方程沒有被證明非常遺憾,戴安已經非常接近證明了。然而在電影的最后,弗蘭克將戴安遺留的手稿送給伊芙琳,原來戴安早已證明了“納維斯—托克方程”,但是她提出一定要在“身后”發表,伊芙琳表示戴安已經去世多年,弗蘭克則解釋,是伊芙琳“身后”。這個遺囑成為戴安報復自己母親的一種方式。她到死也不愿意讓伊芙琳完成自己的夢想,即看到女兒發表這個驚天動地的聲明。而這種報復無疑也是極為可悲的。伊芙琳對著堆滿孩子氣涂涂畫畫以及滲透有戴安淚痕的手稿流下后悔的眼淚。
可以說,盡管戴安這一角色并沒有在電影中真正出場,但是觀眾已經能得到一幅生動的戴安的心靈圖像。
三、倫理自由與審美期待
作為一部商業電影,《天才少女》在讓觀眾看到殘酷的倫理關系,以及主人公有可能面對的倫理困境的同時,又給予了敘事一個符合觀眾審美期待的、較為圓滿的結局。在法庭的審判下,伊芙琳和弗蘭克誰也沒有成為贏家,瑪麗被判進入寄養家庭成長,到12歲以后才能自主決定和誰生活。在與弗蘭克分別時,瑪麗表現出了異常的絕望和悲哀,可見其盡管和羅伯塔和弗蘭克一直過著幸福的生活,但她的內心深處依然有著強烈的不安全感,對于離開舅舅,瑪麗認為這是她又一次“被拋棄”。而弗蘭克也為失去了瑪麗而陷入木然中。終于,在老師邦妮的提醒下,弗蘭克發現了瑪麗心愛的獨眼貓弗雷德被丟入寵物寄養中心,于是下定決心拿出姐姐戴安臨終前給自己的證明手稿換回瑪麗的監護權。伊芙琳得到手稿后,將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教授聯名發表,并在未來的日子里因為收獲名利而俗務纏身,而條件就是伊芙琳放棄對瑪麗的造夢教育計劃。在電影的最后,瑪麗終于能和弗蘭克生活在一起。
電影通過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戴安證明手稿來實現了一種“倫理自由”。根據斯賓諾莎的理論,倫理自由既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人生和德性的完滿境界。在《天才少女》中,倫理自由主要指的是人物的一種理想的倫理關系,人物所得到的倫理關系是符合個人意志的,那么他就獲得了倫理自由。在電影的結尾,瑪麗一方面能夠和弗蘭克過著她期盼已久的幸福生活,將得到弗蘭克和羅伯塔的關愛;另一方面在教育上,她還將繼續在橡樹學校的學習,使自己的數學天賦能夠得到發展,但同時又能夠因為邦妮等人的幫助而繼續結交自己的同齡朋友。毫無疑問,瑪麗將不再是一個除了數學生活中只有一片空白的,游離于社會的怪人,她將過上和母親戴安截然不同的一生。甚至即使是已經釀成悲劇的前代倫理問題,即戴安對伊芙琳的怨恨,也在伊芙琳悔恨的淚水中得到了淡化。《天才少女》在展開了兩條倫理敘事線的同時,又用這樣的方式同時解決了前述兩種倫理問題,即教育和親子倫理問題。
盡管這一結局是理想化的,它高度依賴于一個元素的介入,即戴安的證明手稿。相對于一個悲劇結局而言,它減少了批判的力度,但這是《天才少女》的悲憫德性的體現,也是電影迎合觀眾審美期待的體現。且由于電影在敘事中已經對“納維斯—托克方程”進行了充分的鋪墊,因此,當戴安已經將其證明這一結果拋擲到觀眾面前時,觀眾其實感覺并不突兀。這一敘事策略無疑是成功的。
倫理敘事是從個體性的經驗走向普適性的存在,從個別的故事走向具有普遍意義的精神的。《天才少女》通過對瑪麗個人經歷的敘事,展現了一種個例式的生命感覺,從而引發人們對有關教育的社會意識,以及親子倫理訴求的關注,并在敘事中通過一種“大團圓”結局試圖實現符合觀眾期待的社會倫理自由。觀眾在其中感受到的除了瑪麗作為個人的體認和生命感覺,更得到了關于兒童成長復雜性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