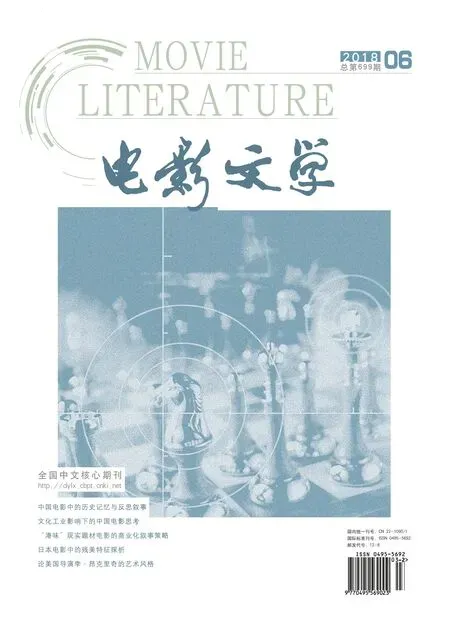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悲劇美學意蘊
董秋榮
(吉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000)
2015年4月24日,戰爭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在俄羅斯上映。該電影改編自蘇聯著名當代作家鮑里斯·利沃維奇·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說,這是該部文學作品第二次被搬上銀幕。不同于1972年上映的第一版電影所采用的詩意敘事手法,最新上映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使用去浪漫化的敘事表達記錄了一場激烈殘酷的森林阻擊戰。電影以集中刻畫戰爭環境中的女性命運與情感為焦點,將于國家危難之際奮勇抗敵的女戰士的柔弱與堅強表現得淋漓盡致,從而使戰爭英雄人物的呈現栩栩如生、個性鮮明,既飽含無盡艱難,又承載無限崇高,深度展現了女性個體生命價值在抗爭與死亡中的涅槃之美,使電影充滿令人震撼的悲劇精神與悲劇美。
一、電影故事的悲劇美學呈現
關于悲劇,亞里士多德曾言:“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這種模仿能夠“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可見,悲劇可定義為一種美感體驗,其可劃歸為美學范疇。一出悲劇通常由劇中人物遭受的不幸引發觀者的悲感體驗,進而通過觸發觀者的憐憫與恐懼之情促成其情感得到宣泄與凈化并獲得心理平衡。誠如王國維曾在《〈紅樓夢〉評論》中提道:“悲劇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它的美學特性是壯美與崇高,它的審美價值是教化與解脫。”
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故事背景是衛國戰爭時期。衛國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發生于1941年至1945年,其規模之龐大、戰況之激烈、傷亡之慘重堪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戰爭之最。衛國戰爭作為蘇維埃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的不僅是俄羅斯民族團結自強的不屈精神內核,更背負著國家政府重振旗鼓、人民祈獲新生的種種企盼。在這一特殊且殘酷的戰爭背景下,五位女主人公的設置不僅使電影故事多了些溫情與感動,也無限放大了這部電影的人道主義精神,電影對人性的極盡歌頌,震撼觀眾心靈的同時,使電影在極強的悲劇效果下盡顯美感。
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題材與背景都在殘酷的戰爭映襯下備顯殘忍,然而電影著重刻畫的人物形象卻是原本碌碌無為且柔弱不堪的婦女,二者間的強烈沖突將戰爭的無情推向極致,卻也高度詮釋了蘇聯紅軍戰士的大無畏英雄氣概,使人道主義精神穿透戰爭的陰霾撲面而來。另外,戰爭時期本是崇尚英雄的年代,電影卻將探尋的觸角伸向普通女兵群體,以刻意表現女兵的柔弱甚至缺點的方式將英雄形象平民化。比如,麗莎還未消滅一個敵人就在回部隊找援兵的途中被沼澤淹沒而亡;加麗婭在戰場因無法抑制恐懼而在敵人槍口下慌忙竄逃,不幸中彈身亡。所有這些都活化表現出了普通人面對戰爭時的無助和膽怯,當這些加諸為國而戰的士兵身上,不但不會抹殺他們的英雄色彩,反而使英雄形象變得更加令人感動、親近且熟悉,不僅使無情的戰場閃耀人性的光輝,更使電影體現了基于個體生命關懷的悲劇美學韻味,告誡著人們,平凡才是崇高的真諦,而英雄的本質則是平淡無奇的,甚至伴有瑕疵的血肉身軀。
二、美之解構與重建
靜悄悄的黎明是充滿和諧的生命世界,然而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黎明卻被戰爭的血腥包裹。女性個體出現在戰場,則象征了女性身份的剝離,女性所代表的純潔與愛淪為被摧殘和異化且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符碼,預示著和諧將被摧毀,悲劇即將衍生的殘酷命運。導演此舉將戰爭與人之間的悲劇氛圍烘托到極致,既揭露了戰爭的殘酷規則,又挑撥起了人們奮起而戰的悲憤感,誠如郭沫若所言:“悲劇的價值不是單純地使人悲,而是在具體地激發起人們把悲憤情緒化而為力量,以擁護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將死的成分。”
戰爭實為血與火的碰撞,“戰爭令女人走開”是亙古流傳的名言,然而,千百年的歷史證明了,戰爭,從未讓女人離開。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女性是戰爭舞臺的嬌艷舞者,她們從幸福與寧靜中脫離,扛槍而戰的身影像是一出戴著冰冷腳銬跳出的狐步舞,溢滿沉重的蕭瑟與凄涼。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小說原作者鮑里斯·利沃維奇·瓦西里耶夫在慨談作品創作初衷時曾坦言,將小說的主人公設置為穿軍大衣的女兵,并未違背生活真實(這與衛國戰爭中大批女性投身軍營、卷入戰爭的事實并無出入)。瓦西里耶夫還提到,一名士兵在戰爭中犧牲,無論看上去多么令人痛心與痛苦,都仿佛是一場嚴酷的斗爭不能避免的,然而,如若倒斃于敵人槍口下的是一位年輕的姑娘,那么,這就是違反常理的、令人發指的悲劇,會引起觀者特別的痛苦。原因在于,姑娘們本是為了愛與繁衍來到人世,讓她們獻身戰場則賦予了作品突出的道德意義與尤為強烈的感情色彩,這樣做會使作品洋溢深刻的激情。電影中,當五位戰士為戰爭獻出寶貴的生命,戰爭的暴戾與猙獰充分暴露,電影借由美之覆滅對法西斯戰爭發出強烈譴責與控訴,這正是女性之純美在電影戰爭場景中的解構與重建,表達了電影創作者對戰爭中女性命運的關注與關于戰爭的反思。
三、女戰士之死的死亡審美
美學史上將人體看作自然美之最高形式,死亡表征生命的終結與美的毀滅,從這一角度而言,將死亡歸結為丑之范疇并不為過,然而,在藝術表現中,死亡實質上是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的。陸楊在其著作《死亡美學》中提道:“通過藝術的中介可以化死亡的恐怖為美感……通過藝術的篩選和抽象,可以進一步強化一些特定的死亡行為和現象先已既有的審美價值。”
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五位女戰士之死具有至高的美感。戰爭中,當男性之死被女性之死所替代,女性之死所表現出的不僅是死之壯美,更蘊含無盡凋零的柔美之感。主要原因在于,古往今來,以生育來延續生命是女性之使命,而死亡與戰爭本應是女性不能承受之重。然而電影中,五位可敬的女戰士則用死亡譜寫了一幅絕美畫卷。
美國作家愛倫·坡認為,一位美麗女性的死亡,是世上最富有詩意的題材。電影中,熱尼婭作為美麗與果敢的化身,直面德寇來襲,與敵人抗爭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鐘,中彈墜落山間的一刻,她用高傲的臉龐與堅定的目光,表達了其對殘忍敵方種種惡行的指控,她的美在死亡的剎那化為永恒。同熱尼婭一樣,其他四位女戰士的生命在戰爭中悲情謝幕,她們的死亡猶如鮮花隕落,帶給人無限傷情的同時,也于瞬間將美麗定格,表達了電影對戰爭的強烈譴責。
四、結 語
女性,是莎士比亞戲劇當中最為脆弱的生物,然而在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女人卻不得不與男人在戰爭的舞臺上共舞,勇敢殺敵,直面死亡。無情的戰爭奪走了女戰士作為女性的玲瓏之美,卻又使她們煥發出超然的雄壯之美,她們在戰爭的硝煙中覆滅,卻也將永恒之美定格于人們心間。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將女性作為戰爭的渲染主體使其成為一部不折不扣的悲劇,然而其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痛訴戰爭無情的同時,也充分描摹出了俄羅斯戰士抵抗敵人的不屈決心,將關于戰爭的悲壯與死亡之美刻畫得絲絲入扣,可謂一種高層次的藝術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