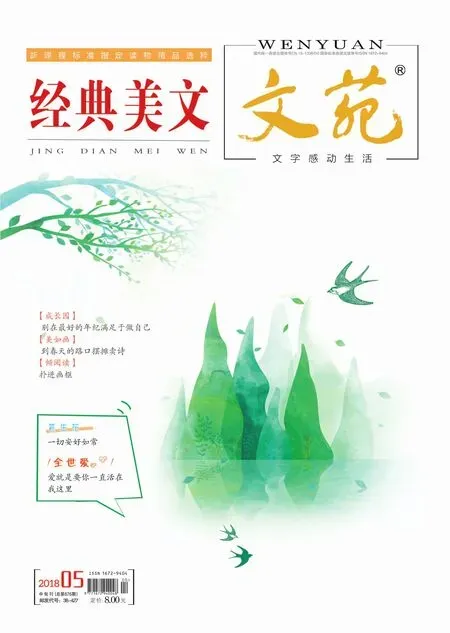胭脂紅妝:留不住的芳華
文/伍詩雅
據(jù)說,擁有全套色系的口紅是每個女生的夢想,這句話,放之古今皆準(zhǔn)。雖然沒有上百個色號的小黑管,也沒有價(jià)值上千的整套彩妝,但古代女子化起妝來一點(diǎn)不含糊,如溫庭筠所寫:“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整頭發(fā)、敷水粉、抹腮紅、畫蛾眉、貼花鈿,一步都不能少。
化妝有多復(fù)雜?看看現(xiàn)代人的口紅包就知道了。
芳華顏色,取于自然
胭脂是古人妝鏡匣中絕對的主角,分為面脂和口脂。在胭脂被發(fā)明之前,最早被用來在臉上化妝的染劑是一種自然礦物材料——朱砂。
朱砂,又稱辰砂、赤砂,由于在自然界容易獲取,一直被古人作為顏料使用。
古代雖然面脂口脂不分,但可以看出,最初化妝品中紅色染劑主要是用朱砂做的。天然朱砂的主要化學(xué)成分是硫化汞,在高溫作用下會釋放汞硫化物,要是不小心吃下去,會導(dǎo)致汞在人體內(nèi)累積,形成積蓄性汞中毒。這樣的化妝品哪怕是《紅樓夢》中“愛吃”胭脂的寶二爺也下不了嘴。
胭脂的出現(xiàn)正好解除了這一生命與美貌的困境。胭脂的準(zhǔn)確傳入時(shí)間沒有定論,《中華古今注》中就說:“燕脂起自紂,以紅藍(lán)花汁凝作之”,認(rèn)為胭脂是商朝時(shí)從燕地傳入的,因此也叫“燕脂”;而《博物志》中則記載胭脂的原料是由漢代張騫從西域帶回來的。若就目前的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至少在漢代,胭脂已經(jīng)進(jìn)入中原地區(qū),并成為一種常見的化妝品了。
紅藍(lán)花就是這種胭脂的原材料。這種植物生于西北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焉支山,也就是今天的甘肅一帶。唐代《妝樓記》中也記載:“燕支,染粉為婦人色,故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支。”“燕支”、“閼氏”發(fā)音相近,“胭脂”一詞——有時(shí)又叫“燕脂”——就出自這些詞的諧音。古代面脂口脂本沒有專門的名字,引入紅藍(lán)花后,便一概稱為胭脂了。
除了外來物種紅藍(lán)花,紫草、蘇木、山花、石榴花等本地植物,也一直被古人用來提取胭脂所需的紅色素。
到了唐代,用來制作胭脂的植物已有二三十種之多,唐玄宗之女永樂公主就曾開辟香料園圃,用來種植制作化妝品所需的各種植物。雖然原料的種類各不相同,但自漢至清,古代胭脂的制作方法一直秉持著以“自然”為美的原則。
20世紀(jì)60年代,美國Cutex公司推出的口紅胭脂產(chǎn)品就以原料自然為賣點(diǎn)。
在花朵到胭脂的這一轉(zhuǎn)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萃取花瓣中所含的色素,在西漢時(shí)期,匈奴人已經(jīng)發(fā)明一套成熟的萃取方法,被稱為“殺花法”。民國時(shí)期的《御香縹緲錄》中記錄了宮廷內(nèi)司以此法給慈禧太后做玫瑰胭脂的情形: 精心挑選砂紅色的新鮮玫瑰,將其反復(fù)搗碎成漿,再用細(xì)紗布過濾干凈,以酸水沖洗,只留下純凈的紅色花汁,最后將剪成小塊的絲綿紙浸入花汁,十余天后取出陰干。
鮮花的色香本不能久存,但胭脂能將這一自然孕育的精華留存下來,以人力延長花葉的生命。在萃取花汁之后,古人或以細(xì)紗布浸潤,或拌以白米粉調(diào)色,或加入油脂熬煮使其凝固,以使胭脂成形并方便保存攜帶。
全能單品,用以百方
有了胭脂,古人會怎么用呢?
如果說胭脂像一支著色的畫筆,那么,其筆鋒所及之處才是真正的精彩。
古人重儀表看顏值,所以在古代,化妝也是有文化講規(guī)矩的事兒。這一點(diǎn),在傳統(tǒng)京劇臉譜上就可以看出。在京劇臉譜中,每個人物的性格、地位、氣質(zhì)都展露無遺——紅臉是忠義英勇,白臉是奸詐陰險(xiǎn),金銀兩色多是神仙高人;畫法上也有三塊臉、六分臉、碎花臉等樣式,花樣可不少!
不僅是舞臺妝,古人的生活妝也頗費(fèi)心思。在《妝臺論》中就寫了幾種當(dāng)時(shí)流行的胭脂紅妝:“美人妝,面既施粉,復(fù)以燕支暈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妝,淺者為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妝。”美人妝是先敷白米粉再施胭脂,以胭脂濃淡調(diào)節(jié)色調(diào);飛霞妝則是先薄涂胭脂,后以粉輕掩——次序不同,得到的效果不一樣。
點(diǎn)唇,是胭脂紅妝中變化最大,時(shí)代特征也最鮮明的一部分。
我國古代,點(diǎn)唇的習(xí)慣由來已久。對古人來說,嘴唇的形色是評判美女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嬌小濃艷的嘴唇最是令人心動。
“點(diǎn)唇”一詞出自漢代,在這一時(shí)期,女性獨(dú)特之美尚沒有得到確立,仍然是以德為先,因此,漢代妝容上講究“粉白黛黑”,追求清疏自然之美。漢代女子點(diǎn)唇時(shí)不會將唇脂涂滿整個嘴唇,而是點(diǎn)成一個上小下大的三角圓樣式,顯得既奪目又不失含蓄。到了隋唐時(shí)期,化妝風(fēng)尚就變得開放多了。且不說唐朝女性以臉寬體胖為美的心胸,光是唐朝女子們前衛(wèi)濃烈的涂脂抹粉方式,就足以將盛唐氣象展現(xiàn)得一覽無余。
唐朝國力強(qiáng)盛,文化氛圍更是出了名的自由包容,在這樣的氛圍下,唐朝的化妝法一改漢魏時(shí)期的含蓄玄學(xué)畫風(fēng)。在點(diǎn)唇之前,她們會以白米粉將雙唇及臉頰全部涂白——這樣一來,她們本身的唇形唇線,哪怕歪了缺了,也沒人發(fā)現(xiàn)得了——之后,再用各色胭脂畫出中意的唇樣,加上華麗的花鈿,發(fā)型搭配。
如果古代有亞洲四大邪術(shù),唐人的化妝法絕對排得上號。
從今天日本藝伎的臉上,我們還能看到獨(dú)特的點(diǎn)唇式樣。
《清異錄》中就曾記載,在晚唐三十余年的時(shí)間里,竟然出現(xiàn)了十七種婦女唇式,并被冠以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圣檀心、萬金紅等花式妝名,比起現(xiàn)代的妝名可是毫不遜色。
在現(xiàn)存的唐代敦煌壁畫《樂庭環(huán)夫人行香圖》中,今天的人們?nèi)匀豢梢钥吹桨雸A形、菱角形、月牙形等各種形狀的唇妝。
唐代之后,人們對唇妝的熱情漸漸轉(zhuǎn)向內(nèi)斂,由宋到清,“胭脂淡淡櫻桃顆”的櫻桃小嘴始終占據(jù)著時(shí)尚界的主流地位,甚至出現(xiàn)了《點(diǎn)絳唇》這樣的詞牌名,不得不說中國男性的審美一直很穩(wěn)定,但在這千年之中,女性獨(dú)特的身影漸漸湮滅。
紅顏如水,見于詩賦
文化的潮流也是此消彼長,但畫中人詩中事可以長存。在很多時(shí)候,人們對古人胭脂紅妝的想象更多地來自筆墨書畫。
中國文人在寫作中對胭脂紅妝的喜愛程度,恐怕不亞于書酒月光,詩人們常用胭脂指代女性,甚至以女性自比。如屈原,在他的楚辭里,香草美人的說法比比皆是。如唐代詩人朱慶馀的《近試上張籍水部》中寫道:“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shí)無?”看上去是寫女子化妝之事,實(shí)際上是想問問考官自己的成績?nèi)绾巍?/p>
除了以女子自比,文人筆下的胭脂往往承載了更多的文化內(nèi)涵。如李后主亡國后所作的《相見歡》“胭脂淚,留人醉,幾時(shí)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蘇東坡的《菩薩蠻》“夜來殘酒醒,惟覺霜袍冷。不見斂眉人,胭脂覓舊痕”——一個是家國之痛,一個是生死之傷,卻因胭脂觸景生情,用胭脂托物言志。在詩人眼里,在永恒與短暫、生與死的命運(yùn)交替之中,人的處境與胭脂紅妝也是同構(gòu)的。
古往今來,當(dāng)人們展鏡梳妝時(shí),對于美好的追求就隱含在輕拍上臉的精彩顏色之中。胭脂其物,以實(shí)用立身,生在艷麗之中,受人喜愛,被筆墨記留,卻像路途的旅客,絢爛易逝,成為歷史長河中一段別樣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