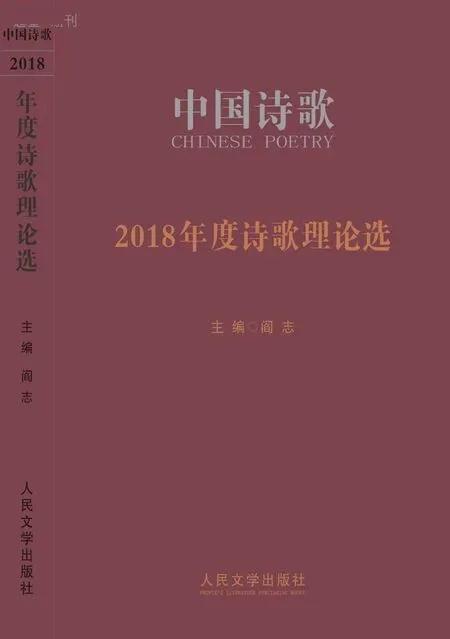中國新詩格律觀念與實踐的遷變
張桃洲
中國新詩是文化和詩學變革的產物, 相對于古典詩歌而言,新詩在諸多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中尤為顯著的是語言與形式, 即以白話取代文言, 并取消了古典詩歌的根本元素——格律。 不過, 新詩誕生后, 自20 世紀20 年代起, 針對初期白話詩的自由散漫而提出的各種格律方案就沒有停止過, 對于新詩是否需要格律、 能否建立格律等問題, 至今仍然眾說紛紜, 莫衷一是。 綜觀圍繞新詩格律所展開的種種探索——無論理論探討還是創作實踐, 抑或某種學術化的研究——則不難發現, 人們在對格律的理解和界定上顯示出兩種傾向: 一種是將格律視為詩歌的外部音響特征, 著眼于對詩歌的音步、 韻腳、 平仄、 建行乃至句法的斟酌與探究, 從早期的陸志韋、 聞一多、 朱湘等人的部分實踐直至當下的某些理論著述, 無不如此; 一種是試圖依據格律的內在化趨向, 重視對詩歌的內在節奏與旋律的經營。 而從格律觀念和建構的來源來說, 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化: 一是受西方詩歌的影響較多, 一是強調格律的傳統與本土特色。 格律的內、 外之別與中、 西分野, 顯然緣于人們詩學意識的差異。
值得肯定的是, 有關新詩格律的探討顯示了新詩形式建設的富于理性的思考, 具有嚴密、 系統的理論傳承性, 為新的詩學建設和創作實踐積累了值得珍視的歷史經驗; 但另一方面, 由于新詩文體的特殊性和歷史境遇的復雜性, 一些格律方案存在著較多認識上的偏誤, 并且與創作實踐明顯脫節, 其間的得失亟待進行反思和探究。
1. 技術難題
一般認為, 聞一多《詩的格律》 一文的發表, 標志著關于新詩格律問題系統探討的開始。 盡管在此之前, 周無、 李思純、陸志韋等曾針對詩歌的音律、 節奏等話題進行過討論, 但似乎只有在《詩的格律》 發表的1926 年, 在徐志摩主持的《晨報副刊》 “詩鐫” 上, 聞一多通過回應饒孟侃關于新詩音節的探討,正式亮出了“格律” 的旗號, 以至于以新月諸子為核心形成了一個“新格律詩派”。 聞一多提出: “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音節), 繪畫的美(詞藻), 并且還有建筑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 他還特別強調自己推崇的新詩格律并非來自傳統的律詩(并指出了二者的三點不同), 而是更多地取法于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
聞一多對格律的倡導帶來了雙重后果。 從負面的效應來說,就是模仿者亦步亦趨, 認為只要行句“均齊” 即可, 最終使格律在寫作實踐中陷入僵化, 導致“豆腐干” 詩盛行一時。 對此,徐志摩不得不做出聲明與辯解:
(格律) 這原則卻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詩, 某式才是詩; 誰要是拘泥的在行數字句間求字句的整齊, 我說他是錯了。行數的長短, 字句的整齊或不整齊的決定, 全得憑你體會到的音節的波動性; 這里先后主從的關系在初學的最應得認清楚, 否則就容易陷入一種新近已經流行的謬見, 就是誤認字句的整齊(那是外形的) 是音節(那是內在的) 的擔保。 實際上字句間盡你去剪裁個齊整, 詩的境界離你還是一樣的遠著……說也慚愧,已經發見了我們所標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誰都會運用白話, 誰都會切豆腐似的切齊字句, 誰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節——但是詩, 它連影兒都沒有和你見面! (徐志摩: 《詩刊放假》, 《晨報副刊·詩鐫》, 1926 年6 月10 日)
與“建筑的美” 引起的誤解(片面追求詩句整齊) 相類似,聞一多主張的“音樂的美” 常常被誤解為詩歌的外部音響(外在聲音), 將表面的鏗鏘指認為新詩的節奏。 兩種誤解都是以表象代替了實質。 就此而言, 梁實秋的疑慮不無道理: “把詩寫得很整齊……但是讀時仍無相當的抑揚頓挫。” (梁實秋: 《新詩的格調及其他》, 《詩刊》, 1931 年1 月創刊號)
與此同時, 聞一多要新詩格律取法西方詩律的設想, 也遭遇了技術上的難題, 這是因為在漢語形態和西方語言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 象征派詩人王獨清就深感中國語言(漢語) 在處理“音” 方面的困難, 他列出一個關于詩的公式“ (情+力) + (音+色) =詩” 后解釋說, “在以上的公式中最難運用的便是‘音’與‘色’, 特別是中國的語言文字, 特別是中國這種單音的語言與構造不細密的文字。” (王獨清: 《再談詩——寄木天、 伯奇》,《創造月刊》, 1926 年3 月第1 卷) 應該說, 中國語言文字本身在音韻的營構上是有其優勢的(比如文言之于古典詩歌), 問題可能在于新詩的格律能否以外國詩律為依據進行建構。 對此, 另一位“新月派” 同人葉公超持不贊成的態度, 他認為“西洋的格律絕不是我們的‘傳統的拍子’ ”, “論新詩我們最好能不用西洋名詞則不用”, 特別是, “我們語言中就缺少鏗鏘脆亮的重音和高音, 因此我們也就不能有希臘式的或英德式的音步, 假使有人一定要勉強摹仿的話, 也一定只是費力不討好的。” (葉公超: 《論新詩》, 《文學雜志》, 1937 年第1 期) 這就從語言差異的角度, 指明了新詩格律之借鑒西方詩律的難處甚至不可能, 畢竟漢語詩的平仄并不對應于西方詩的輕重音和抑揚格。
這種技術難題同樣出現在20 世紀50 年代幾次關于新詩形式討論所提出的方案中。 參與討論的詩人、 理論家、 語言學家貢獻了各自關于新詩格律的見解: 王力提出格律應該遵循“有客觀標準” 和“具有高度的音樂的美” 兩條原則, 認為“韻腳是格律詩的第一要素”, “第二要素是節奏” (王力: 《中國格律詩的傳統和現代格律詩的問題》, 《文學評論》, 1959 年第3 期); 羅念生詳細剖析了格律所包含的節奏、 頓和韻等要素的特點及相互關系(羅念生: 《詩的節奏》, 《文學評論》, 1959 年第3 期);周煦良指出, “對于一個寫詩的人來說, 具備一種格律感是和畫家具備一種色彩感或形象感是同等重要的事情” (周煦良: 《論民歌、 自由詩和格律詩》, 《文學評論》, 1959 年第3 期); 金戈提出可以建立兩類新格律詩: “較嚴格的新格律詩” 和“較自由的新格律詩” (金戈: 《試談現代格律詩問題》, 《文學評論》,1959 年第3 期); 金克木認為格律“大致是以平仄、 單復、 奇偶、 虛實來相間排節奏, 使幾種矛盾的因素相反相成” (金克木: 《詩歌瑣談》, 《文學評論》, 1959 年第3 期); 林庚提出新詩格律的關鍵—— “建行”, 并對之進行了闡發: “中國詩歌根據自己語言文字的特點來建立詩行, 它既不依靠平仄輕重長短音, 也不受平仄輕重長短音的限制; 而是憑借于‘半逗律’。”(林庚: 《再談新詩的建行問題》, 《文匯報》, 1959 年12 月27日) 這些看法有不少是回應1920—1930 年代關于新詩格律的探討的, 比如林庚認為應以中國語言文字特點“建行”、 突破“平仄輕重長短音” 的制約, 便是呼應了葉公超的觀點。 事實上,他早在1930 年代即開始嘗試“半逗律” 和“九言詩”, 惜乎并未得到響應和延續, 這部分地緣于他自己也意識到的實際操作上的困難。
在上述見解之外, 何其芳、 卞之琳關于“現代格律詩” 的闡述格外值得注意。 在《關于現代格律詩》 這篇長文中, 何其芳在充分肯定自由詩“非常富于創造性” 的前提下, 表述了建立現代格律詩的必要性, 并著重就“頓” 和“押韻” 兩方面討論現代格律詩的依據: “現代格律詩在格律上只有這樣一點要求: 按照現代的口語寫得每行的頓數有規律, 每頓所占時間大致相等, 而且有規律地押韻。” (何其芳: 《關于現代格律詩》, 《中國青年》, 1954 年第10 期) 卞之琳則進一步凸顯了“頓” 在現代格律詩中的位置, 將其實踐表現細化為兩種基本的調式, 即偏向于說話式的“誦調” 和偏向于歌唱式的“吟調” (卞之琳:《哼唱型節奏(吟調) 和說話型節奏(誦調) 》, 《作家通訊》,1954 年第9 期)。 他們的理論具有系統性和開放性, 遺憾的是在當時并未得到廣泛支持(尤其在實踐方面), 很快被淹沒在時代喧囂和歷史煙塵中。 何其芳同葉公超一樣, 留意到了現代漢語偏于口語的特性對新詩節奏(“頓” ) 之形成的影響, 卻也因為不能擺脫對外在的“韻” 的依賴, 而難掩其過于形式化的不足。
縱覽探討新詩格律的數十年間, 李思純、 陸志韋、 聞一多、徐志摩、 朱湘、 饒孟侃、 孫大雨、 葉公超、 卞之琳、 林庚、 何其芳、 朱光潛、 王力、 羅念生、 周煦良、 鄭敏等詩人和理論家, 從理論、 技術層面所提出的包括“音組”、 “頓”、 “格調”、 “半逗律” 等在內的形式、 格律主張或方案, 為新詩探尋具有可行性的格律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 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正如當年何其芳批評“民歌體” 在體裁上有限, 句法與現代口語不符, “寫起來容易感到別扭, 不自然, 對于表現今天的復雜的社會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縛” (何其芳: 《關于新詩的“百花齊放” 問題》, 《處女地》, 1958 年7 月號) ——歷史和實踐證明, 探討新詩格律倘若僅僅注重外部音響(外在的頓與韻)的話, 其缺陷是明顯的。 實際上直至當前, 仍然有不少關于格律的討論過分注重外部枝節, 導致新詩格律的確立之路趨于閉鎖。
2. 語言困境
為何在對新詩格律的理解和構想上, 很多人會將重心放在聲音的外在層次? 古典詩歌的音律傳統及其形成的對詩歌的慣性認識(思維) 與期待, 固然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某些寄附于這一傳統和認識的舉動也會潛在地起作用, 比如由“吟” 轉化而來的“誦”。 詩歌的表面音響之受到重視, 大概正是受到了朗誦的促動。 但人們往往忽視了一點: 閱讀文字和朗誦文字其實是兩種不一樣的對待詩歌的方式, 二者產生的效果也迥乎不同。
在此過程中, 現代漢語本身的特性對新詩格律的基礎性意義應得到充分考慮。 在一首詩里, 或許不是字數的多少、 句子的長短, 而是語詞的組合方式, 也就是它的句法決定了它的聲音構成。 新詩在句法上是偏于歐化的, 受西方語法的影響很深, 朗誦的時候較為拗口、 繁瑣, 并不符合一般口語的習慣。 朱自清曾經準確地指出了漢語新詩之難以誦讀的原因: “新詩的語言不是民間的語言, 而是歐化的或現代化的語言。 因此朗讀起來不容易順口順耳”; 除此以外, “新的詞匯、 句式和隱喻, 以及不熟練的朗讀的技術, 都可能是原因。” (朱自清: 《朗讀與詩》, 《新詩雜話》, 三聯書店, 1984 年版)
另一與此相關、 易于陷入的誤區是: 由于注重詩歌的外部音響, 人們在關于新詩格律的探索中, 總是力圖確立某種固定的格律模式, 這從現代漢語特性來說恐怕難以實現。 現代漢語作為詩歌語言的局限性十分明顯, 廢名就認為: “新詩的音樂性從新詩的本質來說是有限制的” (廢名: 《論新詩及其他》,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他繼而提出的“新詩是散文的文字, 詩的內容” 之論, 則從一個側面點明了新詩的某些特性。 何其芳也提出: “五言七言首先是建立在基本上以一字為單位的文言的基礎上。 今天的新詩創作語言文字基礎卻是基本以兩個字以上的詞為單位的口語, 用口語來寫五言七言詩就必然比用文言來寫還要限制大得多。” (何其芳: 《話說新詩》, 《文藝報》, 1950 年第4期) 現代漢語作為新詩語言帶給新詩的“限制” 正是如此: 散文化的句式、 蕪雜的語匯和日常化、 應用型的表達方式。 這些不僅制約了新詩格律的生成, 而且給新詩創作本身提出了挑戰。
面對語言的“先天” 困境, 優秀的詩人總會從上述限制出發, 通過精心錘煉、 鍛造, 探尋能夠彰顯現代漢語特性的詩歌形式及格律。 事實上, 新詩在草創階段即已體現了這種努力, 如沈尹默的《月夜》 (1917 年)、 康白情的《和平的春里》 (1920年) 等。 《月夜》 被認為是新詩史上“第一首散文詩”, “其妙處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此為1919 年的《新詩年選》 中“愚庵” 所撰的“評語” ), 其實該詩的“妙處” 便在于現代漢語虛詞的巧用:
霜風呼呼的吹著,
月光明明的照著。
我和一株頂高的樹并排立著,
卻沒有靠著。
全詩只有四行, 每行末尾有一個“著” 字, 這構成了此詩在外形上的突出特征。 這四個“著” 字的恣意鋪排, 恰好成為引發詩意的源泉: 一方面, “著” 字放在每句的尾部, 在整體上起到一種很好的平衡作用; 同時, “著” 的降調音節顯示某種堅韌和執著, 實現了與詩的主題相得益彰的效果。 類似的如《和平的春里》, 其句末虛詞“了” 字的運用與《月夜》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給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當代詩人昌耀的詩歌, 其詩作的某些句子顯得冗長, 如《冰河期》 里的一句—— “在白頭的日子我看見岸邊的水手削制槳葉了” ——共有19 字之多, 不過其中聲音的起伏規律是可以進行的, 原因就在于詩句間形成了一種內在韻律組織。 確如研究者分析的: “為了凸現質感和力度, 他(指昌耀——引者) 的詩的語言是充分‘散文化’ 的。 他拒絕‘格律’ 等的‘潤飾’, 注重的是內在的節奏。 常有意……采用奇崛的語匯、 句式, 并將現代漢語與文言詞語、 句式相交錯, 形成突兀、 沖撞、 緊張的效果。” (洪子誠、 劉登翰: 《中國當代新詩史》 (修訂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這是現代漢語特性在詩歌中的創造性展示, 同時從另一角度表明, 對于新詩來說, 外在的聲音確實不再重要了, 而應該使節奏、 音韻等要素“內在化”。
這種“內在化” 將對新詩格律的探索導向語言的更深層面。人們常常引用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一句名言“詩是翻譯中失去的部分”, 來說明詩歌聲音的重要性。 不過, 一些詮釋者樂于將“失去的部分” 理解為外在的音韻或聲音。 誠然, 一首西方詩歌被翻譯成漢語詩歌, 亦即經過了一種語言間的轉化之后, 原有的聲音、 韻腳確實難以保留, 可是倘若細究下去會發現, 弗羅斯特的“失去的部分” 也許更符合俄國文論家巴赫金所推舉的“語調”。 在巴赫金看來, 由于“生動的語調仿佛把話語引出了其語言界限之外”, 因此詩人們應“掌握詞語并學會在其整個生涯中與自己的周圍環境全方位的交往過程中賦予語詞以語調” (巴赫金: 《生活話語與藝術話語》, 《巴赫金全集》 第二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他所說的“語調” 是詩歌中的綜合的喻意或韻味, 超越了一般意義的節奏、 音韻。 按照巴赫金的看法, 一個語調放在不同的語境里會生出不同的涵義, 因此語調既包含了詩人的情感和體驗, 又是滲透在字里行間的一種特別的上下文關系, 甚至它還包含了傾聽。 “語調” 對一首詩的個性的展示十分重要, 它也許是風格意義上的, 但又似乎超出了風格的范圍。
在很多人的閱讀經歷中, 大概常會遇到這樣的情形: 一首詩從外形看可能是十分雜亂的, 但讀過之后卻會產生某種強烈的感覺, 這主要是隱藏在其中的語調發揮著作用。 正是語調, 把一首表面蕪雜的詩作貫通起來而激活了其內部蘊藏的力量。 與之相反的情形是, 一些表面上很有節奏、 朗朗上口的詩作, 其內里實則空洞無物, 枯燥乏味。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情形提示人們, 對于詩歌的語調要仔細辨析—— “傾聽”。
不過, 這“傾聽” 卻不是朗誦意義上的傾聽, 而是用感知與心智之耳去聆聽。 弗羅斯特本人盡管非常強調詩歌的聲音, 但他心目中的聲音是多層次的, 更多地建立在語調的基礎上。 人們常常認為他是一個自然詩人, 然而正如詩人布羅茨基所指出, 弗羅斯特詩中的自然是“詩人令人可怖的自畫像” (布羅茨基:《文明的孩子》, 劉文飛等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9 年版), 這里“可怖” 的涵義不僅僅指弗氏詩歌的主題, 而且更指其詩的語調, 布羅茨基顯然是從語調上“聽” 出了弗羅斯特詩歌的“可怖” 的。 比如, 弗羅斯特很多寫田園風光的詩作采用了一種輕快、 詠贊的調子, 但那些詩里更為深層的意蘊, 是一種非常悲觀的對自然、 生命以及無形的恐懼, 滲透了一種強烈的悲劇意識。 人們往往忽略了他詩中那一層不易被覺察的語調, 一種深沉的悲音。
遺憾的是, 很多詩人雖然也懂得把自己的語調放進詩里, 卻只將注意力停留在表層的字音的協調與順暢上, 更為深層的語調未能建立起來。
3. 探求可能性
因此, 從現代漢語特性來說, 建立新詩格律的可能之途在于: 舍棄一種形式化的外在的音響, 代之以深入到聲音的內在層面進行探究。 正如不少人意識到的, 新詩格律的問題不可能“一次性” 獲得解決, 與其提出一個一勞永逸的固定構想, 不如比較一下這其中發生了什么變化, 并從實踐出發分析一下格律建構的可能性。 從以上分析可知, 今后新詩或許是一種包含了語調的寫作, 而不必預設某種固定的韻腳和音節。 或許那樣的寫作,才真正地回到了格律的本義:
格律是形成整齊的節奏、 從而發揮表現媒介(語言文字)底性能的方法或工具, 它應當使內容起更大更深的作用, 所以必須是整首詩底有機的功能或有組織的力量底源泉……格律在一首詩里的作用乃是使語言作有秩序的、 合乎時間規律的、 有組織的進行。 (孫大雨: 《詩歌底格律》, 《復旦學報》 (人文科學版),1956 年第2 期、 1957 年第1 期)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 自由體詩占據了新詩創作的主流, 但也有相當一部分詩人體會到形式、 格律的重要性。 人們開始辯證地看待格律的意義: “格律當然不是產生好詩的保證, 同樣自由詩也不是; 但格律是一定程序上不可或缺的‘組織大綱’ ……正是格律探索使新詩在更高的層次上認識到: 任何文學樣式均有其特征的規定性, 否定了其特征規定性也就是否定了此種文學樣式本身; 新詩可以沒有固定的形式, 但不能缺失形式意識。”(龍清濤: 《新詩格律探索的歷史進程及其遺產》,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04 年第1 期) 其中, 宋琳、 王寅、 西渡、 朱朱等新一代詩人的詩歌觀念和創作實踐, 便顯示了這種意識。
對于這些年輕詩人來說, 至關重要的是: 一方面, 他們受到戴望舒、 艾青、 穆旦、 昌耀等前輩詩人的啟發, 領悟到新詩格律內在化的趨向; 另一方面, 他們從聲音的復雜內蘊入手, 有意識地在其詩歌創作中調配多層語調。 例如西渡詩歌中對雙重聲音的設置: “一個人曾經歌唱∕現在他一聲不響——” ( 《悟雨》 )、“在拐角處∕世界突然停下來碰了我一下∕然后, 繼續加速, 把我呆呆地∕留在原處” ( 《一個鐘表匠人的記憶》 ); 桑克詩歌中語詞的變調處理: “在鄉下, 空地, 或者森林的∕樹杈上, 雪比礦泉水∕更清潔, 更有營養。 ∕它甚至不是白的, 而是∕湛藍, 仿佛墨水瓶打翻∕在熔爐里鍛煉過一樣” ( 《雪的教育》 ); 以及朱朱詩歌中韻律與色調的調配:
雨中的男人, 有一圈細密的茸毛,
他們行走時像褐色的樹, 那么稀疏。
整條街道像粗大的薩克斯管伸過。
有一道光線沿著起伏的屋頂鋪展,
雨絲落向孩子和狗。
樹葉和墻壁上的燈無聲地點燃。
我走進平原上的小鎮,
沿著樓梯, 走上房屋, 窗口放著一籃栗子。
我走到人的唇與薩克斯相觸的門。
——朱朱《小鎮的薩克斯》
這首仿佛一幅“印象派” 油畫的詩作, 以單純的布景和簡潔的線條勾勒了小鎮上寧靜、 安詳的景象與氛圍; 它又宛若一支悠揚宛轉的薩克斯曲, 詩中的情緒隨著曲調的高低緩急而波動起伏。 薩克斯管是此詩的核心意象, 它對應著小鎮的街道, 不僅詩中的各種人、 物圍繞它而聚合在一起, 而且全詩的節奏也與它彎曲的形體保持了一致。 作者似乎有意克制自己的筆觸, 小心翼翼地不讓語言之流恣肆向前。 在雨絲等意象的映襯和變幻光線的照射下, 全詩的色調顯得十分柔和; “鋪展” 和“點燃”, “小鎮”、 “唇” 和“門” 等詞, 交織成了一種特別的韻律。 這些創作實踐, 無疑拓展了新詩格律探索的路徑, 體現了新詩格律從閉鎖到敞開的趨勢, 令人對新詩格律的可能性充滿期待。
或許, 新詩永遠無法獲得像古典詩律那樣“固定” 的格律,卻始終應該保持現代意識燭照下的對形式的追求。
從開闊的視野來說, 新詩格律問題集結著傳統(古典) 與現代、 本土與西方、 自由與規范等一系列相互糾纏的命題, 既有持續的歷史和理論沿革, 又頗具創作實踐的指導意義, 還關涉新詩的未來建構。 顯然, 這一研究將有助于澄清新詩發展中自由與格律相對峙引發的一些問題, 表明自由詩與格律詩這兩條新詩主脈, 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可以互相參照、 彼此啟發的。 從更深層面來說, 新詩格律折射出一種悠遠的民族文化心理(這從近年來舊體詩詞創作活躍即可看出), 它畢竟與深厚的古典詩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而且一度被視為新詩重返文學中心、 重溫古典輝煌的切實可靠的途徑。 因此, 對于新詩格律問題的深入研究, 亦可被納入當前的文化探討與建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