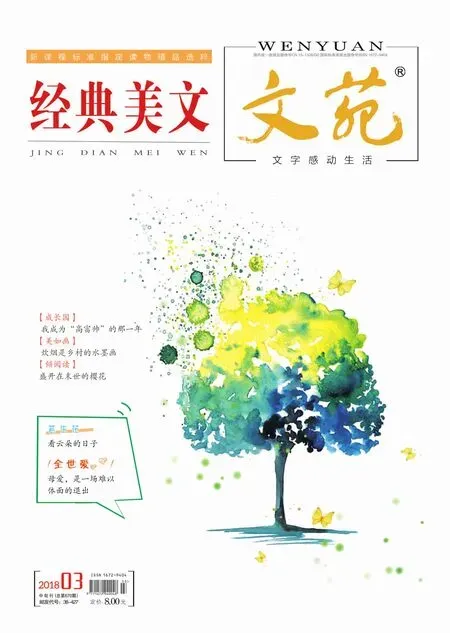帶刺的手
文/劉向武
那是一雙帶刺的手,平凡而又粗糙,可就是那雙帶刺的手讓我懂得了人間的幸福。
“媽,后背癢癢,給我撓撓。”媽媽慈祥地笑了,她用左手撩起我的背心,把右手平放在我的后背上。
“哎喲!”我叫了一聲,媽媽的手上好像長滿了刺,扎得我反而疼了。
“媽的手是干活時磨的,長了很多老繭。沒事兒,媽輕點給你撓。”我皺起眉頭又齜牙咧嘴地忍著,撓完后雖還有些刺痛,但溫暖的幸福從后背擴散到了全身。
1996年年前的一個晚上,我突然發現左眼幾乎什么也看不到了。“媽,媽,我左眼看不見東西了。”
看到我要哭的樣子,媽媽焦急、關切地問:“咋回事,你左眼咋了?”
無望、恐懼的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媽,媽,右眼還好好的,左眼看不見了。我是不是瞎了?”
媽媽用她帶刺的手為我擦了擦眼淚:“能看見那個燈泡不?”
我堵住右眼試了試:“能倒是能,除了燈泡,看見的都是黑的。”
媽媽的淚水似乎馬上要流出來,卻不知被什么東西阻擋著。“咱明天就去醫院,現在醫院啥不能治,你的眼睛肯定是小問題,沒啥大事兒,你別著急,明天咱就去醫院。”
“那我上不了學了啊。”我抽噎著,把心中所有的恐懼都讓媽媽知道。
“沒事兒,等看好了病,再上也不遲。明天咱就上醫院,早點兒看好病,就能早點上學了。”
我雖然有些將信將疑,但心中的恐懼和擔憂已經消失了一大半。
還記得在求醫問藥的奔波中,過馬路時媽媽緊緊地牽著我的手,左看看右看看,生怕有車撞著我;還記得在手術前的幾分鐘,媽媽用她那雙帶刺的手輕輕地撫摸著我的頭,靜靜地看著我的眼睛說“沒事兒,別害怕,啥都有媽呢”;還記得在養病時,媽媽一口一口地給我喂飯,高興地說:“長胖了,臉也養白了,再過不長時間就能看東西了。”
上高一時的那年冬天,我給媽媽送飯。廠房里的溫度很高,又熱又悶。“媽,我給你送飯來了。”媽媽放下鐵鍬,從廠房出來。她渾身濕透了,汗水不停地往下滴,臉上黑黑的。“正好餓了。”她喝了一大口粥,拿起筷子,打開飯盒,“嗯,挺香,炒豆角。”
我急著說:“媽,別在這兒干了,熱死啦,連口氣都喘不上來。”
媽媽吃了幾口菜,嘆了口氣,“唉,現在也沒個好活。在這干得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沒事兒,你好好學習就行了,其余的事兒有我和你爸呢。”她大口大口吃了起來,吃得很香,仿佛那炒豆角是天下最好吃的菜。
我看到她那雙帶刺的手幸福地舞動著,手指頭黑黑的,粗粗的。
2002年,我考上了大學。媽媽從櫥柜里拿出個方便面袋,高興地說:“你就要上大學了,幸虧咱家還有這點兒錢,要不還不知道管誰借呢。”她拿出錢很自豪、很欣慰地點了點:“給你4500,家里還剩下200塊錢,你不夠了就來個電話,下個月我就開工資了。”
我看到那4500塊錢,心里沉甸甸的。“媽,我看病花了不少錢,再加上我和我哥這幾年的學費、生活費也不少,咱家哪來的這么多錢?”
媽媽得意地說:“光靠你爸那點工資咱家早餓死了,咱家是誰想上大學就讓誰上。錢的問題你們別考慮,你爸不行我還能掙點兒,掙不來借也得供你們上。”
大學四年里,我記不清媽媽為我和哥哥的銀行卡上存過多少次錢,也記不清媽媽多少次叮囑“在那邊要吃好,要好好學習”。我知道,媽媽那雙帶刺的手為我們操勞的時間是一輩子。
如今我遠在他鄉工作,可我多么想回家讓媽媽給我撓癢癢!那雙帶刺的手,蘊含著人間最美好的溫暖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