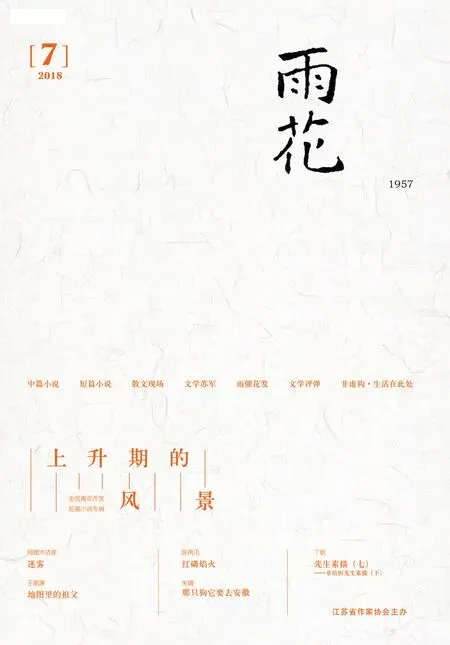紅磷焰火
陳再見
女孩我不認識,長得也不漂亮,不過有一個樸素又好聽的名字,叫素如她是我朋友的朋友,那天我朋友生日,在洛洲錢柜唱歌,朋友叫上了他覺得應該叫上的朋友,也不算多,十來個人,我有幸能被叫上,覺得很有面子。那些人當中,有我認識的,也有我不認識的,比如素如,那晚她唱了幾首英文歌把在座的人都震住了,不過也沒人知道她唱得對不對。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我剛離婚,租住在關外。出租屋隱藏在一條陰郁的巷子里,兩邊開有童裝、文胸內衣和潮州人經營的佛具香燭店面,半夜三更仍亮著紅燈放梵音,還有敗落的中草藥鋪。白天異常嘈雜,只有到深夜才能闃靜下來。我一個人住。一個人住是件挺煎熬的事情,一面渴望朋友來,說說話抽煙喝酒,一面又害怕門鈴響聲,以至于后來我干脆把對講拿開,讓它拖著長長的線耷拉在地上,手機也長期調了靜音,拒絕一切預示著將會被打擾的聲響有一件事卻是例外。隔壁大概住著一個瘋子,他總是在深夜大聲朗誦,不用中文也不是英語——我沒讀幾年書,卻也知道英語怎么發音。那應該是另一個國家的語言,完全超出我的經驗之外,甚至,有可能還是他自創的語言。他每天夜里都要朗誦一小時,聲音又大,簡直有點聲嘶力竭,都能想象他滿臉通紅、嘴角泛沫的情形。我試圖去結識他,我可不在乎他是不是瘋子,或者在旁人眼里當時的我跟瘋子也沒什么兩樣。
上蛋糕時,要點蠟燭。朋友打著火機,卻被素如叫住了,她說不能用火機點得用火柴。誰身上還帶火柴啊?我有啊,只見素如從兜里掏出一盒火柴,推開火柴盒子,翹起小指,從里面捏出一根火柴,嚓的一聲在盒側擦燃,火柴磷頭嗞的一聲,像是一團微小的煙花,就那樣燃開了,空氣中瞬間彌漫了一股好聞的硝煙的味道……我從沒有見過有人能那么優雅地擦燃一根火柴,簡直讓人著迷。
我端了個矮小的茶杯過去敬素如,禮貌而卑微的,我說很高興認識您。
KTV嘈雜,她似乎沒聽清我的話,不過還是點了點頭,和我碰了杯。
后半夜,幾乎所有的人都喝倒了,他們橫七豎八躺在包廂的沙發上,像是一幅文藝復興時期的寫實壁畫。素如唱了最后一首歌,我沒聽過,她晚上唱的歌在我這里幾乎都是陌生的,大概是年代的隔閡,想想也不盡然,把兩只小白鼠放在同一個盒子里,它們也會以各自的姿態生活。在這個幾乎可算是一鍋大雜燴的城市里,西餐廳的樓下就是大排檔,川菜館里的服務員有可能跟你說粵語,站在大街上,你右眼看到的是咖啡廳落地櫥窗里精致的男女無聲地對視,左眼看到的是兩個環衛工人為爭一個紙皮箱吵得口角泛沫幾欲動手……素如應該會是時常帶著蘋果筆記本出現在咖啡廳二樓位置的那種女人,臨著玻璃窗,偶爾也扭頭看看街上的人。
素如關了音響,回頭看見我在低頭喝水。我戒酒好幾年了。聊點什么吧。我說。素如走過來坐在我身邊,她身上有股火柴磷頭的香氣。
“聽說你也是潞城人。”她那么隨意一說。
我點了點頭。我沒想到我們還是老鄉,不過也沒什么值得驚奇的,潞城離深圳太近了,我住關外時,回一趟潞城比跑一次市內的時間還快,有人說,隨便在大街上喊一句潞城話,起碼能找到一半老鄉——也許再過幾年,這個大胃口城市很快就會把潞城給吞并了。
既然都是潞城人,倒也輕松了不少,至少不用再別扭地說著普通話了。
——有一天深夜,我拎著一個酒瓶子去敲隔壁的門,他剛結束朗誦,屋里一派寂靜。我在門口站了有幾分鐘,始終不見有人應,他可能睡著了,我這么想,又堅持站了一會兒,莫名其妙,如果有人上下樓看見了,還誤以為我在干什么,像是某個酒鬼半夜頂著人家的門板撒尿。后來我就沒再去敲門了。有一段時間,朗誦停止了,隔了半個月,突然又開始了,讓我十分驚喜;某一天,又停止了,于是就再也沒有開始。我問了住在頂樓的房東,房東說,具體也不太清楚,據說那人還懂些文墨,好像是喝醉了酒,半夜下海里游泳,淹死了。
我租住的那條巷子正好與海岸線組成筆劃懸殊的T字型,有時半夜能聽見海浪聲,如果福永機場的飛機剛好停歇下來的話。不過后來再也聽不到了,11號線地鐵剛好沿著海岸從巷子口的位置鉆出了地面,如西方驚悚片里那些駭人的龐然大物。
我跟素如講起這些陳年舊事,幾乎是在坦露心胸,如面對的是多年的好友,我對陌生的言語有著一種病態般的癡迷,它們高貴而遙遠。我試圖模仿瘋子發出的幾個音節,希望素如能辨別出那是哪一個地區的語言。可能是我沒模仿正確,她也聽不出來,她認為,既然是個瘋子,自創一套語言的可能性更大。
我們把包廂的門關好,移步到大廳喝茶。有兩個喝得爛醉的中年男人站在門口的臺階上吹牛誰操的女人更多,他們讓我想起,白天去深房廣場的招商銀行辦事時,那位執意在候位座上抽煙的男人,他們都面容模糊,看起來像是同一個人。
素如明顯接收到了我的誠意,她開始松弛,表達輕柔而清晰,她說她從小在潞城長大,來深圳還不到一年——你知道,小城里長大的女孩都有種天然的優越感,如果有一家鄉下親戚,那種優越感就更強烈了,我們不妨把農村想象成一幅彩色的黑白圖畫,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它表面上是彩色的,實際上又是黑白的,然后你搭著小中巴一路進城,顏色一路在黯淡下去,小城的公路、舊樓、工廠、人群……其實都不及農村色彩豐富,可它在你的意識里卻是粲然多彩的,你知道這是為什么嗎?
因為燈火。
她明顯吃了一驚。對,小城的燈火,你跟我想一塊去了。她時不時掏出火柴,擦燃一根,看著小小的焰火燃完,剛好燙到手時,她便用拇指和食指把火苗揉滅。她似乎并不感到灼痛。你看,這就像是小城的燈火,在大城市的霓虹燈下,輕易就能被泯滅了。
我對潞城的印象跟素如不一樣,至少沒有那么深的歸屬感,我的父親從小告誡我,我們來自鄉下,也就是說,如果不是父親的奮發,我們一家就是素如眼里的“鄉下親戚”,甚至連親戚都攀不上。
她說起她的父親。
父親以前是化肥廠工人,好長一段時間她在學校都不敢跟同學們談論起父親的職業,她覺得當一個挖煤工人都比在化肥廠強,至少不會跟農民有那么直接的聯系,有時父親下班繞路去軍潭小學接她,他穿著一身灰色、肥大的化肥廠工作服,散發著一股很濃的肥料氣味。她會故意溜走讓他在學校門口等半天。回到家,父親似乎也不怎么責怪她,他們只是清淡地說一句“怎么沒看見”。他慢慢地就不再去接她了,其實還是心知肚明的。唯一讓她覺得舒服的,是父親在院子里種了好多花,薔薇和炮仗花爬滿圍欄,還有杜鵑、山茶花、月季牡丹……更多的只有父親能叫得出名字。父親每天都從化肥廠揣兩兜復合肥回來,盡可能平均地撒給花卉,接著開始澆水、修剪、松土,他每天花在上面的時間多到有點讓人煩。素如說,她母親至少要喊上三次,父親才愿意洗手,進屋吃飯。母親說,你爸認那些花花草草作家人就夠了。
這個父親形象聽來倒是熟悉,我小時候在潞城每天都能遇到,他們來自化肥廠、酒廠和糖廠。
“我爸算是個粗人,他在化肥廠里什么重活都干,被人呼來喊去的,可他一回到家,就成了花藝師,輕易叫不動他了。”
“現在呢?”我問。
“很早就去世了,肺病,現在想來應該是職業病,可當時還沒有這種說法,人病了,工作也就沒了。我媽又是個清高的人,拉不下臉去打工,也沒怎么打算讓我爸去住院,似乎就等著他死。我記得最困難的時候,我媽把我爸種的花全部拉去龍山橋頭,沒幾天就把一院子花都賣完了。大家似乎早有耳聞,化肥廠的老蔡是個種花高手。你知道,我們那里別的沒有,花市倒是遠近聞名,大家沒事就喜歡種點什么,龍山橋頭一到傍晚就聚集好多老頭在為幾個枯樹頭估價——有一天,我爸躺在床上吩咐我給院子的花草澆水。我直言,它們都讓我媽給賣了。我爸兩眼一翻,淚水滾了出來,沒多久,就死了。他死后第二年,化肥廠也停了。”
我問化肥廠在潞城什么位置。
她說就是現在的城北開發區。
她笑話我是個假潞城人。
離婚后,我確實有幾年沒回去過了。
大廳里的茶越喝越苦,我約她到外面走走,她同意了。我們沿著迎春路往南華街方向走,橫穿嘈雜的十字路口,二十分鐘便能到南華街,街邊有小公園,有各種攤檔,吃烤魚烤雞,還有羊肉火鍋,我想請她坐下來吃點東西。拍拖的男女都喜歡夜里出來吃點東西,有風,枝葉在頭上擺,公園里的小池映著燈光,水當然是濁的,漂著成片成片的枯萎的荷葉和銅錢草,不過夜里看不出來。大概也是誤判,也許說著話忘了時間,我感覺到達目的地的路十分漫長,尤其是下半夜,巷子里幾乎沒遇到一個人,我不知道素如心里是否對我有提防,或者后悔答應我出來走走的建議,但她表現得很從容,甚至向我要了根煙,熟練地抽了起來,還時不時踢掉路上某顆石子。
她每隔一會兒就要擦一根火柴,像是一種強迫癥,我估摸著她想把手里的火柴擦完。
她說她在一所民辦學校當音樂老師。她說了學校的名字。我聽說過那所學校,離這有點遠,幾乎可以說是在郊區。我有點擔心她如何在下半夜回到她的“郊區”,我的擔心也許是多余的,甚至為此我還有了些陰郁的竊喜。
她問我在深圳干什么。
我說我在倒賣軍火。
然后呢?她一臉正經。
然后,有時間還干點拐賣婦女孩童的活。
她笑得雙手捧著肚子,蹲在了地上。
我們竟然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那迷宮一樣的巷子,我們都不是這里的熟客,分辨不了方向,走著走著又回到了原地。素如倒不緊張,一直在笑,她覺得兩個大人竟然迷路說出去會挺好笑,她還添油加醋,跟我說起潞城以前是座山寨,好多年前吧,就幾十戶人家,占著地,四周筑了五六米的高墻,寨子里出惡人,經常到外邊搶奪年輕女孩,搶了扛進寨子,當壓寨夫人,或者丫鬟,最慘就是做妓女,每天被好多人睡……這些十有八九是素如編出來的,她問我是不是跟寨子里出來的人那樣,見了女孩就想拐跑。我說我十八歲之前沒敢跟女孩說話,覺得她們陌生而遙遠。
她說她平時喜歡寫點小故事,報紙副刊有時會登她的小文章,她拿著稿費單去郵局取錢,工作人員用鄙夷的眼神看她,大概因為她的單子都只有幾十塊錢,她就用自信滿滿的語調回道,你們這一輩子可能都拿不到稿費。
我說,那你是想當作家啰。
她說,不是,我只是想做點好玩的事,就像當年我爸喜歡種花草。
那天晚上后來就不了了之了。我忘了我們到底是怎么走出那片迷宮一樣的巷子,最后還把方向搞反了,就是說,我們并沒有去到南華街邊吃東西,想想是蠻遺憾的事情。我們應該是又折回到了錢柜。后來的事我忘了,我們是怎么分開的,分開前還說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她把身上帶著的火柴擦完沒有。
我小時候覺得潞城很大,光我家居住的城北六社就大到沒邊,城北城南就隔著中間一條螺河,螺河也大,水深,應該比現在清澈些,兩邊的石條階梯蹲滿洗衣的女人,白色泡沫順著河水往下流,在過橋洞前匯合。我們城北的孩子很少過橋去城南玩,城南的孩子輕易也不會過城北,那時我站在城北的橋頭望見對面國營酒廠高高的廣告招牌上寫著“螺河大曲”四個大字,感覺像是望著另一個陌生的城市……軍潭小學在城南,也就是說,我打小就不可能跟素如有碰面的機會。我就讀的紅星小學在城北國道邊上,從我家到學校只需要橫過國道,家人每天都擔心我會被國道上的汽車撞死,幸好六年小學讀下來,我的同學被撞死了好幾個,我卻安然無恙說起來命還算大。我猜想童年的素如也不會過來城北玩耍,尤其是女孩子她們都喜歡躲在家里和大人的屁股后面——開發區在城北,也就是說,如果素如沒說錯的話,當年的化肥廠就在城北。我因此覺得素如和我有了些聯系,至少她爸跟城北有了些聯系這很重要,像是一種緣分溯到了源頭盡管有些牽強,且還自作多情。
我的自作多情卻遇到了麻煩。按理說,在一個朋友圈里,和一個人認識了,就不可能丟掉,只要我愿意我大可以繼續,打聽她的聯系方式甚至去她工作的學校找她——可就這樣奇了怪,那個叫素如的女孩我再也找不著了,仿佛憑空消失了一般。我找那天生日的朋友打聽,他蠻疑惑說他的朋友里沒有一個叫素如的,也沒有一個是在民辦學校當音樂老師的,我只能以一個全程清醒的角色幫他回憶現場,我說到火柴,紅磷突然被擦燃的那一瞬間,空氣里飄滿了硝煙的味道……朋友搖了搖頭,說,沒印象,那晚喝得實在有點多,再說了都什么時候了,誰還隨身帶盒火柴啊還是個女孩子。
我竟也無言以對。
也許我遇到了一個刻意隱瞞的人,要么就應該解釋為一場夢了。
我又開始喝酒,酒精像糞坑里的蛆蟲,在記憶的癰疽里蠕動。我對關外那條小巷子的記憶,除了朗誦的瘋子,剩下的便都是嗆人的酒精,之所以搬離巷子,一是瘋子的死,二是為了不再酗酒。有幾年時間我一直在深圳周邊游蕩,像個無業游民,我想學一門手藝,不至于在不遠的將來會被餓死,或者像隔壁那樣成為一個怪異的瘋子,最后淹死在海里。我尋思著學什么好,自然要挑一個在可知的未來里不會失業的活,想來想去,除了當理發師,就是去西鄉幫哥哥做糕點,可悲的是,我完全能預知一旦成為這兩者之一的生活是怎樣的無奈與無趣。我還是想自在一點,便嘗試著與郊區農民做點小本生意,看起來又是那么的無所事事,我販賣過芋粉腐竹、生蠔、雞樅,還有鯧魚,認識我的人都叫我陳老板——市里來的陳老板。我把收購好的貨物都倒賣給市內的特色餐館,剛開始賺得不算多,夠糊個口,反正我也是一個人,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后來生意面逐漸打開了,有好多賣概念的小餐館都靠我供貨,那些年大家都追求綠色原生態,菜葉子沒被蟲子啃過還沒人要,黃瓜和香蕉也喜歡瘦不拉幾的,給圓潤飽滿的,他們還懷疑打過催生激素。我以低價收購農民的次品,轉身拉到市里卻能賣個好價錢,因而賺了點錢。我再三跟和我合作的郊區朋友說,千萬不要施肥,也不要殺蟲,播了種子就不要理睬,放著野生就行了。
很快,趁著市外的房價還沒漲起來,我買了房子。買房已經把我賺來的錢花得差不多了,為了省錢,我請了街頭的游擊隊,做了簡單裝修,不過房子太大了,又裝修得簡單,顯得十分空曠。我最終沒有搬進去住,把它租給了一對在富士康上班的小夫妻。我呢,繼續游蕩,我喜歡聽周邊差異巨大的方言,白話、畬族話、客家話、潮汕話、福佬話……有時,我感覺自己在人群當中,像是一個不守規矩的小丑,大家都排著隊,我卻在這個隊站一下,煩了,又跑到那個隊站一下,我大多時間就浪費在隊伍的更換中,最終也沒能等到其中一個隊伍有輪到我的時候。
沒過幾年,我的小本生意就被擠兌掉了。這很正常,開始時我便能預知。
我在紅嶺村租了一間很小的房子,不足十平方吧,里面什么東西都沒有,除了垃圾,我沒有隨手清理垃圾的習慣,抽過的煙,嗑過的瓜子殼,幾乎能當一層地板。我白天不在家,夜里才回去,大燈壞了,我也懶得修,就點根蠟燭,發呆,抽煙,看手機,然后鉆床上睡覺。我發誓第二天一早一定要打掃衛生,像個人那樣活著,可是第二天,我依然醒不來。每個月1號,我的租戶會把租金轉我賬號上,我用那筆錢的三分之一付我的租金,剩下的剛好夠一個月的生活費。
我的前妻不知道從哪里打聽到我買了房,好幾次找我要兒子的撫養費,我當然不會給,也給不起,況且離婚時我們已經說好,兒子親她,歸她撫養,我把父母一輩子靠倒賣橡木家具換來的潞城的三層樓房都給了他們。我也知道,離婚沒多久,她便把糾纏多時的相好接到了家里,那個整天無所事事到處賭錢比我還爛的男人,我們其實打小就認識。我不知道她究竟看中了他哪一點。他們是在麻將桌上認識的,沒多久便在床上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既然事情都發生了,我也承認作為一個男人的失敗,我可以成全他們,我又不是那種不能好好說話的人。是我主動提出了離婚,她還死活不肯,說沒那回事,是鄰里造的謠。而我一提出房子和孩子都歸她時,她便不再哭鬧了,像是小孩得到了想要的玩具。一切大概都是那個油頭粉面的男人的詭計,慫恿她向我要撫養費的主意,應該也是他的意思。他肯定又在哪里賭輸了錢,保不準回家就揍了母子一頓。奇怪的是,我并不心疼,包括兒子,我才不傻,我只是還沒遇到適合的女人。我大概也是可以重新建立家庭的,雖然一直沒抱多大的希望。
遇到素如時,我已經四十了。四十歲這年,是朋友的生日讓我重獲希望。我開始習慣照鏡子,定期去理發店剃頭刮胡須,我看起來還算年輕,身材也保持得不錯,沒有發福,也不枯瘦,我在家里邋遢,出門還是會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凈,看起來像個蠻有教養的人,素如一定也覺得我是個蠻有教養的人,否則也不敢大半夜和我走那么長的路,說那么多的話。關鍵是,我在深圳還有一套大房子,即使一事無成,我靠它出租也能過好這輩子。
我幾乎隔幾天就會去素如所說的那所位于郊區的民辦學校門口等她,等放學時間,等學生被家長一個個用小車接走,再等老師們開著小車陸續離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是沒有素如,越到后來,我幾乎越堅信,我被她騙了,但我也堅信,我只是被她騙了,至于她這么個人,肯定還是存在的,接受被騙比接受一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要容易得多。我就那樣自欺欺人的,繼續等了下去。慢慢有家長跟學校投訴,他們懷疑,他們有理由懷疑,我可能是人販子,或者干脆就是個瘋子,我不應該時不時出現在校門口,應該把我攆走。學校有人出來跟我談話,他們在試探,我是不是瘋子,他們問我吃飯了嗎?我說吃了。他們問我在這里干什么。我說在等人。他們問我等誰。我說我等了這么久也確實不知道我在等誰了。最后一個問題的回答大概把我出賣了,或者是因為聞到了我身上濃烈的酒味他們一致認為,我是個瘋子,即使不算瘋子,也是一個酒鬼。他們要我離開,我堅持不走。他們報了警。兩個警察開著警用摩托車來到我身邊,不由分說,就給了我幾棍。
我在沙地里醒來時,發覺身上手機什么的都不見了,頭上的血也凝固了,像是身上長出來的疤。我從地里爬起來,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大概已經是深夜,遠處的人家也沒有幾戶窗戶是亮著的。我不知道被丟在哪里過的夜,只能朝燈火處走,走了幾步我就看到了遠處海面上的油船,于是才醒悟過來,眼前就是瘋子淹死的地方。我順著海岸往西走,跨過馬路很快就進入了我租住過的巷子。我很驚訝,幾年不見,這里發現了一些變化,童裝店文胸店中藥店和潮州人開的佛具香燭店都不見了,它們裝修一新,敞著大門,亮起紅燈,看樣子會通宵營業。我路過每一家店面的門口都能瞥見里面歪歪斜斜坐著或躺著幾位姑娘,她們敞胸露腿,眼睛隨著我的腳步移動。我想我到這里來干什么呢,身上又毫無分文,我是想進去,抱住一個女孩在樓上舒坦一夜,第二天一早醒來,陽光剛好照進窗戶,福永機場的飛機依然會轟然而過。
過于狼狽的形象讓我失去了信心,事實上我不是一個膽小的人,下半夜的涼風已經把我渾噩的頭腦吹醒了。這里也不見一輛公交車,我步行回紅嶺村的想法太不切實際,對于一個極度疲憊與困乏的傷者來說,簡直有點殘酷。我不愿在眾人面前展露尷尬。所以,當我發現路過的鋪面只有一個女孩坐著待客時,我心動了一下,確實也只是心動一下。我并沒有停下腳步,繼續朝前走,如果不是她朝我招手,是的,她朝我招手了,像是遇到一個老熟人,她站起來打了聲招呼。她穿著粉紅色的長裙,上身可能裸露太多,有些涼,披了一件短小的牛仔衣,因為牛仔衣,使她整個形象都脫俗起來,如若一條鏤空的粉紅色長裙直撩撩地掛起來,大概也不會對我產生多大的誘惑力。
屋里粉紅的燈火讓人有種迷離的感覺,我早已忘記的傷口,又開始一陣陣痛起來,不過沒什么大礙,像是一個人身上某種程度的騷動。我說,你好啊,咱們認識嗎?我不知怎么就走進了院子里,并且拉了張靠背的凳子坐在了她對面。我想抽根煙,摸遍全身,沒找著,她丟給我一根白色細長的薄荷煙,我并不喜歡抽這個,但有勝于無,她也找不出更烈的煙。我們坐著抽煙。她看著我,職業地笑著,并沒回答我的問題。我想,我們并不認識,她只是在招攬生意。我的問題也太虛偽了點。
她長得跟素如有點像,或者說,我努力讓她們相像起來。
抽了一根煙后,她起身去關了拉閘門,店里確實只有她一個人。她問我,頭怎么啦?我說剛摔了一跤。她說,那先洗個澡吧。我點了點頭。我下身的家伙開始一點點硬了起來,它不像是我隨身攜帶的東西,它脫離了我的控制,早先一步實施了對事物的侵犯。這點讓我尷尬,起身時故意弓著腰,我不能讓她看出來。她還是詭異地笑了一下。
我約素如出去走走時,她也這么詭異地笑了一下。
我跟著她進了一間藏在臥室里的衛生間,衛生間里有一股好聞的薰衣草洗發水的味道,似乎剛被用過,空氣還是暖和的,她幫我脫了衣裳,不脫還不知道,一脫我感覺全身酸痛,她說你怎么摔成這樣,像是被人打的。我說就是被人打的,跑的時候又摔了。她似乎被我的幽默逗笑了,把溫和的手掌放在我后背的傷口上。
這是我洗過的最舒坦的澡,我一直背對著她,害怕直挺挺的家伙被她看見,她試圖把手伸過來,像是伸進洞里來想抓住鯧魚的頭,我別過身子,讓她夠不著。她并不堅持,她的全身都貼在了我的后背上,她不是那種大胸的女孩子,卻能讓人感覺到某種堅實的收斂的真實。我全身都在發抖,花灑的水是熱的,卻像是被人丟進了冰窟里。
大概產生了錯覺,我看見腳下的水有血淌了過去,滑過我貼地的光腳,是的,血混著水,我忘了我剛被人揍了一頓,身上還在流血。我說,血還沒能止住?她說你的傷口看起來已經結疤了。可地上的血越來越多,像是剛有人在洗手間里殺了一只雞。她這才驚叫了一聲,慘啦,怎么這時候來啦。來大姨媽了。她說。這事還真像一個嘲諷。
幸好,我也沒帶錢。我故作調侃,我們已經穿好了衣服,坐在她的床邊,能再給根煙嗎?她把整包煙都給了我。實在不好意思,她說,做不了大哥的生意了。可是我想在這里過夜,我哪也去不了了。火機壞了,煙沒點著。要不這樣,我用手幫幫大哥,大哥就饒了我這次,下次大哥來我給打個折。我說,你不要趕我走,我不會對你怎么樣,我就想睡一覺,抱著你,明天天一亮我就走。她并不愿意,她大概以為我在耍賴。我看起來也確實不像好人。她走出臥室,要去開拉閘門,我不想讓她這么做,她不應該一口認定我就是個壞人,我不過是想過一夜。我上前去拉她的手,她驚叫一聲,用另一只手扇了我一巴掌。打完,她更害怕了,快步沖到拉閘門,用手拍了兩下,拍到第三下時,她被我凌空抱了起來,我實在沒辦法,我必須得這么做,否則招惹來她的同行,她們肯定一致認為我是壞人,要命的是我還沒帶錢,沒帶錢怎么能來這種地方呢,誰不知道這是什么地方,那些躲在樓上打牌的保鏢肯定會把我揍一頓,順手扔進海里也不一定。
我把她扔在床上,她喊救命,我一拳頭下去,她立馬滿嘴是血,我后悔下手重了點,可也只有這樣,她才愿意靜下來,她渾身在抖,說,大哥來吧,我讓你做,不就是來月經了嘛沒什么大不了的,放過我行嗎?我搖了搖頭,我并不是這個意思,我的下身早就癱軟下去了,一想到她的下身就如同她滿嘴的血,我就一點興致都沒有了。我能怎么辦?她并不聽話一點都不信任陌生人。如若是這樣她就不該出現在朋友的生日宴會上既然出現,她更不該無端消失,讓我像個傻子一樣滿城游蕩,尋找她的蹤影。我說,你以為你躲在這里我就找不到你了嗎?你錯了,你不應該躲在這里,這不是你應該出現的地方,你應該在咖啡店二樓臨窗的位置上坐著寫字看書……
大哥,不好意思,我沒明白你的意思。她還想從床上站起來,我順手又給了她一拳,她就又安安靜靜了像個沒有生命跡象的充氣娃娃。
一進門我就問你,咱們認識嗎?你一直沒回答我。咱們到底算不算認識?
大哥,我認識你……
你當然認識我,我還知道你的名字,素如,素如,是不是?
不是的,我叫劉燕……
你還騙人。可憐的她又吃了我一拳,她實在不該騙人,都什么時候了
這下她很安靜了,除了大口喘氣再也不說一句話,我在她身邊躺下來伸手去抱她,我太累了,想睡一會兒就在半睡沒睡的時候,我隱約聽見她在說話,她說她認識我,幾年前,她還是個中學生,每天都在小巷子里進進出出,她的成績并不好,很快就輟學了。
一覺醒來,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她在我身邊躺著,我驚出一身汗。我努力回想那些年在巷子里可曾見到過她,顯然,女大十八變,我無法通過記憶搜索到她的容貌。況且燈光這么暗,她還化了妝,如今她又滿臉是血。
天還沒亮,我抖索著手去摸屋里的東西,實際上我想抽根煙,卻找不到火,我一個個打開抽屜找,去廚房找,去電視機后面找,去茶幾找,去冰箱頂上找……沒找著,我泄氣地坐在沙發上,第一眼看見她時,她也是坐在這個位置上。
我伸手摸到一個紙盒形狀的東西,拿起來一看,竟是一盒火柴。我固執地堅信這個城市只有素如才會隨身攜帶一盒火柴。我再次來到臥室,擦亮一根火柴去看她的臉,她的臉由于腫脹,血已經結痂,看起來倒跟一根火柴磷頭有點像,我不敢繼續看下去,似乎害怕印證出什么。我重新回到外面,又在沙發上坐下來,用火柴點燃煙,抽了起來,一根接著一根。我抽完了煙盒里的十根煙,我想天就要亮了,必須在天亮前離開。我用一根火柴擦燃的火湊近沙發的坐墊,直到火柴燃燒完了,燙著了我的手指,也沒能把坐墊點燃。我又固執地擦燃了一根,盒子里的火柴已經不多,我想如果擦燃所有的火柴都不能點燃,那就算了,我會從窗戶爬出去,改天再想辦法賠她醫藥費。湊巧的是,最后一根火柴,還是把坐墊點燃了。這事就不能全怪我了。趁著火勢還不算大,我快速從拉閘門的底部鉆出,幸好還沒有人這么早起來。
她就不該說她認識我。
我一路又跑回海邊,口中念念有詞,我竟然在朗誦詩歌,每一個音節的發音都和幾年前隔壁的瘋子一模一樣。要命的是,我還懂得它們的意思。這還真是一門自創的語言,它通行在另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