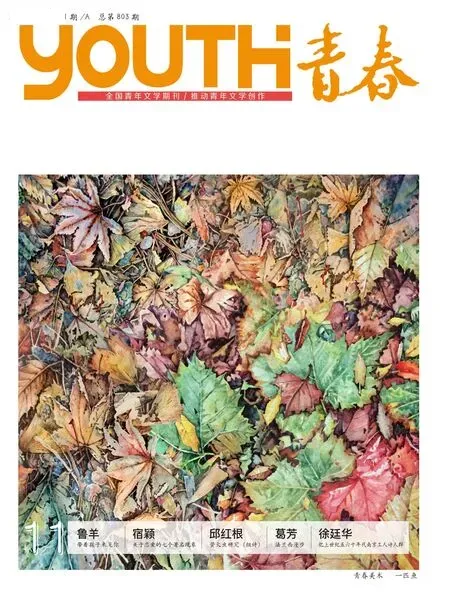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南京工人詩人群
口 徐廷華
有一道風景曾心心念念地縈繞在我的腦際,歲月倥傯,總也揮之不去。因為所有、過去了的,都會留下痕跡。
——題記
一
新詩百年,很自然地會引起人們的關注與回顧。對于新詩的成敗,向來眾說紛紜。對于新詩的處境,據我觀察,簡言之,是外冷內熱。民間曾調侃:十個寫詩的,只有一個在讀詩。形象地道出了目前詩歌的不景氣。
我以為,造成這種境況有多種原因,社會生活節奏的加快,娛樂形式的多樣,審美文化的多元,分化了部分詩歌讀者,使得一些人不再能心無纖塵地走進或厚重或輕盈的文學世界,去關注小說,關注散文,更莫說去關注詩歌,去讀詩,去體味詩中的韻味了。當然還有因新詩美學教育的滯后,導致讀者欣賞水平的亟待提高,而與新詩造成了隔膜與疏離。
而詩壇內部,卻呈現出熱鬧繁榮的景象。各種詩歌活動此起彼伏,特別是網絡為新詩提供了新的傳播平臺。詩藝的探索也在取得新的進展,中國新詩總體上是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但在轉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部分作者的詩作脫離現實,盲目地學習西方的現代主義,語言的朦朧、生澀難懂,令人如墜云霧之中,不知所云。
然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卻曾出現過第一個全民追捧詩歌的熱潮,寫詩讀詩,蔚然成風,詩歌被舉國關注,蔚為壯觀。隨著詩歌創作的蓬勃發展,詩人群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在大江南北,工農兵詩人成為詩界的骨干。像部隊的張永枚、未央、梁上泉、雁翼、星火等,農民詩人王老九、許茂功、霍滿生等。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而來的各行業的大發展,從工礦企業中也涌現出一批當年頗有影響的工人詩人。最早的有北京的李學鰲、王恩宇、韓憶萍,吉林的王方武、戚積廣、于德成,遼寧的曉凡、劉鎮,上海的居有松、鄭成義、福庚、謝其規,湖北的黃聲孝、李聲明,湖南的張覺,河北的白金,河南的李清聯,山東的郭廓,江蘇的孫友田,江西的萬里浪,貴州的成文魁等等。他們開一代詩風,是當年詩壇一道靚麗的風景。
就南京本土工人詩人群來說,在那個時期,也是風起云涌,凌云飛渡,競相綻放,各領風騷,星光燦爛。他們的詩作散見在當年南京僅有的《新華日報》、《南京日報》副刊和剛創刊不久的《雨花》文學月刊上,日后還繼續外延到上海的《萌芽》、北京的《詩刊》等刊物。
這一時期,被詩界熟知的有:南京分析儀器廠的王德安、南京第二機床廠的朱光第、晨光機器廠的蔡之湘、南京礦山機械廠的郭浩、南京汽車制造廠的辛明水、南京汽車離合器廠的曹念祥、南京手表廠的林鐘、南京化纖廠的凌大、南京標準件廠的關海晏、南京寶華山煤礦的徐延平以及南化公司的邵學文、葉慶瑞、吳野等等。其中尤以王德安、朱光第、蔡之湘、葉慶瑞、吳野等人創作最豐,風頭最勁,影響最大。
時間過去了幾十年,當年詩壇的這道風景已成美好的記憶。
二
任何時代的詩歌,總是帶著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痕跡。若論詩歌的風格,那個時期的詩歌和現在差異很大。詩歌創作大都是配合政治,為主旋律服務,當時報刊上發表的詩也都必須服從黨的需要。這批工人詩人身在生產建設的第一線,創作熱情極高,他們一方面踏著時代脈搏,寫了大量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另一方面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工人,又生活在工人群眾中間,對火熱的生活非常熟悉,選擇一些具體的景象、事象和物象進行記錄和描繪,歌其事、頌其人,寫出了大量的反映工業建設發奮圖強、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和工人生活的詩歌。這些產生于勞動原生態的詩歌總的基調是昂揚向上、直白明朗,豐富了中國的詩歌寶庫。在一個時期,尤其在“文革”前的1964年前后,工人詩人詩歌已經成為詩壇的一支主干力量,在當代詩歌史上留下矚目的一頁。
從下面幾位佼佼者中,可窺見一斑。
王德安,1941年出生于廣西桂林,筆名王耽、宋風、青花居等。
1959年開始發表作品,由民歌風起步。我讀他的第一首詩是1960年發在《新華日報》上的,其后王德安的詩作才漸趨成熟,初顯山水。不再是簡單、直白的歌贊勞動,詩作更講究立意新穎、構思新奇,他的詩不隨人云,不入俗套。這從他以后的《百貨譜》《師傅去傳經》《家書》《無聲的責備》等一系列詩歌中,能夠看出作者的匠心。1963年,組詩《工廠光圈》在詩壇頂級刊物《詩刊》發表,其中《送廠長》一詩,歌頌了一位“青布鞋襪、兩袖清風”的老干部“額頭上一道皺紋,歷史上一次風暴”,“時代把他煉成不銹鋼,酸里堿里爛不了!”工人的語言、工人的情懷,這首詩很快選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朗誦詩選》,讓20出頭的王德安名聲大振。1964年9 月《詩刊》發表了他的組詩《父子交接班》,繼而1964年11、12期《詩刊》合刊上,才華橫溢的詩人又推出了他的一首《嚴師》:
……師傅沒說話。/打開紫皮日記本—— / 第一頁寫著我爸爸;/ 上面還有咱廠長,/ 新提拔的技師“土專家”…… / 全是師傅的好徒弟啊。/ 為耕開這“一窮二白”的地,/ 師傅鍛出了多少鋒利的犁鏵!/ 三十年心血育英才,/ 芬芳桃李滿天下……
我呢,排在最底下,/ 格外的精心格外的嚴,/只為我,生在窮人家,/ 父親在雨花臺被槍殺……
幾十年后,讀這樣的詩句,依然很感動。濃郁的時代氣息和那個年月的氛圍,躍然紙上。
大約1974年,王德安和郭浩在南京市工人文化宮舉辦首屆詩歌創作培訓班(那時的培訓班是不收任何費用的),請來的都是當時活躍詩壇的頗有名氣的詩人或大學教授。連續辦了幾期,成果斐然,出了楊毅、李朝潤等幾位詩人,我也是從這個培訓班走上文壇的。
改革開放后,王德安的創作又一次出現“井噴”,這時他不只停留于寫詩,還寫散文隨筆。伯樂識馬,工作也調往江蘇《莫愁》雜志,任主任編輯。王德安勤耕不輟,出版了詩集《遲熟的高粱?霜葉集》《心底珊瑚》,筆記文集《迷你世界》,散文集《昔日吻痕》等。散文詩《黃山哲理》獲“江南春”詩歌大賽一等獎,《莊嚴的憑吊》獲“牡丹杯”全國詩歌大賽頭等獎,《忠厚的竊賊》獲江蘇省首屆法制文學一等獎,另獲第一、二屆金陵文學獎。
退休后的王德安,又愛上了瓷片收藏,風里、雨里、泥里、水里,細心搜集,如醉如癡,就像當年寫詩一樣;揀到一塊畫意好又完整的瓷片,他會高興好多天,就像當年詩作發表時的心情。荏苒多年,撰寫編著多本有關青花瓷的專著,尤其是他的《青花寫意》散文集,因了他詩人的天賦、氣質,加上一幅幅珍貴的瓷圖,讓這本書詩意盎然,別具風韻。他還擔任江蘇古陶瓷研究會副會長,《收藏快報》專家委員會委員,生活于他越發精彩。
朱光第,1933年生,筆名未小竹。
在南京工人詩人群中,朱光第是年齡頗大的一個,我和他在一個企業工作,剛一進廠就慕名去拜訪他,對其更加的熟悉與了解。
朱光第寫詩出道較早。在全民寫詩的1958年,他還精選了所在企業工人創作的詩歌,由南京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1月出版了一本名為《紅旗歌》的工人詩選,當時的市總工會主席夏冰流還寫了序。多年以后,我從廠史中了解到,我的工廠在那個火紅的年代名聞遐爾,一邊出產品,一邊出詩歌。用現在的話說,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個建設都走在全市前列。直到現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還列于我的書架上。雖說里面的詩,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已是生疏,但卻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記憶。
朱光第有首《熱處理工》的詩,至今還能背出來:
……對待工作,/火一樣的熱情;/對待革命,/鋼一樣的堅強!/時刻置身在火熱的熔爐邊,/心永遠是熱的;/整天冶煉的是鋼鐵,/意志也像鋼鐵般堅強!
寓事寄情,借物言志,豪壯的抒情,磅礡的氣概,開闊的胸襟,都閃爍在字里行間。
我們常在廠區碰面,聊的也多是創作,我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師長,很尊敬他。1976年10月1日,朱光第病逝,年僅43歲。本該年富力強,處于生命力最旺盛的他,過早的走完了他的人生。
1978年,市文聯恢復,在一次會議上,我碰到已在報社當編輯的葉慶瑞、蔡之湘,閑談間他們問起我朱光第的情況。聞之,都為之搖頭惋惜,喟然長嘆。
1979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為紀念新中國成立30周年編輯出版了一套叢書,在《江蘇詩選:1949—1979》中,選收朱光第的《女配電工》一詩,那是從他1958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個人詩集《第一件產品》中選出的。
為紀念這位師長,我曾寫了篇《斯人已故音容在》的散文,發在《江蘇作家》上。朱光第如若活著,在這文藝的春天,是會寫出更多的好詩佳篇,謳歌我們這個時代。我常想起他說的:詩要和著時代的脈搏,要表達人民的心聲;詩可以輕歌曼舞,但更要振聾發聵。
葉慶瑞,1942年生,江蘇南京人。
年輕時的葉慶瑞是個帥哥,高挑的個子,白皙的皮膚。1960年開始在報刊發表詩作。當年他在合成氨車間當操作工時,寫了首《加煤工的心愿》:
……望爐膛,/爐膛等著咱的煤;/望公社,/公社等著出爐的肥。/蹬蹬腳步一路響,/踏得地搖天欲墜;/甩一把汗水呀,/也砸得鋼板火星撲撲飛!
滿車的激情,/滿車的汗水,/“嘩——”一聲,/傾進了爐內,/化成千萬噸化肥。/火光里,/那晶亮的汗珠兒,/在把公社的豐收追……
還是那個時代的詩風,那個時代的氣魄,那個時代對勞動的謳歌,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1977年《南京日報》復刊,葉慶瑞調報社副刊部,當時報社在市委的一個地下室辦公,進進出出,十分擁擠。我曾去那兒拜訪過。過了幾年,才遷往新街口的中山路1號。
葉慶瑞在報社文藝處處長任上,一邊精心編稿,扶植培養文學新人;一邊默默地耕耘,寫詩、寫散文、寫隨筆。那些年,他出版了詩集《愛的和弦》《她,就是繆斯》《愛的化石》《多夢季節》《都市冷風景》,散文詩集《相扶的綠葉?無名花》《A弦的詠嘆》,散文集《山水二重奏》等等。
退休后的葉慶瑞徜徉于光影世界,影像世界的獨特魅力深深吸引了他,讓他如饑似渴,如醉如癡,拿起相機的他不斷調整光圈,出新構圖,在湖光山色中捕捉生活中的美景。一路走來,苦中取樂,樂在苦中,那一幀幀作品,是他對美好生活的呼喚。他的攝影夢也像他的詩歌創作,一幅比一幅精彩。這不,不久前一本《葉慶瑞詩畫攝影集》又捧讀于讀者的手中。
蔡之湘,1940年出生于湖南,筆名謝石。
蔡之湘從17歲發表第一首詩歌《牡丹沒有它美》以來,一直筆耕不輟。他的詩生活氣息濃、情感深,在林林總總的詩作中,人們必然會提到他的一首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曾被多家選本選用。這就是發表在省作協主辦的文學雜志《雨花》1964年6月號上的《我的牛頭刨》:
我的牛頭刨,/ 模樣兒像牛,/ 性格也像牛,/晝夜不停地奔走,/ 只要喝幾滴機油。
我的牛頭刨,/ 全身筋骨鋼鐵鑄就!/ 萬斤重量壓在身,/ 腰不彎,氣不喘,/ 像有說不盡的歡樂,/ 唱著歌兒朝前走。
沒有那樣的生活,沒有那樣的真情實感,寫不出這樣的詩。
《南京日報》復刊時,葉慶瑞和蔡之湘先后調入報社副刊部,當記者,當編輯,一面“為人作嫁衣”,一面孜孜不倦地劬力筆耕。“好雨逢時節”,創作上再次發力,作品形式輻射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各領域。
退休后的蔡之湘,在金陵老年大學當校報主編,繼續發揮余熱,一干就是16年。2011年,蔡之湘開始著手整理編纂自己的選集,內容包含散文、詩歌、小說、人物專訪、書評、影視評論和文藝隨筆等多種文體,分為人生漫步、詩歌短笛、小說驛站、人物春秋、生活隨筆和書林拾穗六個部分。書中收有作者對方之、包忠文、江曾培、蘇童、葉兆言、黃蓓佳等著名作家的獨家專訪,并有對曾國藩、巴金、錢鐘書、曹聚仁、陸文夫、賈平凹、范小青等名人逸事的介紹和作品的獨特評析。
“這本文集是一個普通生命在不同年代、不同心境中綻放出來的幾束文學小花,它們有自己的芳菲、風骨和雋永。”蔡之湘在《后記》中這樣寫道。著名作家包忠文評價蔡之湘的作品稱:“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而其基本點則是:凈化人性,使人變得更美。”
吳野,1941年出生,安徽涇縣人。
在這一批工人詩人中,吳野的機遇最好,雖說寫詩起步較遲,然而24歲的他,卻在詩壇小荷初露的時候,有幸參加1965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赴京前夕,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明朝上北京》,放聲歌唱:
夢中笑醒好幾回:/ 想不到,能去北京開大會!/ 蹬開被子把衣披,/ 車間去,再掄它幾大錘!
十二磅大錘輕如棉,/ 一連幾十下不嫌累。/ 窗外月光明如水,/ 師傅把車間門兒推。
多少心里話,含在嘴,/ 老師傅喜的直落淚:/ “小伙子,我知道你睡不著,/ 錘吧,錘吧,你使勁兒錘!
掏出一塊白手帕,/ 師傅給徒弟擦汗水:/ “別太累,快去睡!/ 明早起,紅旗下面去站隊……”
這就是當年還在南京化工研究院實驗車間當工人的吳野發自心扉的詩行。
好風更添力。這以后的幾十年,吳野一直活躍在中國詩壇,以詩歌創作為主。1996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抒情長詩《孫中山》,接著2011年4月,南京出版社出版長詩《南京頌》,用詩為南京寫傳,完成他心中歌頌南京的宿愿。他的詩格外厚重,格外深沉,格外顯出氣魄。
吳野在南化第二中學任教不久,又先后任《江蘇工人報》編輯,《新華日報》城市組副組長,南京藝術學院音樂系創作員,《青春》雜志社副主編,副編審。南京市政協常委。199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退休后的吳野,常往返于大洋彼岸,那里有他的親情。
三
回眸南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工人詩人群的崛起,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當時的環境使然。
當年的南京工人文化宮是培養工人作者的大學校,是工人作者學習創作和接受輔導的重要場所。當時,市工人文化宮固定的一排長長的透明櫥窗里,還不定期的出版“工人詩歌之窗”,展示全市工人詩作者近期的新作,圖文并茂,從不同視角表現了對勞動的贊美、對勞動者的崇敬、對勞動生活的熱愛。同時標出作者單位。我常駐足于櫥窗前品讀。
許多工人詩人的成長,也非一帆風順,有過創作中面臨的困惑與挑戰,尤其在詩歌立意、用語、技巧上的提高都曾實踐了王國維之“三境界”說,都經歷過既有“無言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的迷惘,也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勤奮,還有“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喜悅。對文學創作起于興趣,終于毅力的這批工人詩人,隨著他們人生閱歷的豐富,在實踐中,有了開闊的思想視野、有了圓熟的文字技巧,其中的佼佼者,后來都加入省作協、中國作協,并陸續從事專職的報紙副刊、文學雜志的編輯工作。
回憶當年的寫詩,很多詩人的文學夢,最初都是從正洪街(今洪武路)市工人文化宮起飛,這里匯聚著眾多詩人、作家的青春記憶,提起那段美好時光他們無不充滿留戀之情,還可以想象當年這里曾經有過的高談闊論和歡聲笑語。在青春的日子里,很多事隨風而去,逐漸消失在成長的喧囂之中,唯獨工人文化宮卻一直留存在他們的心底里。無怪,王德安、郭浩們要在1974年,他們當年成長的地方,舉辦全市詩歌培訓班,讓新一代詩歌作者也體驗、享受這個搖籃的溫馨。
有一點需要提及,由于時代主體場景的變更,價值多元時代詩人們對詩歌功能的不同認識,詩人社會角色的個人化,以及由此導致的襟懷格局等因素,這批工人詩人的詩篇,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絕響。
當年的這批工人詩人,健在的都已七十開外,步入人生的秋季。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個境界既是行無羈絆的自由,更是心無一物的忘我。他們或迷于瓷片,或鐘情攝影,或仍操舊業……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樂,“山景總須橫側看,晚晴也是艷陽天”。
在這個繁華與喧囂并至,多元與困惑共存的時代,文學依然在這批詩人群中是一項至高無上的事業。他們執著地堅守著,不斷發力,在執拗的堅守中閃爍光芒,在喧囂與浮躁中堅守一個作家的責任與擔當。他們中的不少人也與時俱進,實現了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他們一如既往地關注現實,但思想更加深刻,構思和語言也變得現代。他們對詩歌的前景依然看好,認為新詩持續發展下去,總會被讀者認可,詩歌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國粹。不會因一時低俗、庸俗、媚俗的作品泛濫而障目、悲哀。相信在實現“中國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會有詩歌創作的新高潮迭起,為這個時代謳歌頌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