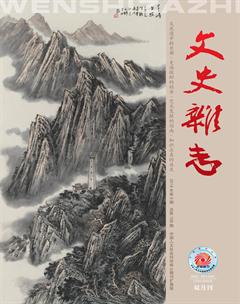明代西南上層社會的生活狀態
胡開全
摘 要:幸存的五部“明蜀王文集”,是研究以蜀府為中心的明代西南上層社會面貌的珍貴文獻資料,那里面展現了歷代蜀王自覺的責任擔當,高貴的生活情趣,積極的地方建設,嚴格的家人約束以及中國文化傳統中高貴、擔當、自由且內斂的貴族精神。蜀府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對成都和西南地方社會和民眾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尤其是蜀府刊刻書籍、提倡文教、培建公祠,參與音樂欣賞和創作等,代表了明代西南地區上層社會對地方文化和風氣的引領,在塑造成都城市精神的同時,也成為中華文化閃亮的一部分。
關鍵詞:明代蜀府;王府生活;貴族精神;文化引領
四川地處中國西南,扼守長江上游,是中華大一統帝國存續的基石。明蜀藩一系,是明代高貴人文情懷的代表。明蜀府是朱元璋分封的24個藩府中,一直延續到明末的11個藩府之一。蜀府是唯一長期獨占一省,并始終享有“忠孝賢良”“宗藩首善”等美名的明代宗藩。由于明末戰亂導致成都的文獻被毀,這個中國歷史上非常難得的貴族群體正面形象一直沒能真正樹立起來。關于研究蜀藩的成果,目前比較詳盡的主要有陳世松研究員的《明代蜀藩宗室考》(《西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馬士訓的《明代蜀藩研究》(廣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宋立杰的《明代蜀王角色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等。這些研究從已知的《明實錄》、明代文獻、明代考古發現,以及《明史》介入,初步勾勒出蜀藩的一些基本面貌,但仍存在許多不足。如受《明史》影響,上述學人普遍將恭王任蜀王的時間壓縮成一年,實際第十二任蜀恭王在神宗、光宗、熹宗三帝的實錄里都有活動記載,[1]直至崇禎四年(1631年)朝廷遣行人龔廷獻往蜀府主行喪禮。[2]至于蜀王朱至澍任蜀王的時間,則要推遲到崇禎五年。而關于蜀藩十世十三王中出現三位“友”字輩和兩位“申”字輩,前述學者將其引申到蜀府內存在陰詭的權力爭奪方面,這也與《皇明祖訓》中關于繼承的原則不符。[3]還有簡單地將蜀藩描述成奢靡者、剝削者、寄生蟲等,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也有欠妥之處。
筆者借助五位蜀王的著作,即四部海外的孤本和國內僅存的一部,共五部“明蜀王文集”,結合明朝制度和《明實錄》中具體的時間點,配合散落民間的碑文資料,計劃作系列研究,[4]力圖用蜀府為例來重塑中國藩王的形象。落腳西南地區,上層社會的代表性群體有黔國公沐英在云南建立的西平侯府(俗稱沐王府)、播州的楊氏家族、環列的土司、長期在本地執政官宦、蜀府下屬的郡王如德陽王府和汶川王府等,然后就是以新都楊家“一門七進士”為代表的世家。在這個層次的人群中,蜀府層級最高,在彼此間往來中,其他都要以朝覲的姿態前來。在整個明朝時期,蜀府的美譽度是西南上層社會的佼佼者,主要體現在其自覺的責任擔當、高貴的生活情趣、積極的地方建設、嚴格的家人約束等方面。
一、蜀藩主動的擔當和執政的策略
對于藩王這類貴族,人們印象中大多是循規蹈矩、衣著光鮮、白白胖胖、沒有能力或實權的人。西方人也把明藩王們納入貴族世界觀的體系之中,而且印象都是一個模式。有一位葡萄牙人伯來拉(Galeote Pereira,活躍于約1545—1565年間)在廣西桂林見過靖江王并受到了相當的禮遇。據他描述,這些皇親國戚在城中的社會地位非常顯赫:“他們盡情吃喝,多半養得肥肥胖胖,隨便看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哪怕我們以前從未見過,我們也看得出他是皇親。他們彬彬有禮,養尊處優,我們在該城的時候,發現從他們手里接受的尊敬和款待,超過別處”[5]。其實,在這種表象的背后,真正賢能的藩王通常受封即立志有所作為,并經過一系列的歷練,包括嚴格的皇室教育和出外游歷增長見識。蜀藩在這方面的行為及其留下的資料,為全國樹立了典范。
第一任蜀王朱椿(1371—1423)在受封后、就藩前的歷練期間,于18歲時寫下一首《中都留別》[6]很能代表其志向,其中“昔聞河間獻,亦有東平蒼。唐宋稱宗室,上下相頡頏。顧我才谫薄,志存先哲王”諸句,以歷史上著名的河間、東平兩位賢能藩王為榜樣。對此,旁觀者能深切感受到朱椿“忠孝為藩奉君父”[7]的決心。朱椿就藩后,還多次撰文警示自己和教育后人要時時牢記以河間、東平為表率。后世蜀王也很好地繼承了這點,時時在詩作中重復這一志向,如第七任蜀王朱申鑿(1459—1493)詩作《為善堂》[8]中有“東平為善非常樂,善足應知降百祥”句。蜀府的這種姿態以及實際行動被朝廷上下反復贊揚,如第一代蜀王朱椿被明成祖朱棣贊為“惟賢弟抱明達之資,敦忠孝之義,處事循理,秉心有誠,稽古博文,好學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9];第八任蜀王朱賓瀚(1480—1508)被明孝宗朱祐樘贊為“河間禮樂文風盛,江夏忠勤世業昌。異代豈能專美事,吾宗亦自有賢王”[10];第九任蜀王朱讓栩(1500—1548)被楊升庵(1448—1559)贊為“視河間可雁行,而于江夏有過無不及者”[11],也被后來的蜀府長史贊為“仰惟我成園……感興操觚泉,達東平之頌”[12]等。這說明在朝廷上下看來,蜀府立場堅定,對皇帝、對朝廷是忠心的。尤其是朱椿,在明朝初年經歷了自己岳父藍玉謀反案,朱棣“靖難”之役,之后又是“谷王反復”,在眾多兄弟被削藩的情況下始終屹立不倒,當是其絕對的忠心、嚴格的自律使然。而忠心與自律,不用說是蜀府在明代復雜皇權政治中之所以一直存在的最重要的保證。
除了忠心與自律外,有作為,為帝國大一統作出實際貢獻,也很重要。四川在明代的版圖上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明代王世貞在《弇山堂別集》中的《名藩擇形勝》里有:“明封秦晉諸王,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旗服飾,僅下天子一等。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續文獻通考》曰:高巍上言,太祖既定中國,體三代之良法,擇形勝之重地,建封諸子……四川雖西南一隅,山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明代彭韶在《山川形勝述》有更具體的描述:“蜀之地,南撫蠻獠,西抗吐蕃,上絡東井,岷嶓鎮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為前門,靈關為后戶,峨眉為城郭,南中為苑囿。緣以劍閣,阻以石門,而越負秦,地大且要,誠天府之國也。”[13]另一點對蜀府的生存也很重要,就是四川距離京城遙遠,特別是朱棣遷都北京后,是所有藩府里離京城最遠的,消息往來的時限最長。事關藩王去世的大事,消息傳到京城大約需要約70天,往返就是5個月。如《孝宗實錄》有兩則關于蜀王朱申鑿薨的內容,就是一例。《明孝宗敬皇帝實錄》卷之七十八說:“蜀王申鑿薨,王定王第三子,母次妃王氏。天順三年生,成化七年封通江王,八年進封蜀王。至是薨,年三十五。訃聞,輟朝三日,賜祭葬如制,謚曰惠。”[14]其時間標為弘治六年七月癸巳,即1493年8月12日。《明孝宗敬皇帝實錄》卷之八十,又出現內容完全相同的一條,但時間卻變成了弘治六年九月甲辰,即1493年10月22日。這應該理解為第一條是朱申鑿死亡的時間,由后世編修實錄時添加上的,而后一條則為孝宗皇帝聽到消息并作出處理方案的日子。而普通人員和消息往返需要11個月。明朝禮部規定“欽依限期,山東德府等府,山西晉府等府,俱限六個月,代府限六個月半,河南周府等府俱限六個月半,陜西秦府等府俱限七個月,肅府慶府限八個月,江西益府等府俱限八個月,湖廣楚府等府俱限八個月,廣西靖江王府限十個月,四川蜀府限十一月”[15]。

有鑒于此,蜀府必然主動承擔眾多的責任,并相機擇處,宣揚朝廷威儀,使西南民眾雖然距京城千里卻感受皇恩咫尺。如守土上,明朝初年蜀府還有兵權時,在宣宗時期,遇到松潘軍情,要求蜀府參與配合,由于軍情變化,有時不得不斷然決策。當時蜀王按照朝廷指令,委派指揮領兵4000出征松潘,并向朝廷匯報。但剛過一個多月,“蜀王友堉奏,前后調發官軍校尉七千余人助討松潘叛寇。”[16]即由前線戰報分析出兵力不夠的問題,又增調3000人。于是“上嘉其能,盡藩職,恭朝命,賜書獎勵之”[17]。蜀府并未以此為驕,反而于四年后,根據朝廷政策,“蜀王友堉奏成都三護衛,請以中右二護衛歸朝廷,留左護衛官軍供役。上嘉其能省約,從之”[18],即主動交出大部分兵權,用實際行動向朝廷顯示忠心。不過,兵權的交出也是蜀府在明末時雖然富有卻無力回天的原因之一。
蜀府最大的貢獻是其獨特的“以文教化一方”[19]策略,帶來《明史》所載“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20]的局面,成為踐行明太祖“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理論的典范。朱椿在延攬名士,鼓勵文教方面成績卓著。他在對宗教的關注和對宗室成員的安置上,最能體現其執政策略。從四川明代佛教碑文[21]可以看出,蜀府除重視傳統的峨眉山、成都、大足寺廟外,重點關注的南面馬湖地區、西南面雅安、天全一帶、西面茂州至松潘一帶的寺廟,為穩固邊疆貢獻良多。從軍事角度看,四川作為當時的邊疆地區,主要受到西北、西、南三個方向的威脅;而南面有四川行都司帶領六個衛所,防守相對穩固。蜀府多次用兵,因之主要在松茂一帶。[22]它仿效“天子守國門”的策略,將宗室主要布置在都江堰一帶。[23]從實踐看,這一策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五任蜀王朱友垓(1420—1463)受到皇帝降旨表彰,特寫下《迎詔》詩,里面對實現民族團結有這樣的描述:“日星璀璨華夷見,雨露沾濡草木妍。萬古岷峨為保障,親藩共享太平年。”[24]
蜀府在經濟上也力所能及地為蜀中作了一些貢獻。首先是利用職權幫助蜀中百姓爭取免稅的機會,如只進貢蜀錦和川扇。對朝廷要求的專項“茶馬交易”,蜀府一方面積極督促地方,一方面府內設立辦茶的專門機構“蜀府正字”[25];每年向朝廷進馬也成為常例,為國家貢獻很大。小項非常多,包括資助修建寺廟、名人祠堂,都江堰歲修,給博士生撥款,給名士賜田等。明代在蜀中形成一個傳統,凡是涉及修公祠、修廟,修橋等公益事業,牽頭人都會想到向蜀府求助。從留下的文獻和碑文看,蜀府或捐錢捐物,或賜田等,參與很多,讓蜀中民眾真切感受皇恩咫尺。下面簡單舉幾個例子。
明初文人方孝孺就很贊賞朱椿的善舉,他曾寫道:“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圣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推先生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遠于遐邇”[26]。朱椿有時還主動施恩,“嘗視成都郡學,分祿米以給教授,俸月一石,遂為令”[27]。他對成都平原重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更是長期關注,投入頗多。明人陳鑒《鐵牛記》記載,在都江堰建鐵牛時,“蜀王聞而賢之,命所司助鐵萬斤,銀百兩”[28]。正德年間的一次都江堰整治工程,“治之日,蜀府差長史李鈞赍幣帛羊酒,勞諸從事者。民環而觀之者,億萬歡聲,震山谷間。其父老皆合掌曰:此吾子孫百世利也……蜀府每年亦助青竹數萬竿,委官督織竹籠,裝石資筑”[29]。
二、王府高貴的生活方式
對于王宮內苑,由于可深入觀察的機會不多,自古有很多揣測,西方人同樣如此。葡萄牙人博克舍寫道:“他的宮室有墻圍繞,墻不高而呈四方形,四周不比果阿的墻差。外面涂成紅色,每面各有一門,每道門上有一座門樓,用木料精制。四道門的主門前,對著大街的,再大的老爺都不可騎馬或乘轎通過。這位貴人住的宮室建在這個方陣的中央,肯定值得一觀,盡管我們沒進去看。聽說門樓和屋頂上了綠釉,方陣內遍植野樹,如橡樹、栗樹、絲柏、梨樹、杉樹及這類我們缺少的其他樹木,因此形成所能看到的清綠和新鮮的樹林。其中有鹿、羚羊、公牛、母牛及別的獸類,供那位貴人游樂,因為如我所說,他從不外出”[30]。從五部“明蜀王文集”來看,蜀府的真實情況是高貴而有條理的。
作為蜀府的主人,在享受榮華富貴之余,仍然守土有責,勤政為本。王宮里有專門的“勤政堂”,第七任蜀王朱申鑿有詩云:“多士皆知學,三農盡力田。明年應考績,補內看喬遷。”詩歌表達了蜀王自己及臣屬的職責。而朱申鑿所寫《思政堂》則讓我們看到了蜀王執政的理念和工作狀態:
思政堂[32]
勤政孜孜有所思,東方向曙早朝時。
奸邪誤國當除卻,賢俊匡時可薦之。
海內只期興教化,民間須得樂雍熙。
唐虞稷契商伊尹,一念惟公豈有私。
蜀府如其他藩府一樣,被規定不干政,不干軍,不從事四業。其所執之政,并不太顯性地讓外人所知。但其儀式感十足的早朝制度還是堅持了下來;因為這是規定的皇家范式,同時還要接受地方官和鎮守太監的監督,是朝廷在制度設計上對藩府的制衡。早朝大致處理一些府內的人、財、物,以及固定禮儀、王莊經營等事;然后就是在初一、十五接受地方官來朝覲。早朝的情況在朱友垓和朱讓栩的詩作中都有描寫。
要實現“忠孝為藩”,除了嚴格的皇室教育和藩王自己及子弟認真讀書外,出外歷練也很重要。第一代蜀王朱椿在皇宮學習由宋濂親自編寫的教材,然后又被派到鳳陽,即在“中都閱武”多年,其間還發生了將西堂開辟出來,請李叔荊、蘇伯衡等著名學者來商榷文史的佳話。等到他在四川就藩后,繼續禮聘以方孝孺為代表的頂級文人前來服務,并帶世子等進京[33]和巡視全川。之后的蜀王也紛紛效仿,長期與蜀籍名人如首輔楊廷和、萬安,狀元楊升庵、才女黃峨等保持聯系,閱讀并模仿他們的作品;然后利用盡可能出現的機會出外歷練,以增加執政能力。朱友垓《定園睿制集》中對外出沿途的描述,在詩歌方面有《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陜州河亭陪韋大夫眺別》《巴南舟中》《宿關西客舍寄嚴許二山人》《江南旅情》《泊舟盱眙》《題江陵臨沙驛樓》等,對細節的描述有《漁村》《訪僧居》《茶人》等。朱申(1448—1471)《懷園睿制集》里亦有《京城》《旅館》《商旅》《田家》《卜者》《醫者》《樵人》諸詩,觀察越來越細,體察民情也越來越準。

朱申鑿的《惠園睿制集》里有《西蜀宦游》《宦途游覽》《題永城驛》《長安秋夕》《春日長安即事》《洛陽早春》《江南旅情》等詩。它們有時還將這種出外歷練描述得比較艱苦,其中比較典型者如:
赴京途中遇雪[34]
沖寒馬一鞭,萬里去朝天。
玉屑將埋路,瓊花正滿川。
群鵝浮遠水,孤鷹落平田。
杳杳村墟外,微茫有暮煙。
到宣宗時期,朝廷開始阻止藩王進京。蜀王不能隨意離開土地,世子等即便出門,也不能得到“面圣”的尊寵。再到后來,地方官進一步限制蜀府的行動自由,“舊例各王府親王郡王以下,凡欲出城祭墓送葬之類,俱先期奏請得旨乃行。蜀府自獻王以來,每遇親喪,親王郡王俱自行送葬,不經奏請。至是,四川守臣奏之,蜀王亦自以本府相承故事為解。命今后各王出城,仍照例先期以聞”[35]。這便導致后世蜀王行動不便,即葡萄牙人印象中的“從不外出”。后世蜀王難有更多的閱歷,除經營內苑外,對王莊也疏于巡視。這也直接導致第九任蜀王朱讓栩只能沉迷于宮苑之中,其《長春競辰稿》以描寫內苑景物而移情宮詞散曲為主。其散曲作品不見南曲香艷纏綿的影響,與蜀中人士楊廷和、楊慎、黃峨等有一致的清麗之風與雅趣思力,顯示出正德、嘉靖年間散曲創作南北分野之際的不同流脈,對當地音樂鑒賞和創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劉大謨、楊慎纂修的《四川總志》亦記載朱讓栩“嘗著有《適庵》諸集,多為縉紳博誦”[36]。
雖然行動不自由,但蜀府中人的吃穿用度仍然高人一等。荔枝是蜀府的特產,非常珍貴和稀少,經常作為進貢的禮物。下臣能得到賞賜,對其本人和家人都是很興奮的事。朱椿有“梁園丹荔初頒賜,奪得歸家遺細君”[37]之句。朱申有“顆顆含瓊液,枝枝綴火珠……奇果真堪愛,輕紅錦作膚”詩。[38]后者“貢珍來上國,勞使走長途”[39]之句,則顯示這些荔枝主要來自川南一帶,朱椿曾將其作為貢品送到南京。
另外吃新米和喝新茶也被他們記錄下來,如朱申的“秋熟喜登場,晨炊玉粒香。流匙何軟滑,樂歲試新嘗”[40],朱友垓的“天產靈芽秀,惟鐘谷雨姿。龍團和露采,雀舌候春期。山遠步尤健,林深路更危。幽齋自烹啜,清味有誰知。”[41]
成都的炎炎夏日,外面酷暑難耐,但住在王府里面卻是很愜意的——因為有涼庭、有冰鎮西瓜等解暑的水果、有涼爽的住所。朱申筆下的王府既在涼庭里“日午尋涼向水隅,脫巾露發總無拘。不須白晝揮紈扇,喜有清水出玉壺。攸而興來游竹徑,坦然倦后臥紗廚。浮瓜沉李隨時用,夢入華胥足自娛”[42],又可利用高大建筑在避暑時發揮巨大的作用,即“熱極似爐中,來乘殿閣風。清涼生細葛,如在水晶宮”[43]。
外界很難知道這些細節,文人們只能通過蜀府的刻書和撰文以及推廣文化和教育的實踐,來推想蜀王們的藏書和讀書情況。關于蜀藩刻書,“初蜀獻王好文學,招致天下名刻書傭集成都,……故蜀多巧匠”[44]。這顯然大大推動了四川刻書業的發展,故蜀藩刻書就走在了宗藩刻書的前列。據《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統計,刻書超過10種以上的藩府有:“弋陽府56種,蜀藩38種,楚藩26種,周藩23種,寧藩22種,趙藩20種,遼藩18種,慶藩13種,益藩12種,沈藩11種……”[45],蜀府在數量上也名列前茅。刻書的基礎是藏書,清人彭遵泗稱:“藏書之富,敝鄉之成都,莫比蜀府。成王喜讀書,宮中為石樓數十間,藏書數億萬卷,日抄寫者數百人”[46]。而且大多數蜀王也實實在在地愛讀書,“潛心孔學應無倦,適間虞琴肯放閑。須信尊賢忘勢利,行看禮樂繼河間。”[47]蜀王們從中找到了樂趣:“簡編用志須研究,墳典開心可卷舒。”[48]這些行為使蜀府在文人群體中樹立起情趣高貴的群體形象。
三、蜀府積極參與錦城社會生活
蜀王府建筑宏偉,設計之初就帶有“壯麗以示威儀”的意圖,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成都600多年的文化中心。這里雖然不是成都的行政中心,但蜀府以模范作為,使其成為西南地區代表朝廷的演禮中心。其一舉一動,在當地百姓看來都是睿旨綸音,深深地影響著成都乃至周邊民族地區。具體方式包括鼓勵名士風范,提攜名醫,修廟、修名人祠堂,創建市民公園,捐建義冢和橋梁,提倡以散曲為代表的音樂等,積極參與錦城的社會生活,并以自己的品味影響著成都。
成都自宋末以來,經濟萎靡、文化凋敝,明初開始恢復,這與歷代蜀王的關注與貢獻密切相關。我們從幾代蜀王所寫“成都十景”[49]就能看出。蜀王除從外省延攬名士外,對當地的文化人也大力提攜和表彰,熱情為社會樹立一些楷模。對他們中的一些人,蜀王命人寫詩來贊美,如“王福,成都人,讀書尚義。偽夏時,元御史丁幫翁流寓于蜀,福館之,事以父禮。既卒,厚殯葬之不吝。蜀王聞其事,更名曰義,命儒臣詩以美之。”[50]對另一些人,蜀王則直接賜予田產改善生活,如“楊敏,字學可,新都人,師杜圭,博經史,避兵云南,還蜀,明玉珍迫之,不仕。洪武賜鈔歸隱。蜀獻王給田八十畝,贈云:流水畫橋題柱客,清風精舍讀書人。”[51]
對醫術高明者,蜀王積極向朝廷推薦,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如“葉拱北,字朝貴,彭縣人,幼習儒業,有大志,因母病,究心醫理,遂精焉。天性孝友,博學能文,尤工詩,嘉靖乙酉(1525年),蜀成王深慕其名,卑禮聘之,試輒奇中,賜宅成都。疏薦于朝,應禮部試,居第一,授以良醫正。回蜀,曾制《存養省察論》陳于王,王嘉納焉。每歲制方藥施貧乏者,其門如市。”[52]
對于成都西門著名的杜甫草堂,歷代蜀王傾注心血最多。朱椿親自到現場調查,訪問當地人員。他有詩道:“卜居草堂近,梵剎有遺基……緬懷杜陵老,千載同襟期。”[53]修杜甫草堂時,方孝孺在蜀并撰文記載,即后人回憶的“蜀獻王之始封也,見祠隘且就圮,曰:‘是足以妥靈而處祀乎?遂拓而新之”[54]。之后多位蜀王又有維修,到張時徹巡撫四川時,又向時任蜀王朱讓栩稟報要搞大型的修繕工程。蜀府應允,“遂辟廊廡,起甍棟,引流為池,易甃以石,規模壯麗,增于故昔蓋十之六七,費白金三千有奇”[55]。杜甫草堂是成都著名景點,來參觀游玩的人眾多,因之對蜀府的評價甚高:“是舉也,見今王繩武之孝焉,尚賢之誠焉,風后之烈焉,非恭儉樂善,其孰能之?”[56]而蜀王本人對修繕工程也很滿意:“遙指西郊舊草堂,少陵遺跡未荒涼……游人仰止祠前水,一曲滄浪引興長。”[57]
之后,張時徹又請蜀王出力為諸葛亮建專祠,結果蜀府也同意了,“辟浣溪之隙地而祠焉”[58]。于是立碑,“蓋以昭蜀王尚德之美”[59]。
蜀王在成都東門新建的祠堂,即凈居寺的宋濂祠,經過幾代蜀王的經營,也成為成都的著名景點。王樵《使蜀記》有記載,楊升庵受邀編撰《全蜀藝文志》,就是在凈居寺花了28天完成的。對于這個祠堂,王士楨是這樣記載的:“過橋至凈居寺,氣象疏豁。入山門為明王殿,次彌勒佛,次大雄殿,皆有畫壁。最后藏經閣。西出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憲公(濂)像。殿后文憲墓,高如連阜,其上修竹萬竿,扶疏櫛比,無一枝橫斜附麗。”[60]
蜀府還修了一些惠及面廣的工程,如位于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園。成都老人口碑相傳:“王宮之東另建園囿,內有古梨樹數十棵,均二三百年古木,每年三月成都士女游玩其間”[61]。城外面的小工程很多,如新都由蜀府郡王修的德陽王橋,“舊名大小毗橋,水勢極險,往來病涉,王命官督建,巡撫李公大書其碑曰德陽王橋。”[62]又如供窮人使用的墳地,即“義冢地,府城四郊,蜀府置”[63]。
蜀府喜歡與民同樂,但不聲張、不擾民,如詩:
元宵[64]
銀漢月華明,游人隊隊行。
笙歌歸禁苑,燈火下蓬瀛。
笑語喧花市,星球璨錦城。
良宵堪玩賞,歸去馬蹄輕。
這種“歸去馬蹄輕”般悄無聲息地參與,導致蜀府的存在感不強。然此處無聲勝有聲。蜀府在公眾場合的低調,彰顯出自由、平和而內斂的貴族氣質,在潛移默化中自然提升了成都的城市品位,當是“忠孝為藩”的體現。
四、蜀府對家人進行嚴格管束
蜀府的蜀王不僅自己以身作責,主動作為,同時還嚴格約束家人,包括各郡王及其子孫、姻親,以及屬臣。蜀王的處置有時是非常嚴格的,如一些郡王犯錯,就被剝奪繼承資格,甚至遷出四川。[65]這些人后來糟糕的境遇對其他宗室的警示教育作用巨大。另外,偶爾發生的臣屬在地方欺凌跋扈之事,因為不存在尖銳的利益沖突或不可調節的矛盾,蜀府也都妥善處理,既平了民憤,又維持了蜀府的尊嚴。嘉靖年間剛入職行人的王樵稱“蜀藩賢于富,宗人少犯法,親王尤厚禮士大夫”[66],就代表了京城對蜀藩的整體印象和評價。能達到這種效果,緣于蜀府以理學為宗,教育到位。這方面第一任蜀王朱椿作出了典范,他甚至在生病時仍然在回憶從宋濂處所受的教誨:“卻憶潛溪老,清宵魂夢馳。”[67]這使得蜀府在成都公眾面前呈現出一個比較賢良的形象。蜀府內,郡王、“將軍”的先進事跡自然也很多。其中一位奉國將軍的事跡尤為顯著。
《天啟成都府志》載:“朱讓棟,號幾山,汶川奉國將軍。生而慈和正靜,能篤愛父母,順承三兄,常捐貲濟內外婚喪,以居產讓貧族。方伯余公建橋塔,助米百石。中年喪淑人唐氏,遂不娶。居常延名師教二子諸孫,家庭禮讓,宛然儒風。其冢子中尉承燸,博雅敦倫,綽堪宗范,先棟卒,人多惜之。棟年八十,蜀端王暨本郡王褒禮稠渥交,旌其閭焉。棟善事不一,此撮其槩。”[68]這則記錄中的奉國將軍,屬于汶川郡王府,系蜀府第五等爵位,按規定“歲支祿米六百石,俱米鈔中半兼支”[69],卻能動不動就助米百石,而且還“善事不一”,確實令人敬佩。
而蜀王每年出城謁陵,更是蜀府“孝道”文化的集中展示。各個蜀王對于謁陵還有自己特殊的感想,有些被記錄了下來,如朱友垓《謁和園》[70]中有“寢園樹木籠蔥茂,朝殿丹青煥爛鮮。恩德不忘懷厚土,劬勞難報感蒼天”句,表達要不忘恩德,勤勞執政。朱申鑿《余謁東景山》的“兄王厚土千年固,內翰雄才百世豪”[71],則有感謝兄長之意。朱讓栩《東郊謁奠先考寢園有感而作》云:“朝罷匆匆應轉首,彷徨東顧不勝哀”[72],表達出拳拳孝意。
蒯氏是與蜀府關系密切的顯貴家庭,第一代蒯克隨獻王來蜀,第二代蒯縉任西城兵馬指揮司指揮,其女為定王妃;后世襲職武德將軍(正五品)、武略將軍(從六品)等職。蜀府遂與蒯氏成為姻親。某年,當后者完成國家任務,受到朝廷表彰時,蜀王特作《題蒯氏八詠》組詩,對其既褒獎又告誡,總體不離忠誠、行義、周貧、撫孤、修橋、耕讀等。蜀王乃借機重申蜀府對外提倡的生活方式,茲錄其中一首,以饗讀者:
攄忠報國[73]
平生義氣許誰同,志在操修竭寸忠。
勉力拳拳期報答,小心翼翼貴謙恭。
數竿勁竹凌霜翠,一點方葵向日紅。
為國勤勞無懈怠,致身常近五云東。
這雖然是蜀府為蒯氏所寫,但可以想象,由于各種傳播途徑,對其他姻親和本地士紳會有引領作用。
結 語
蜀府一系雖然以忠貞報國,以仁義名世,但在明末亂世卻畢竟不能夠挽救明朝的危亡,合族也被張獻忠屠殺,王府和陵園被破壞殆盡。其時,末代蜀王至澍投井,大致效仿崇禎帝之死。至于宗室成員在都江堰附近被殺,則跟明初的“天子守國門,死社稷”的政策有關。之后如張象華《哀蜀藩》所寫“天社星隳古社壇,杜鵑聲盡石苔瘢。井花清冷無人汲,留得丹心萬古寒”,對蜀府消失扼腕嘆息的文人不在少數。在明代的社會環境下,延續200多年的蜀府一系,能夠展現自覺的責任擔當、高貴的生活情趣、積極的地方建設、嚴格的家人約束等貴族精神,代表了那時貴族階層的很多優良品質,雖地處西南一隅,卻為全國作出了表率。蜀府這種有實績、有文獻、有文集、有陵墓、有民間口碑支撐的賢王群體,隨著今后的系列研究成果(如《蜀府文教化一方》《楊升庵與明蜀王》《獻王家范詳論》等)的陸續推出,藩王的形象將被重塑,而中國傳統貴族精神將會重現光芒。這也是逐漸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民從傳統中擷取的一份文化自信。
注釋:
[1]見《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四十九、卷五百六十六,《明光宗實錄》卷七,《明熹宗實錄》卷六、卷十八、卷三十、卷三十七、卷七十九等。
[2]《崇禎長編》卷五十二,崇禎四年十一月戊子,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第3032頁。
[3]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按照明朝制定的宗法系統,即:第一順位:父死子繼,有立嫡立嫡,無嫡立長;第二順位:無后,兄終弟及,嫡弟優先,庶出其次;第三順位:叔伯侄,先嫡后庶。有些郡王的繼承資格是事先被蜀王剝奪的,后面的研究計劃《獻王家范詳論》將作解釋。
[4]筆者自費從日本公文書館找到《獻園睿制集》《定園睿制集》《懷園睿制集》《惠園睿制集》,并取得掃描件,配合國內的《長春競辰稿》,目前已經完成基礎性研究三篇:《明蜀王文集考——兼論從日本新發現的四部與國內僅存的一部》(《文史雜志》2017年第3期);《少城一曲浣花溪——明蜀王文集中明代成都的初步印象》(《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壯麗以示威儀——明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內涵》(先被《天府文化研究院》第一卷收錄,再發表在《文史雜志》2018年第2期)
[5][30]博克舍(CharlesBoxer),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vira,Fr.Gaspar da Cruz,0.P.[and]Fr.Martin de Rada,O.E.S.A(1550—1575)London (1953),pp.40—41.41—42.轉引自(英)柯律格著、黃曉鵑譯《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頁,第27頁。
[6](明)朱椿:《獻園睿制集》卷十三,成化二年刻本,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書號“漢16870”。
[7](明)釋宗泐:《全室外集》卷四《蜀王江漢朝宗圖》,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版,第30頁。《明實錄》上另有“書‘忠孝惟藩以自警”的記載。
[8][31][32][34][48][71][73](明)朱申鑿:《惠園睿制集》卷六、卷二、卷七《勤政堂》、卷十二《思政堂》、卷四《涌泉書舍》、卷七、卷六,弘治十四年刻本,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書號“漢16874”。
[9]《明太宗實錄》卷四十二,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第680頁。
[10][11](明)楊慎:《長春競辰稿》序,載《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五輯第18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頁。
[12](明)游淄:《長春競辰稿》后序,第625頁。
[13][27][36](明)劉大漠、楊慎等纂修(嘉靖)《四川總志》卷四十八、卷一、卷一,書目文獻出版社,第698頁,第20頁,第20頁。
[14][35]《明孝宗實錄》卷七十八、八十,卷一百三十,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第1497、1524頁,第2298頁。
[15](明)《禮部志稿》卷七十三,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2頁。
[16][17][18]《明宣宗實錄》卷三十、卷三十、卷八十,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第790頁,第790頁,第1858頁。
[19]蜀府“文教化一方”的內涵和具體措施非常豐富,筆者規劃有專文論述。
[20]《二十五史》卷十二《明史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版,第705頁。
[21]見龍顯昭主編《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書社2004年版。
[22](明)朱申鑿:《惠園睿制集》卷六《西岷保障》有“將軍掛印鎮西岷,攻擊羌酋靖虜塵”句。
[23]云間顧山貞撰《客滇述》有“蜀府宗支多在灌縣,乃發兵圍之,不論宗室細民皆殺之”,載葉夢珠輯《續編綏寇紀略》卷一,第5頁。《鹿樵紀聞》卷中有“知蜀府宗支多在灌縣,圍而屠之;蜀世子亦被害”。
[24][41][47][64][70](明)朱友垓:《定園睿制集》卷四、卷三《茶人》、卷四《書齋閑詠》、卷二、卷四,成化五年刻本,藏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書號“漢16869”。
[25]目前在崇州、大邑、資州都發現有關“蜀府正字”的碑文,具體是承奉正辦貢茶等,詳細內容后面有專文論述。
[26](明)方孝孺:《成都杜先生草堂碑》,《遜志齋集》卷二十二,寧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716頁。
[28](明)虞懷忠、郭棐等纂修(萬歷)《四川總志》卷二十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200—23,齊魯書社。
[29](清)黃廷桂監修《四川通志》卷十三上《水利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5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33]據《明實錄》,朱椿是進京朝覲次數最多的蜀王。
[37](明)朱椿:《獻園睿制集》卷十五《賜和典寶新荔枝并詩二首》。
[38][39][40][42][43](明)朱申:《懷園睿制集》卷二《荔枝》,卷二《荔枝》,卷七《稻》,卷三《涼亭避暑》,卷七《避暑》。
[44](清)羅廷權等修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十六,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第33頁。
[45]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1版,第273頁。
[46](清)彭遵灑:《蜀故》卷十八《蜀府藏書》,清乾隆刻補修本,第52頁。
[49]詳見拙著《少城一曲浣花溪——明蜀王文集中明代成都的初步印象》(《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50][51][52][62][63][68](明)趙世雍撰《天啟成都府志》,卷二十四《孝義列傳》、卷二十五《隱逸列傳》、卷二十四《孝義列傳》、卷三、卷三、卷二十四《孝義列傳》,成都時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頁,第339頁,第331頁,第66頁,第57頁,第328頁。
[53](明)朱椿:《獻園睿制集》卷十三《賜草堂謙巽中長老》。
[54][55][56](明)張時徹:《重修杜工部祠堂記》,杜應芳:《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十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678冊,影印明萬歷刻本,第290頁。
[57](明)朱讓栩:《長春競辰稿》卷八《成都十景》之《草堂晚眺》。
[58][59](明)張時徹:《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杜應芳:《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十九,第290頁。
[60](清)王士楨:《秦蜀驛程記》,轉引自吳世先主編《成都城區街名通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頁。
[61](清)吳偉業撰,李學穎點校《綏寇紀略》“獻忠屠蜀”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5]蜀府第一代郡王華陽王就被遷出四川,這一支后來有很多不良記錄,但與蜀府已經關系不大,后面的研究計劃《獻王家范詳論》將作詳細解釋。
[66](明)王樵:《使蜀記》,《方麓集》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285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67](明)朱椿:《獻園睿制集》卷十四《臥病述懷》。
[69]《續修四庫全書》第789冊,第666—668頁。
[72](明)朱讓栩:《長春競辰稿》卷十一。
作者單位: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