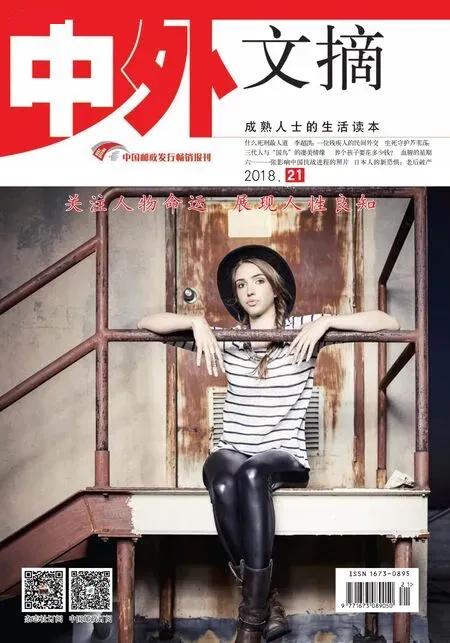施光南:如歌少年
□ 沙 青

童年施光南與父母的合影
音樂神童打的啞謎
很難忘記初見施光南時的印象,他那虎背熊腰的體格、黑黝黝的臉龐,曾讓我好生納悶。雖說人不可貌相,但若不是他談吐生動,舉止有度,短短一席話,居然旁征博引地脫口而出十幾個地方劇種的唱腔,我著實難在一次接觸中,將他五彩繽紛的歌曲作品,協調地統一在他那五大三粗的儀表之中。施光南的父母,一個出生在浙江諸暨,一個出生在四川江津。兩家家境貧寒,二人都在很小的年齡走上了革命道路。父親施存統,1920年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49年后曾任勞動部副部長,母親鐘復光是中國婦女運動早期領導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軍校第一批女軍官。音樂神童施光南就生長在這樣一個革命的家庭。
這個“怪癖神童”絕處逢生的真實故事,幾年來一直盤旋在我的腦際……
施光南的處女作是一支隨口哼出來的快樂的歌——“春天到了,桃花開開,小鳥飛飛,黃鶯在樹上叫,他們快活,我也快活,我們大家都快活。”那時他5歲。
施光南出生在山城重慶。1944年他長到4歲,母親不忍心把他獨自關在家中,帶他到自己任教的小學就讀。母子相距咫尺,兒子的一言一行保準會傳到母親耳朵里去。
“施光南今天又不好好聽講,老做小動作。”“你那孩子真淘氣,還影響其他同學。”也怪了,總是音樂老師到母親跟前告狀。有一天,音樂老師動了肝火。
這天的音樂課,老師在上面教唱《兩只老虎》。“大家跟著我唱:‘兩只老虎,兩只老虎’,唱!”……施光南沒唱,低頭自言自語。
一會兒,老師再讓唱,施光南揚著頭大聲唱起來:“肚子餓了,肚子餓了,要吃飯,要吃飯,吃飯沒有小菜,吃飯沒有小菜,雞蛋湯,雞蛋湯。”
哈哈哈哈……全班哄堂大笑。
老師大怒!拎起施光南的耳朵,狠狠往上揪。
“喲!喲 !痛啊 !”
“你為什么搗蛋?!”老師的手松了一點。施光南眼淚汪汪,說:“您教的歌,我早就會唱呀。”
“你還撒謊!說大話!”
“啪,啪……”施光南當眾挨了一頓揍。
哪個老師不喜歡規規矩矩的孩子呢?誰又愿意去琢磨孩子淘氣的原委呢?但兒童的天賦,往往就藏在頑皮之中。
施光南音樂天資之高,一支歌曲過耳即熟。記事不到兩年,他腦子里裝進去的歌,已經可以和一般成年人比個多寡。在施光南“挨揍”的第二年,重慶市舉辦小學生音樂比賽。音樂老師為施光南精選了演唱曲目。但臨近比賽,施光南卻哼哼唧唧自編了一支歌。
到了比賽上一唱,居然得了乙組第二名!這支被他母親記錄下來的歌,就是施光南的處女作《春天到了》。
舉凡神童,家庭催化、環境逼迫,常常是他們茅塞早開的根由。說來不信,施光南家中無一人偏好音樂。倒是他的父親施存統,早年求學于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時,不僅與一代音樂宗師劉天華同窗,還在現代藝術教育先驅李叔同的門下學習音樂。
雖然音樂名師在上,又與音樂巨子為伍,但施存統救國心切,終日在外奔走,以至于徹底荒疏了音樂學業。所幸,李叔同心寬地闊,讓這位始終未通音律的革命學生,每每拿得音樂課的及格分數。說不清是父親施存統的特殊閱歷讓兒子受益,還是施光南受命彌補父母的缺憾,總之,這個沒有音樂傳統的家庭中,孕育出一株生機勃勃的音樂幼苗。
上世紀50年代初,施光南隨父母到北京定居。
1956年夏季的一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少年合唱團舉辦音樂會。事先登出的演出廣告上,有這樣一個演出曲目:愛沙尼亞民歌《懶惰的杜尼亞》,詞曲作者是阿差杜利亞。當晚的演出中,這首曲調優美的“外國歌曲”通過女聲婉轉而略帶俏皮的演唱,贏得了滿堂喝彩。誰也沒有對這首歌的出處發生懷疑,更沒有人注意到一位徘徊在劇場外的16歲少年。這位少年就是施光南。他放學看到演出廣告,飯也沒吃,一口氣跑來等別人的退票。在所有演員與觀眾之中,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這個秘密:《懶惰的杜尼亞》的真實作者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
不脛而走的作品不止這一首。沒過多久,施光南隨父親去青島療養。一天,施光南偶然走進療養區的俱樂部。立在舞廳樂池譜架上的曲譜像磁石一樣吸引了施光南的目光。傍晚,俱樂部的門衛攔下了一個急匆匆、大有搗亂之嫌的小孩。“穿短褲禁止入場”,門衛指著俱樂部的章程給施光南看。
施光南氣惱卻無從爭辯。換個思路,一位來聽自己作品演奏的作曲家,怎么能被拒之門外呢。好在,施光南的父親隨后趕來,這才將他帶了進去。舞廳里熙熙攘攘。施光南默默坐在一隅。他眼巴巴地望著、等著,終于,樂隊開始演奏了……他兩年前寫的這首《圓舞曲》,不脛而走,在青島的舞池翩翩躍動起來。

施光南(圖右)與伍紹祖在一零一中學就讀時期的合影
這些作品都是施光南在一零一中學就讀的6年中創作的。
讀初中時,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韻律,看到窗外一片枯葉翻飛,便即興唱一支《落葉歌》。同學們聽他唱這唱那,好奇地打聽出處。他便順口謅出一個名字。后來,學校辦一個刊物《圓明園歌聲》,他被推薦當了編輯。這對一個隱名埋姓、孤獨創作的作曲者而言,真乃天賜良機!
施光南將自己各種風格特點的歌曲作品,標著不同國家、民族、作者的名字,統統刊登在《圓明園歌聲》上。以假亂真的《懶惰的杜尼亞》、匿名的《圓舞曲》,便是這樣流傳到社會上去的。
“怪癖人”想入非非
上高中以后,施光南突然變了。變得不求上進,怪得讓人難以理解。從小學到初中一直保持著全優成績,上高中以后,他卻跌進中游。
不求上進也就罷了,施光南終日愁眉不展,躲避同學,形單影只。同學因此送給他一個綽號“怪癖人”。
施光南也是真夠怪的,在宿舍睡到半夜,悄悄爬起來,跑到路燈下寫寫畫畫;上課時,不是被同學揭發“做小動作”,就是被老師點名“示眾”。最無厘頭的是,他發誓“只考4分”,高中3年,他堅定不移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說來,施光南的古怪變化,起因倒也十分簡單。初中畢業后,他冒出了一個報考音樂學院的念頭。周圍的人視其為“想入非非”。父母不能理解他,老師為了規勸他回心轉意,費盡唇舌。
施光南只剩下一個知己,他的同班同學、后來擔任全國學聯主席的伍紹祖。
伍紹祖公開講:“我們不能用一般的標準要求施光南,他說不定會成為真正的作曲家!”臨到高中畢業,伍紹祖還召集同學籌款謄印了一本《中外民歌選》。其實,這本歌集中的60余首“中外民歌”,皆為施光南的作品。
一個人理解施光南,畢竟太少了。施光南苦苦熬過了高中3年。畢業時,細心的母親發現了兒子的一腔熱望。
母親問施光南:“你現在最需要什么?”
“鋼琴。報考音樂學院要考鋼琴演奏。”
如果是在3年前,施光南剛好是音樂學院附中的適齡考生,那么他所面臨的考驗并不嚴峻。可現在,他已到了必須直接考音樂學院的年齡。按照該院作曲系的報考規定,他不僅要具備彈奏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能力,還要掌握相當程度的樂理知識。這對于一個從未摸過鋼琴,對樂理知之甚微的學生而言,簡直就是癡心夢想了。更何況,距離考期只剩下半年時間。
施光南臨時抱佛腳,跑去買了一本《拜爾鋼琴教程》。母親四處托人找鋼琴教師。不知轉了多少個彎,總算尋到一位家住東四的私人鋼琴教師林太太。母親揣好學費,拎著禮品,帶著施光南來到林太太門下。
林太太正在鋼琴前教一個小男孩。聽見腳步,稍稍抬起頭,從眼鏡框上面瞥了一眼來人:“找誰?”
“我們是來學鋼琴的。”母親忙答。
“誰學?”母親趕緊把施光南推上前去。
17歲的施光南原本長得粗壯高大,和四五歲的小孩站在一起,真像是羊和駱駝站在一起。

施光南與妻子在家中

施光南與《打起手鼓唱起歌》的詞作者韓偉以及演唱者關牧村
林太太說:“我從來不教這么大的人。喏,手指早僵了。”
母親再三央求,并說明這是燃眉之急。
林太太不聽則已,一聽便咧嘴笑了:“他還要考音樂學院?!人家可要的是幾歲開始學琴的喲。你們當家長的也是,想讓他學怎么不早點……”
母親拉起施光南,原路退了出來。
半年一晃就過去了。施光南斗膽走進了中央音樂學院考場。
第一關是筆試,施光南闖這一關可算是出盡了風頭。但接下來的和聲、樂理考得一塌糊涂不說,考聽力,他雖然聽力良好,卻不懂音樂術語,答得風馬牛不相及,硬是把嚴肅的監考老師逗得忍俊不禁。
眼看是山窮水盡了,施光南卻硬著頭皮又去過第二關。
一進考場,好家伙!面試考場里迎面一排監考人,正襟危坐。施光南還沒定住神兒,坐在當中的江定仙教授(作曲家,代表作品有《煙波江上》等)便發了話:“你自報曲目吧。”
“我彈莫扎特的《G大調小奏鳴曲》。”話音剛落,考場內傳出輕蔑的噓聲:彈這么簡單的曲子,只配去考音樂小學!
施光南的手指尖觸到硬冷的琴鍵,一下哆嗦起來。喲!彈錯了……重來,又錯了……真是越急越亂,越亂越急……拼命學了半年鋼琴,怎么趕得上人家的童子功喲!再說連個老師也沒找著,只能一個音符、一個音符的自己摳下來。怨父親嗎?他是沒舍得給你買鋼琴,也沒利用自己的地位幫你找一位老師,卻舍得把兩萬元積蓄全部捐獻給國家,這讓你只能在別人家的鋼琴閑下來時插空彈一會兒。但你理解他,他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又是著名經濟學家,他有自己的理想、信念……
監考老師似乎對施光南失去了信心,不經意地讓他進入下一項:彈奏一首復調曲。施光南一報曲目,考場內又是一陣騷動:小奏鳴曲沒彈下來,他還敢彈《牧童短笛》?簡直是胡鬧!
施光南看上去比前一次倒輕松了許多。他的手指靈活地輕觸琴鍵,《牧童短笛》流暢地飛揚起來。
“我再彈一首《流水》。”施光南爭取了主動。
“誰的作品?”
“我的。”
“?!……”
《流水》在考場中流動了起來,時而溪流潺潺,時而瀑布飛降,時而巨浪排空……全場為之驚愕。為何莫扎特的《G大調小奏鳴曲》彈不成,后兩首卻得心應手?
原來,施光南經過半年的獨自摸索,總結出一套彈五聲音階的鋼琴指法,正適合彈奏《牧童短笛》。而《流水》的魅力,則更多的得益于他的作曲才能。
再接下去的考試項目是演唱民歌。施光南這下可如魚得水了。他先是唱京劇《斬黃袍》,接下去是川劇《投江》、蘇州評彈《宮怨》、河南墜子《鳳儀亭》。唱罷戲曲又唱民歌,若不是江定仙先生連連說:“打住,打住吧。”他真想把肚子里上百首民歌,一股腦兒都倒在考場上……
考試結束才得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這一年并不錄取學生。施光南徹底絕望了。就在他痛苦萬分、不知往何處去之際,忽然收到了監考的江定仙先生的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施光南同學……你的基礎知識較差,但考慮到你有良好的音樂感覺和作曲才能,建議你去附中插班學習……”
真是路遇良知,絕處逢生,施光南由此邁上了音樂殿堂的臺階。
新聞人物與“尾巴”同學
施光南來到當時還設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附中,轉眼就成了附中二年級的“新聞人物”。“江定仙先生推薦來的”,只這一句傳言,同學們就對施光南另眼相待了。
施光南到校的第一天,一群不知深淺、又想試試深淺的同學先給施光南來了個下馬威。
“彈一段吧。”這不算過分的要求。
施光南老實巴交,傾其所有、盡其所能地彈了起來。圍觀的同學先是指指點點,繼而擠眉弄眼,最后嗤之以鼻。哈哈,鬧了半天,來了個業余范兒的!看他無名指那個木喲,小拇指倒要翹到天上去了……
“你是跟誰學的?”一位同學冒了一句。
“自己學的。”
“自己學?”從小被老師手把手教出來的孩子,實在無法想象鋼琴怎么能夠自學。
“哎,你喜歡什么作品?”又一位同學發問。
“我喜歡民歌,還喜歡京劇、昆曲……”
“我問你喜歡什么大作曲家的,外國的,懂嗎?”
“嗯。我喜歡蘇聯的杜納耶夫斯基的歌。”
“瞎,你難道就不喜歡偉大的作品?比如,肖斯塔科維奇的協奏曲、奏鳴曲。”
“不太喜歡。”
“噓,噓……”噓聲夾雜著說笑聲漸漸遠去。
周圍安靜下來,施光南迷惑不解:我說錯了什么?
對于藝術,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興趣點和愛好范圍。但在頂尖音樂殿堂,施光南敢直言不喜歡外國大音樂家的作品,卻說喜歡土生土長的戲曲,這在學西洋音樂的同學眼睛中,如果不是大逆不道的瘋子,就是個地地道道的土包子。
初次交往,同學們便領教了施光南的“業余”。接下來,施光南更是成了“尾巴”。二年級的視唱練耳課原本為成績平平的學生開了一個乙班,施光南一來,又專為他設了一個丙班。這下,施光南成了班里名副其實的“尾巴”。問題是,這個“尾巴”同學居然敢“說大話”。一天,班里開生活會,一位同學指著施光南的鼻子說:“他連肖斯塔科維奇都看不起,他也太驕傲了!”
施光南是個要強的人,他受不了這么牽強的指責。一散會,施光南沒影了。老師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最后是民警把施光南從火車站送了回來。
施光南帶著他的“先天缺陷”步入音樂殿堂。但天才畢竟是天才,他很快就成為視唱練耳甲班的課代表。連年的全優成績,更使他成為整個年級的佼佼者,成為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的高材生。就連他那半路出家的鋼琴演奏,因為在畢業考核時演奏了作曲專業的學生無人敢碰的格里格《A小調鋼琴協奏曲》,讓同學們嘆服。
在天津音樂學院上課之余,施光南創作的小提琴獨奏曲《瑞麗江邊》廣為流傳,他寫的《革命烈士詩抄》套曲也頗多佳評。漸漸的,作曲界開始注意到了這樣一個鋒芒初露的新人。
神童的黃金時代
施光南大學畢業了。天津音樂學院和施光南進修過的中央音樂學院爭相承認他是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
上世紀70年代初,施光南拿出了新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這首一反當時格調的抒情歌曲,風傳全國。緊接著,他又創作了激情、奔放的獨舞《鴻雁》的音樂。這讓那些妒火中燒、靠追風逐浪發跡的人抓住了“把柄”。
“資產階級的輕歌曼舞”、“沙龍音樂”……一摞摞帽子扣在了施光南頭上。一時間,不僅作品被電臺、出版社列為禁物,連施光南自己也被驅趕到農村去勞動“贖罪”了。
1976年的最后一夜,施光南伏在鋼琴上,淚水滾滾滑落。翌日清晨,《周總理,您在哪里》的曲譜端端正正地擺放在鋼琴上。當這首意境深邃的歌曲飄蕩在大街小巷的時候,施光南還覺得意猶未盡。恰巧,他的老搭檔韓偉寄來了《祝酒歌》的歌詞。施光南吟之動情,拍案叫絕。幾天后,采用民間鼓點節奏譜寫的《祝酒歌》完成了。
嚴冬剛過、春寒料峭。盡管一年后電臺才將這首激越昂揚的歌播送給聽眾,但春天畢竟來了!
施光南從此進入了他創作的“黃金時代”。他心中,樂思綿綿如絲,他則像一只無盡無休吐絲的蠶,春去冬來,夜以繼日。到了年底一算,嗬!平均3天創作一首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