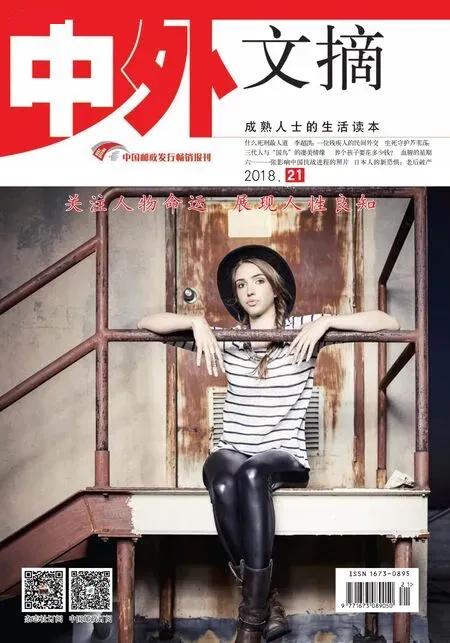也無風雨也無晴:《讀書無禁區》及以后
□ 沈昌文

沈昌文
《讀書無禁區》及以后
幾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說過這樣的話:“記得《讀書》雜志,不必去記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記李洪林。原因很簡單,李洪林在《讀書》創刊號上發表過一篇有名的文章:《讀書無禁區》,由是使中國讀書界大受震動,《讀書》雜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我至今仍然這么看。
《讀書》雜志一九七九年四月創刊時,我還沒去《讀書》雜志,并沒有經手這篇文章,但是它引起的震動,卻是我感同身受的。這篇名文一直為人稱道。所為者何?原因很簡單。這里首先分析批判了史無前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的禁書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禁書,確是“史無前例”,今天的年輕讀者絕難索解。三十多年后,仍然禁不住我大段摘抄這篇名文的沖動。
請先讀這篇名文中對“四人幫”禁書政策的揭發:
在林彪和“四人幫”橫行的十年間,書的命運和一些人的命運一樣,都經歷了一場浩劫。
這個期間,幾乎所有的書籍,一下子都成為非法的東西,從書店里失蹤了。很多藏書的人家,像窩藏土匪的人家一樣,被人破門而入,進行搜查。主人歷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圖書,就像逃犯一樣,被搜出來,拉走了。
這個期間,幾乎所有的圖書館,都成了書的監獄。能夠“開放”的,是有數的幾本。其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莎士比亞到托爾斯泰,統統成了囚犯。誰要看一本被封存的書,真比探監還難。
書籍被封存起來,命運確實是好的,因為它被保存下來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當中被燒個精光。后來發現,燒書畢竟比較落后,燒完了灰飛煙滅。不如送去造紙,造出紙來又可以印書。這就像把鐵鍋砸碎了去煉鐵一樣,既增加了鐵的產量,又可以鑄出許多同樣的鐵鍋。而且“煮書造紙”比“砸鍋煉鐵”還要高明。“砸鍋煉鐵”所鑄的鍋,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鍋,是簡單的循環;而“煮書造紙”所印的好多書,則是林彪、陳伯達、“四人幫”以及他們的顧問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書。這是一些足以使人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新書,其“偉大”意義遠遠超出鐵鍋之上。于是落后的“焚書”就被先進的“煮書”所代替了。
如果此時有人來到我們的國度,對這些現象感到驚奇,“四人幫”就會告訴他說:這是對文化實行“全面專政”。你感到驚訝嗎?那也難怪。這些事情都是“史無前例”的。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究竟對多少書實行了“專政”呢?《讀書無禁區》的作者寫道:
在“四人幫”對文化實行“全面專政”的時候,到底禁錮了多少圖書,已經無法計算。但是可以從反面看了一個大概。當時有一個《開放圖書目錄》,出了兩期,一共刊載文科書目一千多種。這就是說,除了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書籍之外,我國幾千年來的積累的至少數十萬種圖書,能夠蒙受“開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種!
除了秦始皇燒書之外,我國歷史上清朝是實行禁書政策最厲害的朝代。有一個統計說清代禁書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種。蔣介石也實行禁書政策,他查禁的書不會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幫”的禁書政策相比,從秦始皇到蔣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農醫書籍除外(這類書,秦始皇也不燒的),清朝和國民黨政府查禁的書,充其量不過幾千種,而“四人幫”開放的書,最多也不過幾千種,這差別是多么巨大!
中國的出版社原就不多,“文革”前只有八十七家,職工約一萬人。“文化大革命”中,經撤銷、歸并,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五十三家出版社,職工四千六百四十九人。中央級的所謂“皇牌”出版社五家(人民、人民文學、人民美術、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注意:三聯書店早在一九五三年裁撤,當時早已不存在了),原有職工一千零七十四人,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編輯六十三人)。上海原有十家出版社,職工一千五百四十人(以上據《中國當代出版史料》,第六冊,六十二頁)。
讀書人見不到書,怎么辦呢?一位朱正琳教授近年回憶他的青年時光說:
記得我興匆匆跑到離家最近的一家書店時,那景象真讓我吃了一驚。書架上空空落落,已經沒剩下幾種書了。我站在那里,只覺得手足無措。一種失落感漸漸變成一種悲憤之情,我突然作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舉動:幾乎是當著售貨員的面,我從書架上拿了兩本《斯大林選集》就往外跑。
這以后我索性退了學,躲在家里讀書。自己擬了個計劃,系統地讀。想讀書,書好像就不是問題,我總是有辦法找到我想讀的一些禁書。后來則更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到各個學校的圖書館去偷書。一家一家地偷下來,我們幾個人的藏書種類(限于人文類)就超過許多家圖書館了…
偷書的好處不僅是有書讀,而且還讓我們大開眼界——許多“內部發行”的讀物讓我們見著了,這才知道山外有山。
只可惜還沒來得及讀多少,我們一伙就已鋃鐺入獄,那些書自然是被盡數沒收。不過我們被捕的案由卻不是偷書,而是“反革命”。那時候趕上“中央”有文件要求注意“階級斗爭新動向”,說全國各地出現了一些“無組織、無綱領但實質上是”的“反革命集團”。于是全國各地都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被捏成一個個不知其名的“集團”,有些地方則索性命名為“讀書會”。我們幾個人被定為在貴陽“破獲”的“集團”(據說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的“學生支部”成員,我們的“地下書庫”簡直就是天賜的“鐵證”。這一坐牢就坐了四年多。待到出獄時,離本文篇首所說的排隊買書的日子已經不太遠了。排隊買書之后緊接著是《讀書》雜志復刊,頭條文章的標題是《讀書無禁區》。從那時起我開始與“饑荒”告別,漸漸地卻發現,市面上有越來越多的書讓我相見恨晚。(《里面的故事》,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五年七月版)
《讀書無禁區》這篇文章發表后,引起了一場風波。有一陣子,有人還認為,此文的宗旨是“不要黨的領導,反對行政干預,主張放任自流”。有人甚至認為,文中在“毛澤東”后未加“主席”兩字,就是反動思想的表現。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狀。
范用說:“《讀書無禁區》原來的標題是《打破讀書禁區》,發稿時,我把篇名改成了《讀書無禁區》。”當時,他并非不知道這樣做會有麻煩,但是,“我當時心里就是這么想的,因為毛澤東讀書就沒有什么禁區”,范用說。此前,他有數年時間專門給毛澤東買書。
雜志出來后,上級主管機關先找范用談話,批評“讀書無禁區”提法不妥。范用說:“我當時進行了辯解。估計那位領導沒有仔細讀完這篇文章。因為里面的內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鎖,文章有一段說得很清楚,‘對于書籍的編輯、翻譯、出版發行,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對于那些玷污人的尊嚴,敗壞社會風氣,毒害青少年身心的書籍,必須嚴加取締’。”他還說:“我個人認為,我們要相信讀者的判斷力。即使是不好的書,也應該讓他們看,知道這些書不好在什么地方。”
以后,連續刊發了幾篇批評和反批評的文章,做公開討論。《讀書》的實際負責人倪子明以“子起”筆名寫了贊同的文章。尤其是,當年人民出版社的領導曾彥修用筆名“范玉民”,發表了一篇《圖書館必須四門大開》。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意思。過去“圖書館”三個字有一種簡寫,就是把書字放在一個大“口”字里。“范玉民”從這個字出發,建議圖書館去掉外面的“口”,普遍向讀者開放。這表面上是討論文字,實際上探討的是一個社會問題——當時書店不準賣這書那書,連圖書館的許多書也不能外借。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讀書》又發了一篇重要文章:《實現出版自由是重要問題》,作者于浩成。文中指出:“一切由國家壟斷,統得太死,管得太嚴,缺乏競爭,是當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實現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于出版事業的發展和繁榮。”“言論出版自由的問題不解決,憲法上的有關規定也就是一紙具文,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空的。”這篇文章出自延安老干部之手,上面也無可奈何,但對《讀書》自然是更加警惕了。
在一九八一年《讀書》創刊兩周年的時候,陳翰伯親自執筆寫了一篇《兩周年告讀者》,重申辦刊宗旨,文中坦蕩地堅持“讀書無禁區”的主張,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絕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聽憑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辦法,更是不足為訓。我們愿意和讀者一起在激蕩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點智慧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結束,我調到《讀書》雜志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代表雜志到上級部門作檢查。我代表編輯部寫過一些書面檢查。后來,出版總署通知我去出席一個各出版社領導人的會議,事先通知我要在會上作沉痛的深刻的檢查。我花不少時間準備了稿子。到了會場,議程排來排去,一直沒有安排我上場。最后散會,我一言未發。以后也不再提這事。那次會議,主持人是杜導正。近年多讀此公言論,有點覺得他那時實際上是在故意放我們一馬。未知然否。
《哪壺水不開提哪壺》和《跪著造反》
《讀書無禁區》事件后,糾紛還是不斷。不久,《讀書》上又有文章批評海關對進口書刊檢查太嚴,例如有人帶了有裸體畫插圖的圖書進關時要被沒收。海外文化人士如韓素音對這很反感。這一來惹得海關大怒。他們要求著文答復,文中強調他們是執行中央的方針。這一來,弄得我們有點無可奈何。
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發了一篇《人的太陽必然升起》,作者是李以洪,一位女作家。文中主張人性解放,說“三十年來,我們曾經把尊敬,熱愛,信任和崇仰無限制地奉獻給神,現在是償還給人的時候了”,“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曾經成了禁區。但是神封的大門一旦被實踐推開,巨大的能量就會被釋放出來,豐富的精神蘊藏就會在實踐中煥發光彩。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所有社會實踐的領域都將迸發著摧枯拉朽、振聾發聵的聲響和火光,以此歡慶歷史新時期的開端。這將是人的重新發現,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人的重新發現”,文章最后提出:“神的太陽落下去了,人的太陽必然升起。”
文章寫得真精彩,我們編輯部全都拍案叫絕,但我們都擔心能不能發,并請示了陳翰伯、陳原兩位老先生,陳原讀后立即回話:一字不改,全文刊登。不久就有一位老作家馬上寫了一篇反駁文章《狗的月亮已經升起》。后來知道,這兩篇文章的爭論,其實背后是周揚、胡喬木對“人性論”的爭論。
還有一類糾紛屬于另一種性質。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上發表了老作家李荒蕪的一些舊體詩,總題是《有贈》,最后一首是《贈自己》。李先生是外文局系統的老前輩,馮亦代的老朋友。一九八〇年第四期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的內部刊物《未定稿》上發表了朱元石的批評文章。元石認為這些詩作表達了對現實的不滿,加以猛烈的抨擊。他同人民出版社當時的黨委書記(我那時的最高領導)相熟,又把文章寄他,請他轉《讀書》發表。書記當即批示我照辦。
李荒蕪的原詩說:“羞賦《凌云》與《子虛》,閑來安步勝華車。三生有幸能耽酒,一著驕人不讀書。醉里欣看天遠大,世間難得老空疏。可憐晁蓋臨東市,朱色朝衣尚未除。”元石說作者“不過是拈封建士大夫階層失意文人的筆觸,來刺中國人民生活著的社會主義‘現實’罷了”。這顯然荒唐,但是元石有“來頭”,怎么辦?
經過了解,李荒蕪是當年的“右派”,曾在黑龍江原始森林里伐木為生,進行勞動改造。他對此自然不滿。于是那些老左派一直盯住他的言論不放,要在雞蛋里挑骨頭。
幸好,我背后還有更高的領導——陳翰伯,經他和陳原等同意,不予發表。陳原當時有一句名言,獲得大家首肯:“《讀書》的性格,應當是容許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但不容許打棍子。”元石此文經各人反復閱讀,認為不是爭鳴,而是“棍子”,乃退。
(盡管如此,后來聽說,李荒蕪這位老人以后多年處于無欲望無興趣的境地,臨終遺言是“但求安靜”四字。這想必同改革開放以后左派仍然對他窮追猛打有關。我們雖然沒有加入窮追猛打,但是過于潔身自好,也不全對。)
經過這一系列事件,我知道,我們正面臨著一個新的考驗。
怎么辦?
在這關口上,范用有一次跟我講了一件事情。我們三聯書店的頭頭鄒韜奮,他辦的刊物有一次得罪了日本人,日本人找蔣介石,蔣把我們的刊物封了。這就是所謂的“《生活》事件”。但是因這一來,三聯書店刊物的名聲更大了。因此,我們要敢于講話,不怕封。
我聽了大為驚訝。他的這種態度我如何學習和實行?我私下里跟陳原談了這事。陳原很擔憂,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他認為現在歷史條件改變了,共產黨掌握政權了,不能那么做了。但是他認為時下不合理的事確實不少,我們的雜志要說話。如何說話,可以研究,但不必采取國統區的辦法。這話對我深有啟發。
也在這時,上面也有人說話了。上級機關批評我們的用語是:你們現在“哪壺水不開提哪壺”,意為你們專愛做上面不讓做的事。
這倒也對。的確,我們編輯部里面有幾位是熱衷于此道的。我那時算是實際負責人,他們惹出麻煩,一切都在我身上。雜志一出事,上面和單位,都來找我。我該如何是好?范用屢次說,有事他擔當。但是,上面開會,他從不出席。他只對我說,“讓他們來找我,我才不找他們呢!我做出版的時候,他們在哪里?”
在這萬般無奈之際,我想起了六十年代“反修”時,我們常常引用的一個故事。列寧批判考茨基的時候,指出考茨基之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無非是“跪著‘造反’”。我們后來反修,多次例舉這一故實。我覺得,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批評種種不合理之事,大可借用這說法,以此行事。因為它可以解釋為“小罵大幫忙”,從根本上說,是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并擁護社會主義的。
以后,我就以此作為我行事的準則,并不斷宣揚。這是我不敢被“封門”的懦弱表現。我大概這輩子也學不到韜奮先生,包括范用了。我在三聯書店系統的幾十年里,范用不斷罵我“沒出息”,以致一再絕交。以此開端,良有以也。
厚積薄發,行而有文
“跪著造反”這一總方針之下,《讀書》對文章的具體要求,首先是“厚積薄發,行而有文”。從陳原開始,《讀書》雜志就主張文章要寫得有文采,“不文不發”。我們退掉過很多著名學者的稿子,他們的觀點很可以,但是文筆實在不行。比如,老革命何方的稿子被我退掉過兩次。有一次何方寫了一篇《記李一氓同志的為人和幾個重要觀點》的文章,談李老的古典詩詞。李一氓是中國共產黨里面最有文采的人之一,但是何方的文章卻寫得像社論,大家覺得實在沒辦法用。結果何方后來到處告我的狀。又如王亞南先生的學生孫越生先生,所寫關于官僚主義的文章分析很深刻,但乏文采,我記得也壓下未發或少發。近年讀一些思想先驅者的文章,對他的觀點評價頗高。
在那時候,文章要能做到這八個字的,只能找文壇老人。那時完全想不到,在八十年代,找老一代名家組稿有多容易。因為那些老人受困多年,大都還挨過整,現在一旦解放,是多么想寫些東西,一抒胸懷。可以說,《讀書》雜志當年之所以成功,大都得力于他們。
我首先要提到呂叔湘老先生。我同他老人家結識后,他知道我從學徒時期開始,就不斷自習他的著譯。從《中國人學英文》開始,到讀他譯的《伊坦弗洛美》,一直到在做校對員時自學《語法修辭講話》而出人頭地。他很樂意指導我編刊物,幾乎每月讀過《讀書》后就寫一封信給我,提出意見。他的不少意見,具有方針性,不只是就文論文。如他說:
編《讀書》這樣的刊物,要腦子里有一個general reader(翻成“一般讀者”有點詞不達意,應是“有相當文化修養的一般讀者”)。要堅持兩條原則:一、不把料器當玉器,更不能把魚眼當珠子;二、不拿十億人的共同語言開玩笑。
他還為《讀書》總結了風格:
什么是《讀書》的風格?正面說不好,可以從反面說,就是“不庸俗”……可是這“不庸俗”要自然形成,不可立志“不庸俗”。那樣就會“矜持”,就會刻意求工、求高、求深,就會流于晦澀,讓人看不懂。
當然,他自己也為《讀書》寫了許多耐讀的好文章。
還有金克木先生。我們去找這位老先生之前,編輯部內的老人就同我們打招呼,說這位老教授特別不好對付,脾氣特大。等我們一接觸,發現完全不是如此,同金老特別容易親近。我想這可能因為過去是“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老知識分子看到官方的編輯不免要有幾分警惕。現在不一樣了。我同他談話,總是無法結束。他送行時,同你握手言別,然后手握門把,還要談三五分鐘。一次趙麗雅找他寫一篇稿,他一口氣寫了五篇,統統請趙處理。金老的文章特別受讀者歡迎。正如陳平原教授后來所說,“像他那樣保持童心,無所顧忌,探索不已的”,“難以尋覓”,“以老頑童的心態和姿態,挑戰各種有形無形的權威——包括難以逾越的學科邊界,實在是妙不可言。”
還可以舉一位舒蕪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就認識舒先生,和舒先生在一棟樓里辦公。不過那個時候,舒先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一般在樓東辦公,而我在樓西,很少見面,也沒有什么接觸。尤其,政治上他是“胡風分子”,我們看到他都要躲著走。但改革開放后,情況就完全改變了,我開始認識到,舒先生是一個真正有學問有見解的學者。舒蕪先生給《讀書》雜志寫的文章之多,大概為眾老者之首。他的文章言之有物,有許多不錯的見解,比如,他對周作人等當時的一批老學者都有很多看法,在許多方面對我們有許多啟發。老先生受了五四的影響,特別關注女性問題,往往有過人的見識。
還如張中行先生。剛開始時,聽說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要不要去找他,很猶豫。后來一生二熟,發現這老頭真能寫。那時主要由趙麗雅同他聯系,他們很快成為了知己。張老為《讀書》越寫越多。在他只是隨便寫寫,卻把埋藏在深處的寫作熱情給挖掘出來。正如有的評論家所說,本來打口井取點水喝,沒想到一下子冒出了豐富的石油。值得一提的是,張中行先生對趙麗雅有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三年他寫了一篇名為《趙麗雅》的專文,居然說:“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沒有離開書,可是談到勤和快,與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風。”作者和編輯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實為我畢生所僅見。
寫到這里,我禁不住想起一位奇人——勞祖德(谷林)。我早在五十年代就認識他。那時他是出版總署財務處的官員,財務專家。寧波人,滿口鄉音不改,所以我非常愿意聽他說話。料不到,到改革開放年際,這位先生寫作之勤快,作品之耐讀,完全出乎我輩意外。在我主持《讀書》期間,他寫文不下百篇。這樣深藏不露的學問家,多年由趙麗雅聯系。他們都有“深藏不露”的特點,所以特別談得來。
老人中應當還有顧準,盡管《讀書》創刊時他已作古。范用最早欣賞顧準,我由他才知道,顧準的弟弟陳敏之先生原來是“老三聯”出身的,現在上海。我很快同他取得了聯系,得到一篇稿件,立即發表。可以說,《讀書》是國內最早發表顧準文章的。可惜的是,后來得到一篇是談毛澤東思想的文章,我不敢發,怕挨批。以后貴州出書,此文已收入,說明我太膽小了。怨不得范用對我的膽小恨之入骨。
我們很榮幸地能請到一些老革命家為我們寫稿。例如夏公(夏衍)一九八四年二月特地給《讀書》寫了篇《關于讀書問題的對話》,有很大影響。于光遠老先生也經常來稿。這些,大都由范用親自組稿,或者他指派董秀玉辦,我很少插手。
上面經常批評《讀書》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力。這是我們的一大難事。我們不反對談這些,只是找不到好文章。后來,我想到了龔育之。他過去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時我們有接觸,我發覺他有文墨氣,不像官員,辦《讀書》后,還常往還。現在我帶這難題向他討教,他說,這好辦,我來開一個專欄。不久,這個名為“大書小識”的專欄就開場了,他用了一個筆名“郁之”,文章寫得不俗,又符合大方向,快何如之!
還有一位專家用很特別的方式關心我們,這是近代史研究所的沈自敏先生。他老先生沒事就來編輯部同我們聊天,說的都是“閑話”,實際上是代表了一位老學者對學術界、對《讀書》文章的看法,使我們十分得益。
老一輩的大家,還能列出不少,如:許國璋、王佐良、王宗炎、陳樂民、徐梵澄、何為、柯靈,等等,這里不多說了。至于老一輩以下,大多是當年剛露頭角的留學生,留待別處去說吧。這里還想表一下的,是我個人聯系老學者時的幾個敗筆。
首先是錢鐘書。這位老人家一直是由董秀玉聯系的。她去香港工作,我頭腦發熱,很想趁機同這位老人家有些接觸。我是《圍城》迷,五十年代喜歡得發瘋,連當時自己所譯的書,署名一概是“魏城”。在錢府同錢老晤談幾次,都很高興。后來,三聯書店要出版一套學術叢書,想請錢老署名編委。我很愿意去當說客,欣然而往。錢老也欣然同意,楊絳在旁,也沒發表意見。不料,幾天后又去錢府,楊絳對我說:“外面傳錢鐘書要列名三聯書店某某叢書編委,這是謠傳,沒有這事。我想這是欒貴明搞的,你們別去聽他。”我一聽大驚。那不是我同你們兩位老人家前幾天當面議定之事?本想辯解,轉而一想,其事必有緣故,還是作罷為好,于是唯唯而退。回社后將已排的顧問名單一概撤銷,從此絕跡錢府。
還有一件事是同季羨林老先生有關的。學界傳聞,季老同金克木老先生不和,我們既同金老莫逆,也就不去多找季老。但在某日,我本人忽然接到季老一個電話,說你們刊物上盡發文表揚出版總署官員宋木文當編委的叢書,貶低我們編的一套關于四庫全書的書,太不公平。你們編刊物,只聽官員意見,逢迎拍馬,太不像話,我要寫信抗議。我聽后惑然不解,只能表示,研究研究。以后收到來稿,方知他是批評丁聰、陳四益兩位的詩配畫中的論述。這個專欄談什么書,同官方何涉?陳先生也絕不會同官員有關,而官員宋木文也絕不是喜歡別人逢迎的人。再一打聽,方知季老這一動作同某書某書的商業利益有關,季先生是明顯給人利用了。如何辦?橫下一心,把季文原樣發表。以后由陳四益先生為文反批評,很是熱鬧了一場。我由是知道季老為事的特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