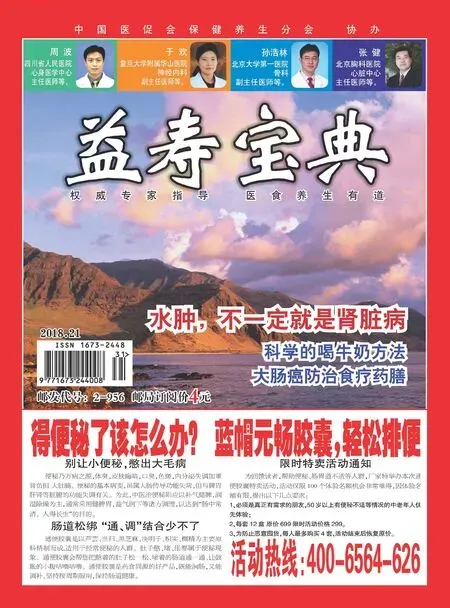中醫藥在古詩里飄香
文/錢海

“竹葉柳蒡道,泰山磐石邊。龜鹿二仙興至,逍遙桂枝前。更有四君三子,大小青龍共舞,玉女伴天仙。陽和桃花笑,碧云牡丹妍。酥蜜酒,甘露飲,八珍餐。白頭翁醉,何人送服醒消丸?涼膈葛花解酲,保元人參養榮,回春還少年。四海疏郁罷,常山浴涌泉。”短短的一曲《水調歌頭·湯頭拾趣》容納了30個藥方名稱。藥名詩、本草詩、養生詩……詩詞中的中醫藥,將中醫藥的博大精深與詩詞的優美韻律完美結合,既便于記憶,也體現了“儒醫”的文化底蘊。
藥名詩
“是草皆為藥,無山不出云。”作為極具觀賞價值和食用價值的植物,許多中藥如菊花、芍藥、菖蒲、黃芪、丁香等,都已是詩中常客,單單《詩經》《楚辭》中的中藥已不在少數,但卻算不得嚴格意義上的中藥詩。算得上的,要數藥名詩。
藥名詩多取當歸、熟地、益智等字面含義,或以諧音字隱藏藥名,或為藥名之謎面,或以藥名分嵌于詞之首尾,讀來不覺有回環往復之趣。古來文人多涉獵醫書,蓋為求文字之樂,詩客騷人多有藥名詩傳世。“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簡文帝蕭綱的這首詩是最早流傳的藥名詩。
南宋豪放派詞人、愛國將領辛棄疾留給后世的藥名詩較多,其中的《滿庭芳》和《定風波》最為出色。如《滿庭芳·靜夜思》“云母屏開,珍珠簾閉,防風吹散沉香,離情抑郁,金縷織硫黃。柏影桂枝交映,從容起,弄水銀堂。驚過半夏,涼透薄荷裳。一鉤藤上月,尋常山夜,夢宿沙場。早已輕粉黛,獨活空房。欲續斷弦未得,烏頭白,最苦參商,當歸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黃。”再如《定風波·邀醫生馬荀仲同游》:“山路風來草木香,雨余涼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風月費篇章。”暗藏木香、禹余糧、石膏、防風等藥,可謂工巧。最后在“湖海早知身汗漫,誰伴?只甘松竹共凄涼”中,把甘松這味中藥嵌入詩句中,既不失詩情,又別有一番風味。
穴名詩
穴名與藥名一樣可以入詩,梁朝編有《針穴名詩》。明朝李梃曾作穴位即景詩,每詩合一景,如《野寺》:“隱白云中一老僧,大都離俗少人憎,幾回太白商丘過,汲取陰陵泉幾升。”名義寫野寺,實寫足太陰脾經5個重要穴位:隱白、大都、太白、商丘、陰陵泉,還把老僧下山汲水之境寫入詩中,令人回味無窮。
更有值得后世研究的是,由明代楊繼洲著、靳賢補輯重編的《針灸大成》,將人體的奇經八脈與十二正經相通的8個穴位都以一首《西江月》釋義,而且還涵蓋這個穴位所有的主治病證。例如內關穴:“中滿心胸痞脹,腸鳴泄瀉脫肛,食難下膈酒來傷。積塊堅橫脅搶,婦女心痛脅痛,結胸里急難當,傷寒不解結胸膛,瘧疾內關獨擋。”
本草詩
詩詞專寫藥性、藥理,并有醫家專門研究的,稱為本草詩。清代趙瑾叔的《本草詩》、朱東樵的《本草詩箋》、陸典的《本草詩》為此類詩集代表。如趙瑾叔寫紅花:“紅花活血味辛溫,火焙還教用酒噴。遍體瘡瘍苗可搗,天行痘疹子須吞。宣通枯閉經中滯,救轉空虛產后昏。記取當歸常共用,不愁燥糞結肛門。”將紅花的性味、炮制方法、功效主治寫入詩,清晰明了,易于記誦流傳,不失為中醫藥文化與知識傳承的有效方式。
當然,歷史上文人騷客也做本草詩,蘇東坡曾贊薏苡仁:“不謂蓬狄姿,中有藥與糧,舂為芡珠圓,炊作菰米香。”畢竟藥食同源,薏苡仁兼有二妙,詩也清新素樸。
養生詩
詩詞中亦不乏養生、保健、疾病與醫治的記載,道家專有養生保健詩。
白居易可謂其中楷模,因其手不釋卷,酒不停盞,“書魔昏兩眼,酒病沉四肢”,曾作詩道:“早年勤卷看書苦,晚歲悲傷出淚多。眼損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頗見眼病之苦,悔恨之切。并進一步詳細描述癥狀:“散亂空中千片雪,朦朧物上一重紗。縱逢晴景如看霧,不是春天亦見花。僧說客塵來眼界,醫言風眩在肝家。”可見他當時已視物不清,大概患了近視或者老年性白內障。為此,白居易四處求醫,并將診治經過續寫于詩中:“醫師盡勸先停酒,道侶多教早罷官。案上漫鋪龍樹論,盒中虛捻決明丸。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詩意為:醫生曾建議我戒酒,除去功名修心養性,常讀眼科專著《龍樹論》,并服用眼疾的常用方劑決明丸,可我服藥后無效。最后醫生決定采用金針撥障術,即針撥白內障術,試著去除我的眼疾。通過這首詩,后人可見唐朝完整的眼科醫治病案。
作為同歲至交,留下“生疾不必太憂心,三治七養謹而慎”養生名句的劉禹錫與白居易書信往來頻繁,他在《閑坐憶樂天以詩問酒熟未》中也曾勸導過白居易:“案頭開縹帙,肘后檢青囊。唯有達生理,應無治老方。減書存眼力,省事養心王。君酒何時熟,相攜入醉鄉。”在詩中,劉禹錫建議白居易常讀醫術,減少過度使用眼力。
——中醫藥科研創新成果豐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