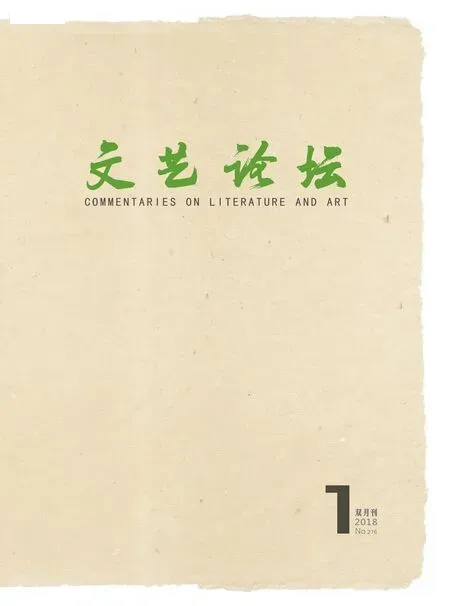文化意識與電影敘事
——談中國電影對“中國夢”的影像建構
◎ 溫立紅
中國的發展和中國電影的發展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和它與“中國夢”展開的過程的關系異常緊密①。新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在敘事層面講好故事以建構“中國夢”的歷史使命,在文化意識上闡釋和繼承幾千年的文化精髓及當代意識,挖掘中國特色的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當代生活狀態,創造出觀眾樂于接受的作品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國夢”與中國電影
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中國夢”“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念”“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中國夢的宣傳和闡釋,要與中國當代價值觀念緊密結合起來”“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②以來,“中國夢”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起社會各界的深入探討,綜合相關研究成果,“中國夢”的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和社會和諧;當代中國價值觀就是體現中國現時代精神價值、充分展現中國國家形象和反映中國國家軟實力靈魂的價值觀體系,包含中國優秀傳統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中國夢”等體現時代精神的價值觀等內容。2017 年的十九大報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科學的行動指南和強大的精神力量。
符號學家麥茨認為電影的實質就是滿足觀眾的欲望,電影與夢共有的退行狀態是電影機制與夢機制的相似性,同時電影與夢之間因其感知態度、感知形式和感知內容的不同,電影又被稱作“醒著的白日夢”。我們在觀看故事的時候能夠得到現實匱乏缺憾的想象性滿足,電影院總是把人們導向與現實世界相隔絕的精神世界甚至無意識領域的漫游之中,使觀眾不自覺地接受意識形態詢喚,想象性地化解現實矛盾,渾然忘卻現實困境,獲得解脫升華。中國電影要為實現中國夢做出貢獻,需要為“白日夢”的快樂原則注入更多積極的價值,提升電影的思想、人文和美學品味,使中國電影在白日夢幻想象里有更多對國家、現實、社會和人性的積極思考,把個人的夢想與國家的富強夢、社會的進步夢結合在一起,電影院才不只是一個讓觀眾進入“退行狀態”的黑匣子,才能使觀眾在發泄壓力、釋放欲望后,也獲得在現實世界為理想奮斗的動力和方向感。
電影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想像,是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表達的形式之一,在中國夢的建構工程中承擔著非常重要的使命。任何一部電影,都應該是特定時代、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的表征和反映,同時又反作用于它所產生的時代、民族和文化。正如福柯說:“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現實的意識形態需要是某部作品產生的直接根據。中國電影和中國百年的社會歷程相伴相隨,電影是“中國夢”的表征,“中國夢”是電影的靈魂和綱領,是民族復興的召喚。
二、電影傳播“中國夢”的困境
無論作為藝術形式,還是文化形式,電影都反應特定時代的國家民族、種族地域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而表現特有的文化價值觀念,觀眾通過認同銀幕上的人物和故事,進入創作者所營造的視覺幻象中,喚起他們的心理認同和情感共鳴,影響和制約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選擇。“中國夢”電影是承載著中華民族靈魂的文化身份標識,映射整個民族的集體記憶與精神訴求,肩負傳播中國人思想靈魂與對美好生活追求之夢的使命。倡導電影的“中國夢”,應該超越票房和市場,關注如何讓電影影響世人的價值觀念及精神欲望的滿足。
但當前電影市場環境中,電影傳播“中國夢”的過程存在諸多問題干擾甚至阻礙了“中國夢”的營造,一些主流電影與青年受眾之間存在諸多對接上的問題、矛盾和障礙;電影敘事上遠離現實,故作玄虛,類型模式情結偏重。與之相應的便是大片并沒有留下和他的轟動效應相匹配的精神遺產,集體遠離現實,大多局限在武俠、歷史、玄幻、神怪等類型,創作者少有意識從文化高度上討論當代話題,更多的是在搶占市場,對商業利益的追求導致對于承擔道德立場的摒棄,忽視思想情感力量,缺乏精神探索和人文價值,缺少思想質地和社會意象;電影作為精神產品是夢幻,但電影的產生絕對要立足于現實,立足現實才能重塑中國電影與當代社會的關系,使受眾與夢幻之間形成一種交融的狀態,觀眾從影像中感受到精神的滿足。另外喜劇電影只有宣泄,缺乏健康的娛樂底線,無論是草根狂歡式,還是“小妞電影”輕喜劇亦或戲仿現代社會文化現象的惡搞古裝喜劇,大多只能依靠一些媚笑搞怪的情節博取觀眾笑聲,這種瞬時娛樂缺少深度,缺乏動人心魄的感染力,成為“心靈冰激凌”式電影,忽視內涵價值、不重人物性格、缺乏深度理想。
所以中國電影需要解決的是在主流意識形態、大眾文化心理需求以及電影敘事三者之間建立互動,使電影在社會心理層面,通過敘事主體與社會現實相聯系,把大眾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引入到敘事文本中,將社會現實與觀眾的期待視野相縫合,使觀眾通過想象的路徑向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完成對個體的意識形態詢喚。在個性心理層面,通過電影的夢幻機制實現個人欲望的想象性滿足,想象性地化解現實生活的矛盾,使觀眾心靈得到撫慰,情感得到升華。
三、以電影敘事建構“中國夢”
如何以電影建構“中國夢”,如何創作與傳播蘊含“中國夢”靈魂的思想藝術觀念及文化意識作品,就要以“中國夢”為綱領,形塑、建構、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國夢”電影的創作和傳播不僅僅是口號性的宣傳,而應該是電影創作的靈魂和綱領,是立足于民族文化與社會傳統上的現代社會理想,是中華民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影像展現。電影創作主體應具備宏觀視野、文化意識、歷史視角、現代審美觀念,深刻認識“中國夢”的思想價值內涵,在文化內涵上弘揚積極向上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融入時代新元素,展現民族新形象,感應社會熱點,創造出受眾喜聞樂見的作品。
1.“中國夢”是人民的夢
“中國夢是基于國家立場的夢而不是個人立場的想象,電影的中國夢,夢的內容不是個人欲望的滿足,而是個人夢想的升華③。”“中國夢”是國家夢,是中華民族的夢,歸根結底還是人民的夢,是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形成的既屬于個體,又屬于集體的夢想。以電影建構“中國夢”的途徑之一便是講好故事,立足現實塑造好普通人的形象,表達普通人的人性現實訴求和理想,在人物塑造上關注個人命運、尊重個性差異、回歸人性原點,創造出立體而豐滿的人物,巧妙地弘揚其中的正能量,踐行“中國夢”是“個人夢”與“集體夢”的統一內核,以觀眾樂于接受的方式來表現中國夢的主題,如此“中國夢”的核心價值才有的放矢。
2.以影像敘事建構“中國夢”
電影并非被動地反映社會,而是參與意識形態的建構,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種,通過主體在鏡式文本中建立起自己與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完成對個體的詢喚。問題在于電影以什么樣的方式傳達意識形態,中國電影曾試圖以其奇觀影像和明星效應來刺激觀眾的視聽感官并意圖達成意識形態企圖,卻忽略了影像敘事才是傳達意識形態最為有效的手段。
法國哲學家保羅力克揭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即從某一方面講,我們的精神世界都是通過敘事來建構的。關于電影敘事的研究表明:“導演作為敘述者和大影像師,其敘事行為建構的‘敘事視角’‘敘事情景’‘感官反應’等成為觀眾身份建構價值認同的主要參照”④。英國后現代敘事學家馬克·柯里認為,人的身份不在人的身內,而是由差別所構成的,通過不同的敘述,“學會從外部,從別的故事,尤其是通過與別的人物融為一體的過程進行自我敘述。這就賦予了一般敘述一種潛能,以告訴我們怎樣看待自己,怎樣利用自己的內在生活,怎樣組織這種內在生活”⑤。對電影生產來講,銀幕上的敘事場景與觀看心理之間形成較強的感官反應場,這直接詢喚了接受者的價值判斷系統,進而影響著大批年輕觀眾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方式,它“決定著可見與不可見,決定著影像之間的關聯性質,決定著影像的可見度與延綿,決定著影像在人的感官系統中投射的面積和深度”⑥,特別是對年輕人的意識及價值判斷系統具有其他藝術形式不可替代的影響作用。
所以“中國夢”的核心思想應借助電影這一強大敘事機制系統,在與觀眾形成的感官反應場中,激起觀眾的情緒反應,當電影敘事機制越發達,敘事能力越強大時,對“中國夢”的傳播就越廣泛深入人心。如:2006 年《東京審判》激起民族熱血吸引大量觀眾;2016 年《湄公河》在對個體生命尊重的基礎上完成愛國主義教育和國家意識宣傳,使愛國主義有了堅實的基礎,彰顯了國家主權和國家能力的提升;2017 年的現象級的全民電影《戰狼2》創造影史記錄,將愛國主義的主流價值和商業電影的類型化創作完美結合,既呼應時代、觀照現實,又尊重市場和觀眾,可以說《戰狼2》是在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社會心理之間形成了共鳴,片中的陽剛之氣代表著主流意識形態,代表著主旋律電影應該承載的社會責任和意義表達。影片的出色之處便是敘事上尊重藝術規律,人物塑造有現實的質感,借助個人英雄來暗示國家愛護人民的意圖,將個體聚合的人民意愿和國家集聚的人民信任合為中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將個人欲望的自我想象與國家意識形態的集體想象縫合在同一個電影的敘事本文中。這些個案表明,觀眾對國家認同、社會認同的需求以及國家和民族自豪感一直都存在,關鍵在于要有宣泄口,有認同渠道,中國人心靈深處蘊藏著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正氣,這些精神內涵承載于、散落于數千年的歷史中,在適當時間以適當方式加以挖掘,主流意識形態電影完全可以被觀眾主動接受并認可。
3.民族文化意識滲透
視聽一體化的電影是一個藝術化的“擬態環境”,是世界認識了解和評價中國的窗口,是具有文化標識的藝術,中國電影就是要展示中國特色和民族文化以提升軟實力。當今銀幕世界風從西方來,確切說是好萊塢的文化霸權,所以好萊塢的趣味和風尚成了我們的趣味和風尚。即便是有限的在國際影壇上獲獎的中國電影也很難進入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主流院線放映。但越是如此,中國電影越需要有恒定心,“無論怎樣追隨世界潮流,都不可丟棄自己文化傳統的核心部分以及文化細節,這樣才能具有文化的辨識度和特色顯現而得到尊重”⑦。“中國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結于《周易大傳》的兩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中⑧。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就中國電影而言,從起步階段就注重向傳統民族文化中探勝求寶,誕生之日就和傳統藝術緊密相連如《定軍山》;受中國民族傳統文化浸染的早期電影編導,很自然地把中國傳統文藝的經驗技巧有機地融合在電影創作中,使影片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民族文化本土特色:從鄭正秋沿襲下來到蔡楚生、費穆、鄭君里,謝鐵驪、謝晉、吳怡弓、吳天明,胡炳留、張藝謀、陳凱歌等,都十分注重從中國文學藝術中汲取營養,注重形神關系、虛實把握和意境營造,追求寫意風格,使得影片具有濃郁的中國東方神韻和民族風情。
中國電影民族化的生物基因和文化積淀相互滲透,要電影融入文化意識,首先要強調民族化特色,不應用低俗和噱頭將觀眾拉近影院,而應該用民族文化的自身魅力征服觀眾,用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來回應一統化并立足于世界藝術之林;其次,中國特色和民族文化的展示應該與現代化相銜接,并實現與現代生活、未來發展有機結合,李少白先生在1980 年代論述中國電影民族化時便指出“民族化和現代是同步的”⑨。最后,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傳統文化內核縫合于電影中,提升內涵價值和文化根基。
“中國夢”作為中國電影的靈魂和綱領,引導著中國電影的影像實踐,中國電影不僅可以映射和表達“中國夢”,也參與著“中國夢”的營造,中國電影需要意識到影像敘事是傳達意識形態最為有效的手段,通過大影像師的敘事行為為觀眾建構身份價值認同體系,在社會層面完成對個體的意識形態詢喚,在個性心理層面實現個人現實匱乏的想象性滿足,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傳統民族文化意識內核縫合于電影中,為影視注入更多文化含量、更明確和更積極的價值觀,這樣才能使電影真正成為邁向民族復興之路的文化符號。
注釋:
①張頤武:《“中國夢”: 想像和建構新的認同—再思六十年中國電影》,《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第9 期。
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同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國外文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1 頁。
③陳犀禾,劉吉元:《中國夢和當下中國電影創作》,《電影藝術》2017 第2 期。
④曲春景:《導演的敘事行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權》,《探索與爭鳴》2015 第2 期。
⑤[英]馬克·柯里著,寧一中譯:《后現代敘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24 頁。
⑥李洋:《電影的政治詩學——雅克朗西埃電影美學評述》,《文藝研究》2012 第6 期。
⑦朱大可:《走出中國電影的文化瓶頸》,《電影藝術》2014 年第3 期。
⑧張岱年:《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張岱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397 頁。
⑨李少白:《電影民族化再認識》,《電影藝術》1989 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