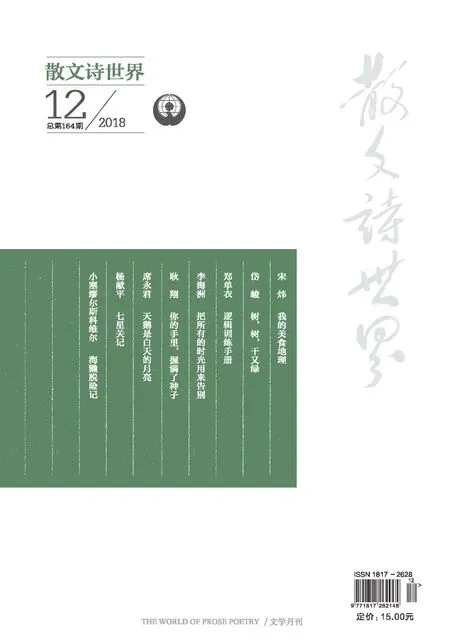青葙 外二章
2018-11-21 06:01:33趙華偉
散文詩世界 2018年12期
趙華偉
于秋的田野上,燃起一團團橘紅的火,時光的一個轉身,將大自然的賜予,風霜、雨露和陽光,轉化成了最濃烈的顏色。在鄉下,青葙的俗名更接近于土地,叫“昆侖草”或“雞冠菜”,若假之以靈巧的雙手,則會變成一道度季的佳食。
透過那重火焰,我曾看到一座幻城:人們徘徊其間,放棄思索、收緊雙足,以等價交換的形式,贏得錦衣玉食或一夜安眠。母親說,逾是遠離,愈是想念,我終究成了一個撞鐘的人,哪怕最結實的白花藤,也未能纏住我驚奇的步子。
《本草》記載,青葙可治夜盲、眼翳,更多時候,卻是為思鄉的人還魂。
曠野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薄霧,在褐色的山頂緩緩鋪開;有飛鳥穿過,羽翼上還殘留著昨夜的星輝;天空俯下身子,讓每一個渺小的崇拜者,親吻他的面頰,隨后,靜待日出,猶如一個心懷慈悲、手握權杖的人。
樹林下的枯葉,在往復之中重生:或是化作一截炊煙,洗去村莊累積的薄涼,或是零落成泥,為一顆種子續寫欣欣向榮的身世。喘息中的蒲公英,用盡力氣,送給所有的孩子一個飽滿的前程。北風在奔跑,以最干凈的身子……此刻,我們應該向一只秋天的螞蟻致敬。
冬天的曠野并非乏善可陳,短暫的沉寂過后,便會綻放一個最清白的開始。
墳園
墳園的盡頭,挺立著一棵柏樹。它是強者的象征,忠實地守護著光禿禿的墳頭,與眾多默然的逝者相比,它蒼老的枝杈上,掛滿了歲月的述說。他們曾跋涉,他們曾為夜色中的燈火而跋涉……他們最終回到童年的土地上,并將之還原為一處安身立命之所。
我們從不畏懼墳塋,親近的人會一直親近,在天寒地凍的臘月天里,尋找著墜落的柏殼。聞香識季節,一旦柏殼燃起,冬天便會以誠相見。植物學家說,柏樹最真實,決不隱藏自己的牙齒,故以“裸子”為名。當寒風乍起時,我對此深信不疑。
即使鄉村生長迅速,墳園也足夠寬廣,最多擠一擠,便能容下所有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