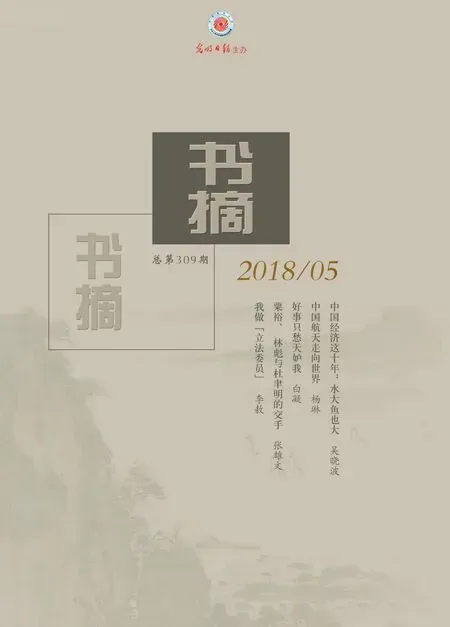《宣和畫譜》與文人畫
☉[美]卜壽珊 著 皮佳佳 譯
《宣和畫譜》是北宋末年的皇家收藏目錄。北宋末年出現了中國繪畫史上的兩大重要發展。一個是蘇軾文人圈影響下出現的文人繪畫藝術。第二個是在12世紀早期徽宗朝的畫院改革。在后來的藝術理論發展中,宋代畫院與文人繪畫風格看起來比較對立,代表了在于藝術上不同的探索方向。從寬泛的歷史觀點看,這兩種藝術發展都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認為它們都是藝術,而不是手藝。對這些由蘇軾領導的早期保守派,盡管徽宗對他們的政治政策比較搖擺,但卻把他們的藝術觀點引入到畫院繪畫的實踐中。
11世紀晚期,因為蘇軾文人圈的影響,繪畫開始進行文人式的探索。又經過一代后,徽宗對繪畫產生極大興趣,并提高了宮廷畫家的地位。在唐翰林院,士人與書法家、畫家和工匠這些群體區分開來。在宋代開端,分別建立了翰林御書院和翰林圖畫院,在真宗時期(998—1022在位),有的宮廷畫家得以身著紫袍,但職位遠低于舉人。在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7),書畫院的成員們獲得“佩魚”的榮耀。他們獲得部分官員待遇,領取俸值,免除體罰,須由皇帝裁定才能免職。在所有的藝術機構里,御書院成員擁有最高的職級,圖畫院成員居第二位。宮廷畫家不僅獲得官員待遇,他們的考試也仿照國子監。黃庭堅說過,繪畫和文學的創作原理基本一致,這個理論被用到了實踐中。院畫家應試時,他們要用圖畫來描述一句詩,以此來表現他們的聰明才智,就像學子們參加科舉表現出寫作能力一樣。院畫家也需要學習文學作品,先是學習早期辭書和道家經典。簡單來說,宮廷畫家基本得到了官員般的特權,他們的教育雖然受到一點限制,但也包含了文學的學習。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院畫家的地位已經接近士大夫。我們知道有兩位士人藝術家在徽宗朝任職,就是米芾和宋子房,他們的地位是院畫家不能比的。
藝術家的社會地位反映在當時的繪畫史中。在《圖畫見聞志》的宋代部分,郭若虛按從上到下的地位分別排出了宋仁宗(1022—1063在位)、十三位王公貴族和士大夫,還有兩位隱士,其他人包括院畫家,一起歸入專事繪畫的行列。在1070年徽宗改革之前,郭若虛應該就已經在寫這本書,但是到了1167年,他的繼任者鄧椿依然認為這樣的劃分是恰當的。在《畫繼》中,鄧椿分門別類列出了一位皇帝、十三位王公貴族、十七位高官、六位高人隱士,四十六位低級官員和縉紳、二十二位道士僧侶、十九位士大夫后裔家眷和宦官。最后剩下九十七位歸入專事繪畫一類,院畫家也包括其中。同樣的社會階層劃分也出現在吳太素的《松齋梅譜》中,這是元代一本從文人觀點出發的梅花畫法手冊。這些事實表明了兩點:第一點,在11及12世紀,藝術家的地位受到關注,可能因為更多地位高的人重視繪畫。第二點,在評論家眼里,院畫家沒有官員地位,不過是專職繪畫者。
在《宣和畫譜》里也出現了同樣的社會階層意識。《宣和畫譜》是北宋末年徽宗的繪畫收藏目錄。一般認為此書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編纂的,但也許是在聲名狼藉的宰相蔡京(1047—1126)和他的弟弟蔡卞(1054—1112)直接指導下完成的。實際編纂者應該是一群士大夫,他們依據早期的資料對畫家進行討論。由蘇軾文人圈形成的觀點偶然添加到文本中,并經常出現在后代藝術家的傳記中,因為這些傳記并沒有現成的資料。《宣和畫譜》沒有列出社會類別,只是區分出皇親國戚、高級文武官員和隱士。最后面再分為三類,文臣、武臣和內臣,院畫家沒有特別列入一類。編纂者用蘇軾的觀點作參照,給了士大夫最高的尊重。文人畫被看作在閑暇時所作,是文學技巧的流溢,表達了無功利的瞬間靈感。有趣的是,對皇親國戚最高的贊揚,也是按照士大夫的標準。比如,這樣描述宋太宗的曾孫趙仲佺:
不沉酣于綺紈犬馬,而一意于文詞翰墨間,至于寫難狀之景,則寄興于丹青,故其中畫中有詩。至其作草木禽鳥,皆詩人之思致也,非畫史極巧力之所能到。
皇室宗親的地位當然比士大夫高,但宋代文人是以聰明才智來體現價值,而不是世襲爵位。黃庭堅贊揚趙令穰對藝術的貢獻,不過也提示,趙令穰應該多讀書,以便使自己的風格更加完美。《宣和畫譜》體現出前一代文人所表述的文化價值觀。
詩與畫的比較,還有以文學天賦入畫的能力,這樣的語句經常出現在文本里。甚至在蔬果類的畫家篇章里,也有這樣的論述:
詩人多識草木蟲魚之性,而畫者其所以豪奪造化,思入妙微,亦詩人之作也。
上面的典故來自孔子的《論語》,孔子建議弟子們多學《詩經》,因為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通過這種關聯,蔬果被認可為繪畫題材。這些段落看起來干癟,學究氣重,不如蘇軾和朋友們的詩歌有趣。更適合在其他地方比較這兩種藝術。李公麟的畫作《陽關》包含了道德寓意,被認為“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于畫”。王維的畫被認為不如他的詩:
觀其思致高遠,初未見于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意,由是知維之畫出于天性,不必以畫拘,蓋生而知之者。
王維的聲望當然不能從他的繪畫來判別——也許對宋代編纂者來說,他的繪畫過于簡單——不過他創制詩歌意象的方式是圖畫式的。
偶爾,當一個畫家與文學世界相聯系時,他被認為在作品中表達了思想和靈感。羅隱(833—909)的兒子羅塞翁轉向了繪畫,《宣和畫譜》以這樣的方式為他的選擇辯護:
隱以詩名于時,而塞翁獨寓意丹青,亦詞人墨客之所致思。
如《宣和畫譜》這樣評論蘇軾的朋友文同,認為他自然而然接近了藝術:
凡于翰墨之間,托物寓意,則見于水墨之戲。
同樣,南唐后主詩人李煜(卒于978)“政事之暇,寓意于丹青”。在這種聯系中,“寓意”,就是“在某事物上寄托自己的思緒”,這個詞描述了一種副業,指業余畫家在閑暇時揮灑藝術,也有一種抒發情感的含義,因為這是為了娛樂。“寄心”也意為“寄托人的心靈”,是含義相近的詞語。經常會出現一對意思相近的術語,“寓興”或“寄興”,就是在繪畫上“寄托興發的情感”。“興”是藝術家受到激發,于是產生靈感,是引導一名業余畫家創作的藝術沖動。仁宗的駙馬李瑋以這樣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繪畫:
時時寓(遇)興則寫,興闌輒棄去。
高居翰追蹤“興”的文學起源,一般來說可以定性為加強的反響。他也指出,寓意或寓興表現了理學對于宋代文人藝術理論的影響,因為它們強調從外物和自身感受中提取的價值。然而,這些哲學意味并不總是存在。藝術確實可以看作一種抒發途徑,高士們用來抒發情感以保持合乎正道的平衡。但在《宣和畫譜》中,“氣”和“韻”常常只是簡單描述一個人在閑暇時的當下行為,也就是一種業余的藝術。這些術語無一例外都用于達官貴人或文人隱士的畫作。院畫家和專業畫家被排除在外。而且,幾乎所有藝術家的作品都被拿來與詩相比,以顯示他們是貴族顯要、士大夫和文學之士。
在早期畫家王維和李成的兩個故事里,可以看到這種勢利的社會現象。王維在一首詩里稱自己“前身應畫師”,可以對照閻立本被稱為“畫師”的憤怒。《宣和畫譜》的編纂者暗示,王維能夠寫下這句名詩,因為他對自己的詩名很自信,但是閻立本只擅長繪畫,被賦予這個稱號就不可能感到安心。第二個故事關于李成的卓然不屈,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盡管李成生活不太如意,他依然聲稱只是為自己作畫,就像高士一樣。據說在給一位固執的收藏家孫氏的信中,李成強調了自己的獨立地位:
自古四民不相雜處。吾本儒生,雖游心藝事,然適意而已。奈何使人羈致入戚里賓館,研吮丹粉,而與畫史冗人同列乎,此戴逵之所以碎琴也。
在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里,李成就是那兩位高人逸士之一。從信的內容我們可以判斷,如果一個人只是畫家,那么他的地位就很低。院畫家除去他們的特權,很有可能也屬于這一類。
相較院畫家,士大夫具有較高聲望,這也進一步說明文人藝術對皇家宗室的影響。兩位皇室成員王詵和趙令穰都是知名的文士藝術家,徽宗自己也以文人的方式畫花鳥。趙令穰的小山叢竹據說從蘇軾那里學得,趙令庇的墨竹就受到文同的影響,趙令晙畫馬以李公麟的畫作為模板。我們也知道,徽宗在他的畫上題款和題詩,就像自己是一位文人。在形成自己的顯著風格前,徽宗還學習過黃庭堅的書法。然而,文人畫的題材和風格在畫院不受歡迎,在徽宗朝,只有一位院畫家專工墨竹。這部分證明士大夫和達官貴人們獨享這種藝術品位。但是在前代大師之作基礎上的山水畫,無論是水墨還是著色,都受到顯貴、文人和院畫家的追捧。徽宗最知名的風格來自院體譜系,它由崔白的花鳥畫派生出來。就是這種華麗精致的藝術培育了北宋院體繪畫。徽宗面臨兩種繪畫方向,他既畫文人風格,也畫院體風格。《宣和畫譜》根據社會地位進行表述,反映出文人藝術家與專業藝術家之間的對立,卻沒有指出兩者在風格上的不同。
在接下來的一個階段,文人繪畫傳統在中國的南北方都逐漸形成,這一時期的藝術理論也有某種程度的發展。但是北宋文人的著作奠定了文人藝術理論的基礎。相較后面的時代,北宋時期涌現出更多高質量的藝術理論著作。一種對藝術心理的新關注點出現了。與早期的評論家不同,蘇軾、黃庭堅和董逌關注畫家對自然的闡釋,認為創作過程至高無上。米芾和米友仁描述了繪畫的“戲”和表達方式,并構建了一種新的文人藝術品位。《宣和畫譜》的編纂者強調,藝術是君子的閑治之事,作為業余興趣愛好來揮灑。文人畫理論的這些方面,將在后來的評論著作中屢次出現,隨著文人藝術傳統的發展,最終將形成一種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