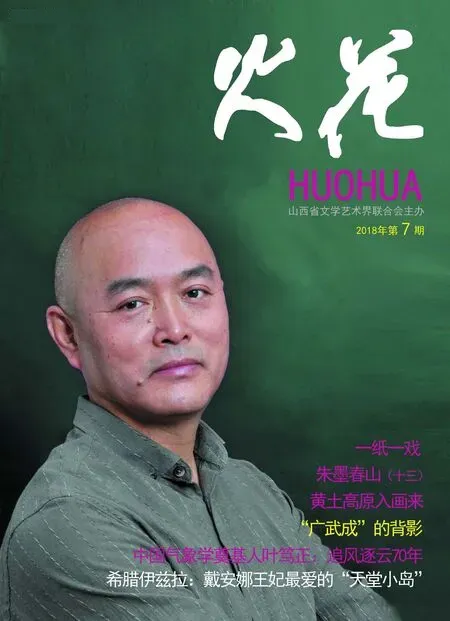故鄉是時間積累成的空間(外一篇)
介子平
中學時代私聽鄧麗君的靡靡之音,一首不知名的歌印象最深,詞曰:“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瑪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古圣和先賢,在這里建家園。風吹雨打中,聳立五千年。”聽鄧麗君的歌,得到的并不是興高采烈、心花怒放,而是停云落月、若有所思。比如她唱蘇軾的《水調歌頭》,聞者無不徘徊瞻顧,茫然退立,蘇軾千年之后,真的覓得了知音。比如《梅花》:“梅花梅花滿天下,越冷它越開花。梅花堅忍象征我們,巍巍的大中華。看啊遍地開了梅花,有土地就有它。冰雪風雨它都不怕,它是我的國花。”威武不屈,我心貞確,點點梅花,苦難中的國民,何以如此鐘情之,我與君,共歲寒,她的歌都回答了出來。金岳霖說:“雅作為一個性質,有點像顏色一樣,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鄧麗君的歌,眾人感受到的是其顏表,絢爛背后實則雅的底里。
后來張明敏唱了首《青海青黃河黃》的歌:“青海青,黃河黃,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浩浩,山蒼蒼,祁連山下好牧場,這里有成群的駿馬,千萬頭牛和羊,馬兒肥牛兒壯,羊兒的毛好似雪花亮。”這首歌詞,押韻和叩,跳躍有致,處處言景,卻處處是情,但歌者不高明,雄壯不足,婉約欠缺。關鍵是沒有唱出民國味,沒有唱出七十年代的風韻。
聽過兩歌之后,便以為青海是個充滿詩意的區域了,至少在民國人眼中。青海不是地之域、詩之域也,這些歌詞寫家,至少在寫作此歌時,從未踏上過這片高原。但這似乎并不重要,范仲淹未至洞庭,作《岳陽樓記》,沈周未登廬山,作《廬山高》,皆遺世經典。
王洛賓創作于民國年間的《在那遙遠的地方》,其發生地也在青海,此歌流傳甚廣,對邊疆的詩意描寫,多受其影響。王洛賓的邊疆也郁郁失樂,忽忽惘然,“美麗小鳥一去無影蹤,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即他的“去年今日此門中”,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人生聚散,信如浮云,庾郎從此愁多。
青海后來我去了,是個好地方。傅雷說:“可嘆學問與心靈往往碰不到一塊——感受與心靈也常常無緣相合。”的確,帶著詩意去找詩意,本身便是一種迂,找到的定是初戀情人在當下的失望。這些花底填詞、香邊制曲的詞家,若果真在苦寒的青海生活過,關注點必然有所變化,寫出的必也是“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青海戍頭空有月,黃沙磧里本無春”“蠻夷長老怨苦寒,昆侖天關凍應折”“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之類的凄句。二手的感受往往是被過濾被遴選的詩意,親身經歷者,則不會搔首對西風。詩人狀物,手法不一,即不一在感受。
席慕容的《出塞曲》,背景換成了內蒙,但思路仍不出王洛賓。后來此詩被譜了曲,蔡琴唱得也好,低沉含蓄,悠悠不竭,尤其是后一段,凄涼感發,柔腸百轉,使人悵惘若失,良久愴然:“而我們總是要一唱再唱,像那草原千里閃著金光,像那風沙呼嘯過大漠,像那黃河岸,陰山旁,英雄騎馬壯,騎馬榮歸故鄉。”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席慕容濃濃的蒙古情結,在古代,不在現在。她曾說:“我覺得在我四十六歲踏上故土以前,這個世界沒有給我一個正確的內蒙古,沒有給我一個完整的、仔細的、正確的內蒙古的草原文化。現在我想要加倍地補回來。”但故鄉是時間積累成的空間,席慕容對原鄉,同那些詞家的感受幾同。沒有時間的積累,空間怎會成故鄉?
后會無期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人一走,山岑水寂,花殘葉落,一派秋感覺。
多數人走后,再沒回來。那些恢廓局量中的欣然之事,成了久久的追憶;那些曼妙風景里的心儀之人,已然遲遲的回味。所有的再見,或有緣無分,機會錯失,或無緣有分,不知所措,皆不出緣起緣滅的注定。最好的時光,是無回的歲月;最重的珍惜,是無言的陪伴。離開的地方不是三疊的陽關,或許就在隔壁,不在折柳的灞橋,或許幾次路經,只因當初那個莫名的期待,踟躕其間,“不愁一去蹤難覓,卻恐重來事轉生”,故地無心游,盡管印了騎縫章的半紙死契你還珍藏。夢去心去,心還夢不還,此處再不會出現意外的驚喜。相見亦無事,不來忽憶君,罷了,罷了,你知他,他不知你。
道路有多長,孤獨就有多久。丹麥畫家哈墨休伊鐘愛畫女子的伶仃背影,顧影感傷,不免凄涼。所有的故事,都會泛黃,所有的青春,即既往。眾生可愛,眾生可憫,“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
而今才道當時錯,曾經以為,看窗外風景的應是兩人。為順從別人,扭曲自己,為討好別人,作踐自己,那就低了。無奈有些人與事,一輩子只此一班車,且無回程票。沒有彩排,不容后悔,待遺憾溢出,惆悵早已滿缸滿甕。總有一些無法再見之人,無法歸來之地,無法竟成之業,無法修復之憾,無法親近之人,無法占有之情。過去的,終究頹喪,現在的,往往不足珍惜。離開方知所謂共同經歷之短暫之易散,語境變,談論的是不相識之人,時空變,穿戴了不熟悉的搭配。“你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但你還是你。你沒辦法從自己身體里面逃離出去。”海明威的話對否?
一人一世界,安詳且孤獨。歲月不光寫在素顏修行的臉上,還漸變了你一成不變的習慣。盡人事,一念放下,聽天命,萬般自在,大靜于身者,黃花人瘦,大靜于心者,人淡如菊。越老越靜,靜若止水,起初可都不是這個樣子。顧城說:“在我放棄了自己的時候,我忽然就自由了,我終于理解了什么叫自然而然。”
生命是將喧囂調成靜音的過程,松間明月,石上清泉,耳邊具琴筑,只向是非聾。孫犁曾言:“余至晚年,極不愿回首往事,亦不愿再見悲慘、丑惡,自傷心神。然每遇人間美好、善良,雖屬邂逅之情誼,無心之施與,亦追求留戀,念念不忘,以自慰藉。彩云現于雨后,皎月露于云端。賞心悅目,在一瞬間。于余實為難逢之境,不敢以虛幻視之。”辛苦鄉關路,重來斷客魂,難逢之境,后會無期,收攤掃尾未見,至老何曾等來。“勇敢點,別擔心。反正我們誰也別想活著離開這個世界。”朱德庸之戲言不戲,坦言矣。
天近黃昏,恍然有悟,天命便是一生的期待,而本就無法實現。一片蛙聲傳遠渡,你能聽見,卻過不去。曾記昔年登眺處,夕陽紅樹正清秋,流年的不盡之意,不經歷不往心里記。
小草猶開秋后之花,種子落在地上,是秋天最后的伏筆。舊的結束,不也是新的開端?季節循環,故事也往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