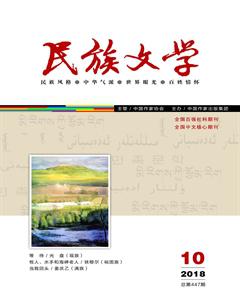遠(yuǎn)去的沃土
譚成舉
我是農(nóng)家出身,曾經(jīng)是有過土地的。三塊,都不大,小者兩個(gè)平方,大者兩畝。可惜如今它們都離我遠(yuǎn)去,我只能在記憶中、睡夢中去翻耕、播種,并快樂地收獲了。
——題記
童年的沃土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的谷雨過后吧,那時(shí)我六歲,未上學(xué),農(nóng)村自然也無幼兒園可上,瞧見生產(chǎn)隊(duì)安排全隊(duì)的婦女去田邊地腳打窩種南瓜,我在看守好為生產(chǎn)隊(duì)代養(yǎng)的豬牛的同時(shí),便跟了去,小心地從婦女隊(duì)長分發(fā)給母親的瓜種中偷偷摸下幾顆瓜子“也傍桑陰學(xué)種瓜”來。
無疑,種瓜是偷偷進(jìn)行的。那時(shí),一切作物都是禁止農(nóng)戶私自栽種的,否則就是資本主義。私自栽種的瓜豆等物,是資本主義的尾巴,那是要被割掉的。所以,我之種瓜必須秘密進(jìn)行。如若被他人知曉,告到生產(chǎn)隊(duì),不僅瓜要被鏟除,家里大人還要被戴高帽、受批斗,另外還要遭處罰、扣口糧。所以,生產(chǎn)隊(duì)不準(zhǔn)種,家人也是不準(zhǔn)種的。
而我卻偏偏還要去偷著種。一是好奇心使然。那時(shí)不僅物質(zhì)生活匱乏,精神享受也幾近為零,小孩子除了能找同伴打打鬧鬧外,什么娛樂都沒有,看到大人種瓜,這無疑具有巨大的誘惑,自然心癢難耐。再說,好奇和模仿也是小孩子的天性。二是饑餓所致。生產(chǎn)隊(duì)每月分的那點(diǎn)口糧遠(yuǎn)遠(yuǎn)不夠吃,大人小孩每天都餓兮兮的,其滋味實(shí)在是不好受,若能種得瓜來,瓜葉可以吃,瓜花可以吃,南瓜無論是切片炒著吃還是切砣煮著吃,都是難得的充饑佳品。就是將瓜切碎了,摻幾瓢水,煮成稀稀浪浪的南瓜湯,也是聊抑饑餓的。你說我能對(duì)種瓜不急切、不心動(dòng)嗎?
六歲的孩子本該懵懂,然而,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卻催生了我的早熟。既然是偷著種瓜,就要在“偷”字上狠下一番功夫——不能讓人發(fā)現(xiàn),至少要不能讓人抓住把柄,否則,割起資本主義尾巴來,實(shí)在是讓一家人受不了的。當(dāng)然,這種瓜之舉是連家人也不能讓其知曉的。于是,我便將瓜地選在了離家一里之遙的地方,而且是一個(gè)巖氹氹中間,那地兩米見方,四周有刺圍遮,很難讓人發(fā)現(xiàn),即便發(fā)現(xiàn)了,若非抓到現(xiàn)行,根本找不到是誰種的。這就是我那時(shí)的小聰明。
整地選擇在大人都出工,別的孩子或上學(xué),或被大人帶去工地了,而我將為生產(chǎn)隊(duì)代養(yǎng)的豬牛趕上山并割滿一挑牛草之后。工具不敢用大人常用的鋤頭,怕被發(fā)現(xiàn)遭追問,再者人小力薄也拿不動(dòng),只能選擇大人一年用不上幾次的小鎬鋤,輕巧,在那巖氹氹翻耕也實(shí)用,用后擦干凈,往門角角一放,誰會(huì)注意?地,我整得很細(xì)致。先將地翻過來,挖泡、整細(xì);再將草根、樹棍、碎石之流撿拾干凈;其后打窩,鋪底肥。地窄,我只在四角各打了一個(gè)窩。鋪底肥,原本最好的是發(fā)酵過的豬水糞,可我挑不了,人還沒得糞桶高呢,也沒那么大的力氣挑,再者目標(biāo)大,害怕被發(fā)現(xiàn),我只得改用牛圈里的牛糞——牛糞是固體的,分幾次少少地往地里運(yùn),目標(biāo)小,不費(fèi)力。牛糞運(yùn)走后,留下的坑氹鋪點(diǎn)草,把牛往里一關(guān),一踩,幾腳就踩沒了痕跡,誰也發(fā)現(xiàn)不了異樣。鋪完底肥,還要在上面蓋一層不薄的細(xì)土,如若直接將種子下在底肥上,底肥一發(fā)酵,產(chǎn)生高溫,是要燒壞種子的。下完種子后,還要用細(xì)土將種子蓋住,上下接地氣,種子才能發(fā)芽。
從翻地到下種,我足足用了四天。這幾天,苦和累自不需說,搞得我十分疲憊,每每吃完晚飯就睡,再不像往昔與同伴們瘋癲個(gè)沒完,不到午夜不歸家,以致父母以為我身體出現(xiàn)了問題,嚇得問這問那的。我卻喜悅,卻滿足。白天老是滿臉掛笑,夜晚睡覺都笑醒幾次。
也是天公作美,下完種這天,晚上飄起了細(xì)雨,這無疑為我的瓜子變?yōu)楣厦缙鹆舜呋饔谩5诙瘴彝低蹬苋赋龉献觼砜矗鼈兊募庾焐暇挂验_裂,探出了細(xì)細(xì)的、白白的、彎彎的萌芽。
我自然喜不自禁。自此我全身充滿了活力,辦事也格外有動(dòng)力,眼光看什么都一片喜色。
幾天后,芽苗就冒出了土,先是白尖,再是兩豆瓣樣的嫩葉,再是葉片的不斷增多,再是長出了藤蔓。
隨著瓜苗的每一次變動(dòng),我的喜悅就增加一份,激動(dòng)就增加一份。我看著那不斷變長的藤蔓,眼前就不由幻化出黃紅黃紅的鮮艷的瓜花,還有瓜花底部不斷長大的南瓜,進(jìn)而聞到了瓜花的味道、南瓜的味道,直讓我饑餓的肚子咕咕造反,誘發(fā)出口水忍不住地長流。其間,我寶貝樣呵護(hù)著“我的”瓜地我的瓜,除草、松土,噴水,幾乎每天都要來一次,盡管那土是松的,草可以說看不到一星半點(diǎn),可我仍然要將不多的“業(yè)余”精力全部投放在那兩個(gè)平方的希望之上。
然而,好景不長。正在我信心滿滿、自我心醉地憧憬著如何烹食我的南瓜時(shí),一個(gè)星期天的早晨,從“我的”瓜地旁傳來了嘈雜的人聲。那時(shí)我正在為家人做著早餐——熬制苞谷糊糊。聽到聲音,我心頭猛地一顫,感覺一定出事了,這也正是我在希望和喜悅中最擔(dān)心發(fā)生的事情。我急忙將火熄滅,來不及關(guān)上灶屋的門就匆匆往出事的地點(diǎn)趕,這時(shí)也見出早工回來的大人們陸續(xù)向那里集結(jié)。
果然就是“我的”瓜地出了事。
我從那嘈雜的聲音中知道了原委。原來,一個(gè)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因早上餓極了,便出門找三月泡充饑。找到“我的”瓜地旁,正巧有一棵三月泡樹,盡管上面的果實(shí)還是青色,遠(yuǎn)遠(yuǎn)不到采食的時(shí)候,可饑餓難耐的他管不了那么多,統(tǒng)統(tǒng)對(duì)它們一掃而光。還不夠,他又去周圍細(xì)細(xì)尋找,這就發(fā)現(xiàn)了“我的”瓜地,這就叫嚷起來,引來了生產(chǎn)隊(duì)長和他的不少“臣民”。
隊(duì)長大發(fā)脾氣,說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這資本主義的尾巴必須得割,這樣的行為必須嚴(yán)懲……
接著,自然是展開調(diào)查。那時(shí)隊(duì)長沒有“破案”的技術(shù)手段,也沒有有效的“破案”方法,靠的是淫威和敷哄嚇詐。但是,那事的后果誰都知道,又有誰敢承認(rèn)那是自己搞的“資本主義”?更何況那本身就不是他們的“杰作”。隊(duì)長就把目光刺向了歷來老實(shí)懦弱的父母,說我們家離這瓜地最近,不是我們家種的還是誰種的?想不到這次父母沒有懦弱——大概也是想到了“資本主義”這頂帽子不好戴,后果我們家也無力承擔(dān)——幸喜我也絲毫沒有向他們泄露我的種瓜秘密——他們這次竟破天荒地頂撞這隊(duì)長,死不承認(rèn)。找不到證據(jù),隊(duì)長也沒法,卻又放不下臉面,便強(qiáng)行要我的父母將那四蔸南瓜秧扯掉,將地刨平,還壓上幾塊大石頭。
當(dāng)時(shí),我的心情是無法形容的。我強(qiáng)忍著在眼眶中打轉(zhuǎn)的淚水,悄悄地溜回了家。
其后,隊(duì)長還多次來查看那塊地以及別的地方是否有人栽種,是否還有人敢“復(fù)辟資本主義”。
至此,那塊沃土夭折,成了我一世的記憶一世的痛!
第二年春上,我搬開石頭,偷偷在那塊地里種上一棵小小的巖桑樹,后又將那些石頭壓在樹的周圍,造成樹是自然生長出來的假象,這才再?zèng)]人發(fā)現(xiàn)。這樹后來茁壯成長,每至初夏,都結(jié)滿桑葚,飽了我等的口福,飽了鳥雀的口福,成了我不滅的念想,成了我心中永遠(yuǎn)的風(fēng)景。
我的土地我的情
實(shí)行農(nóng)村土地承包責(zé)任制后,我們家有了自己的土地,我們成了土地的主人。那種喜悅真是無法言表,總感覺在那土地上勞作時(shí)有使不完的勁,就是在那土地上站一站,也感到溫馨,感到踏實(shí),感到再也不會(huì)有饑餓的降臨。我每每從學(xué)校回歸,都是要去土地一趟的,或耕作,或看看土地上的莊稼,或感受土地的滋味。那不是父母的強(qiáng)迫,而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自覺。
一九八三年,二哥成了家,于是,父親便讓我們?nèi)苄址旨伊簦?dāng)然土地也分成了三份,其中就有我的一份。兩畝。
那時(shí),我正在縣師范讀二年級(jí),還有一年就要走出校門參加工作了,原本我是不打算要分給我的那份土地的,我不知道我將來會(huì)去哪里工作,但我知道我工作后是肯定沒有時(shí)間好好伺候土地的。我既然無法正經(jīng)地去親近土地,我就不能荒廢了它,愧對(duì)了它,否則,那會(huì)成為我新的痛,我會(huì)感到我的無恥,我會(huì)在世人面前抬不起頭。但父親不依,他有他的思維,他有他的考慮。他說,你今后無論在哪里工作,你是農(nóng)村出去的,你就永遠(yuǎn)是農(nóng)村人。農(nóng)村人怎么能沒有土地呢?你將來就是沒時(shí)間回來種它,還有我們種,你還要找媳婦,還有媳婦要種,再說,你今后萬一什么都沒得了,你還有土地!你要老,你要退休,你還得回到農(nóng)村,你還得種你的土地。我拗不過父親,只得勉強(qiáng)接受了,但我真的沒時(shí)間正正經(jīng)經(jīng)去侍弄土地,我只得將我的土地交給父母。父母爽快地接過了土地,但父親卻說,你記住,這土地是你的,我們只是暫時(shí)代你耕種,今后你還得自己來種。
一九八五年,我?guī)煼懂厴I(yè)后,分回了我老家的學(xué)校任教,老家學(xué)校教師少,除了數(shù)學(xué)課外,我任教那個(gè)班的其他課我全包,還要當(dāng)班主任,我哪有時(shí)間回去正經(jīng)地伺候土地?
第一個(gè)周末我回家休息,自然要去親近我那份土地。我那份土地被父母他們種上了苞谷。此時(shí)苞谷正蔫須脹砣,那個(gè)大籽滿的苞谷砣,散發(fā)著誘人的清香,讓我從教學(xué)的疲勞中一下子解脫出來,瞬時(shí)感到神清氣爽。我不禁閉上眼睛,深深長吸了幾口氣,深切心肺地感受一下苞谷的溫馨和土地的恩惠,感受父母的辛勞付出和他們對(duì)土地的深愛。
見此,陪我同來的父親笑著說,朗門樣?
我不假思索地說,那當(dāng)然,您侍弄的土地那還有說!
父親深情地說,土地是個(gè)好東西啊!土地有情,你對(duì)它好,它就使力地回報(bào)你!
我也深有感觸地說,人有情,土地自然也有情啊!
父親看了看我,嚴(yán)肅地說,這回你感受到有土地的好了吧?
我說,自然,有土地什么時(shí)候都好!
父親又說,你也分回來了,學(xué)校離家也不算遠(yuǎn),這地,我還得交回給你種。
我聽父親這么說,一下子急了,說,除了周末,我哪有時(shí)間來種地?
父親沉著臉說,那我不管。
我說,你不管哪個(gè)管?當(dāng)初分我地時(shí),我說不要,你偏要給我!
父親說,你剛才不是還說有地好么?
我說,有地是好,可那也得有時(shí)間種啊!沒時(shí)間種,讓地荒廢了,那是心中愧得慌的事啊!
父親想了想說,這個(gè)道理我自然懂。可是,我不能總種著你的地呀。我們也老了,種不動(dòng)地了,也怕愧對(duì)土地呀!這樣吧,我給你找個(gè)人來種,好不好?
我嘆口氣說,那也只得這樣了。不過,別隨便找人,把地種壞了。你得找個(gè)種地的好手,那才對(duì)得住那地。錢我來出。
父親不再說什么,只是滿臉的笑。那笑,在我看來,既有滿足,又有狡黠。我不知道向來老實(shí)的他為什么有這樣的笑。
而我,則只剩下滿心的苦笑了。
第二個(gè)周末,我又回到我的土地上,我撫摸著不斷走向成熟的苞谷砣,心中說不出的滋潤。
這時(shí),原本去趕場賣雞蛋的父親匆匆趕了來,要我趕緊回去,說是幫我種地的人找到了,并且來到了家里,要我趕快去見面。
我自然心中一喜。
母親正在刷鍋?zhàn)鲲垼瑵M臉喜慶。堂屋里坐著一老一少兩個(gè)女人,正在交談著什么。老者我認(rèn)得,是我的舅娘;少者我卻不識(shí),只是覺得與我年紀(jì)相仿,有些嬌小,但長得蠻清秀,很入眼。我卻不知她們倆與我要找的“種地的”有什么關(guān)系。舅娘自己有一大家人,她是家里的頂梁柱,自家的地她都耕種不過來,哪還有精力來幫忙種我的地?那個(gè)年輕的女孩長得細(xì)皮嫩肉的,又那么小小個(gè)的,也不是種地的料呀?
我正疑惑,想問問父親怎么回事,舅娘卻眼尖,發(fā)現(xiàn)了我,我只得急忙走過去給她們打招呼。那女孩羞澀地站起來,對(duì)我點(diǎn)點(diǎn)頭不做聲,只低垂著眼瞼紅著臉看著自己的腳尖微微地笑。舅娘也站起來,笑著向我介紹那女孩,說她是我某某姨娘家的表姐,大我?guī)讉€(gè)月,現(xiàn)在在學(xué)裁縫,是應(yīng)我父親之請(qǐng)找的幫我種地的。
聽完舅娘的介紹,表姐輕輕地叫我一聲“表弟”,便抿著嘴,搓著手,不知所措了。我也一下子不知說什么好,腦中瞬間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是怎么逃離她們的。
我找到父親,他正在灶屋幫做飯的母親燒火。他正與母親商量著什么,他們倆都一臉的喜不自禁。見我走來,便問我,人,你也見了,朗門樣?
我低著聲音板著臉沒好氣地說,您上次說,是給我找一個(gè)幫忙種地的,這次您卻讓舅娘幫我找來個(gè)裁縫。裁縫只會(huì)和布打交道,她哪里會(huì)侍弄地?
父親仍喜色不減,說,裁縫朗門了?她就配不上你?
我說,我要您幫我找的是來種地的,這種下力的活,只有男的才耐得活,您找來個(gè)女的,還是個(gè)只會(huì)拿剪刀不會(huì)拿鋤把的,長得也那么單薄,她種得了地?
一直沒說話的母親聽了,忍不住哈哈一笑,忙伸過頭去偷偷瞧舅娘她們一眼,后才低聲對(duì)我說,你個(gè)傻兒!虧你還是教書的!講給你找個(gè)幫忙種地的,你以為就真是種地的了?那是給你找的媳婦呢!
父親也說,對(duì)農(nóng)村人來說,媳婦不就是“種地的”?找到了媳婦不就是找到了“種地的”?
父母這么一說,我一時(shí)懵了。這是什么邏輯,這是什么觀念?!
等舅娘她們吃過飯走后,我與父親大吵起來。大致的意思是,我還年輕,才十八歲,還不想這么早找對(duì)象;我工作還沒穩(wěn)定,端公家碗服公家管,說不定哪天我就調(diào)到別處去了,找個(gè)“半邊戶”在家,我還是沒法回來幫她種地,到時(shí)她身累我心累,難免會(huì)搞得吵吵鬧鬧的,大家都不舒服;再者我和表姐是近親,近親結(jié)婚將來對(duì)子女不利,國家法律也不允許……
我的堅(jiān)決反對(duì),父親也沒得法,這門親自然沒開成,搞得舅娘對(duì)表姐不好交代,很尷尬,以致好久都不理我。而我那表姐,自那一別,她是再也不見我了,就是我母親過世,她也沒到場,只是請(qǐng)她的母親帶了個(gè)“人情”,直到三十年后的一天,她的母親去世,我去吊唁,才再次見到她。這時(shí)的她,已是兒孫滿堂,而當(dāng)年的風(fēng)韻仍然留存。我們只匆匆地打過招呼,沒時(shí)間進(jìn)行交談,我不知道她的景況,其實(shí)我是很想知道的。母親過世的悲戚明顯寫滿她的臉上,而絲毫看不出她對(duì)我的幽怨,這,也許是時(shí)間的磨礪讓她淡忘,也許是閱歷的遞增讓她理解了我當(dāng)年的拒絕吧。
我沒有找到幫我種地的人,父母只得繼續(xù),但父親有言在先,只給我再種一年,一年內(nèi),我必須要自己找一個(gè)滿意的“種地的”。這一年,盡管父親時(shí)常問我找到“種地的”沒有,我也不急,只一味地拖延,一味地應(yīng)付他。正當(dāng)父親下最后的“通牒”時(shí),我被調(diào)離了老家的學(xué)校,我知道我今后回家的時(shí)間就少了,我是再也沒時(shí)間侍弄我的地了。不得已,我將我的土地,還有包括山林、房屋,一應(yīng)分給了我的兩個(gè)哥哥,白白送給他們,不要一分錢的補(bǔ)償。
離開老家的前一天,我特意去了一趟我的土地。地里還是種的苞谷,苞谷比往年長勢更好。我先是站在地邊看,看個(gè)大籽肥的苞谷,看肥沃出種的厚土;再是毫無目的地在地里往復(fù)地慢慢行走,穿梭在那密密的苞谷林間;其后是一屁股坐在地里,雙手捧起泥土慢慢地搓,深情地聞那泥土的氣息。我不由得想起了六歲時(shí)私自開墾的土地,還有那地上長出的瓜蔓……
離開那地時(shí),我沒有流淚,卻滿心傷感,默默地將地在心里記了又記。
汗灑貧瘠地
一九九二年,我成家了,妻子不是種地的,她是我們學(xué)校旁鄉(xiāng)里醫(yī)院的護(hù)士。這似乎有違父親的初衷。我們兩邊家都在農(nóng)村,家里條件都不好,雙方父母又多病,那時(shí)還沒興外出打工,雙方的兄弟姐妹都只得待在家里耕種土地,這就缺錢用,雙方父母一病,就只得往我和妻子這里送。那時(shí)工資不高,我和妻子總計(jì)只有五百多一點(diǎn)。我們的日子就過得很艱難。這就讓我萌生了要找塊地種種的想法,這樣,除購買國家供應(yīng)的糧油以及偶爾去場上買點(diǎn)肉、蛋之類外,在蔬菜方面自種自給,也是可以節(jié)省出不少的錢來的。那時(shí)的人都珍惜地,把地看得像命根子一樣,誰還有多余的地送給我們種?
沒有地,就自己開墾吧。剛好在醫(yī)院的駐地后面有個(gè)打巖場,大致兩分地。土是取巖后留下來的,貧瘠,里面多碎石,而且經(jīng)過拖巖石的車輛的反復(fù)碾壓,變得極其死板。沒有人要,便閑置了,稀稀拉拉長了些芭茅草。我便與妻子商量,把這塊地耕種起來。妻自然同意,貧窮人家走出來的人都能吃苦,也能放得下臉面。
鋤頭和鐮刀是妻從她的老家專門找她的外公、舅舅打制的。她外公和舅舅是她們那一帶有名的鐵匠。給外孫女、外侄女打制的器具就自然格外上心,使用起來自然就耐用、好用。只是沒有鋤把、刀把。妻的娘家在城郊,那里生長稻谷,卻不生長樹木,我只得利用周末徒步三四十里路去老家。老家那時(shí)交通還很不發(fā)達(dá),無公交不說,車路也還沒修到家,回一趟老家是真不容易的。
趁這次回家也正好去看看父母,看看我的曾經(jīng)的土地。
父母見我回來,自然高興,特別是知曉我回來找鋤把、刀把,要開荒種地,更是喜歡得不得了。他馬上就上樓,將樓上炕得干透了的一節(jié)米多長、碗口粗的青樹取下來,用他那多年干木匠活的手藝,斧砍刨削起來。他說,你能重新把土地種起來,好呀!土地是個(gè)好東西,不管任何時(shí)候,你只要有了土地,你就能生存,你就能過日子!
我去了我曾經(jīng)的土地一趟,那地被哥嫂們種得很是厚實(shí),末秋時(shí)節(jié),收割后殘留的粗壯的苞谷稈,告訴我這方沃土沒有虧待莊稼,沒有虧待種莊稼的人,這讓我欣慰又讓我依戀。
開挖那塊地很是費(fèi)了我們一番心血的。那段時(shí)間,一有空,我和妻就忙碌在那塊地里。妻負(fù)責(zé)撿拾并運(yùn)走碎石,我負(fù)責(zé)開挖整土。開挖土地自然是個(gè)苦差事,一鋤下去,往往與躲在土層下面的亂石發(fā)生碰撞,迸出的火花四處噴射,也讓鋤頭彈出老高,將我的雙手震得發(fā)麻劇痛,即刻爬滿血泡。好在我吃慣了苦,憑著毅力堅(jiān)持了下來。一周后,我的雙手已變得木木的,好像那手已是別人的,硬是不聽了我的使喚,以致寫起字來十分難看,形若蒙童學(xué)書,引得學(xué)生大笑,當(dāng)探知此狀的原委后,見我掌上血泡重復(fù)著血泡,便又生出一片感佩,我也趁機(jī)現(xiàn)身說法,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一番熱愛土地、勤勞自給的教育,也算另有收獲。而妻的兩手也是粗糙硌人,遠(yuǎn)遠(yuǎn)與她護(hù)士的身份不相符合了,讓她苦笑,讓她無奈。
整出來的土瘦弱不堪,要使它變得肥沃厚實(shí),可得花上不一般的功夫。好在學(xué)校和醫(yī)院不缺農(nóng)家肥,一有空我就挑來潑灑。潑灑一遍后,讓太陽曬一周,我又將地翻一遍,接著再潑灑農(nóng)家肥。如此反復(fù)三遍,直到農(nóng)家肥在土中發(fā)酵,使土地發(fā)生質(zhì)變,看到昔日那死板的黃土變成現(xiàn)如今松軟的黑土,我才開始種植。
時(shí)序已是冬日,許多品種的蔬菜早已過了種植期,我只得買來青菜幼苗——那種在寒冬中勃勃生長的愛物,避開日照,在傍晚之時(shí)栽種,又淋上水,只盼它們能好好存活,以不枉我這么久以來的苦心和下的苦力。第二天起來一看,這些菜苗無一不活得新鮮,讓我大喜大慰,感謝土地對(duì)我的賜予!感謝菜苗對(duì)我的憐惜!
至此,我每早起來的第一件事便是察看青菜的長勢,捉去喜食嫩葉的青蟲。從學(xué)校歸來,每每見了土地缺水或是稍有板結(jié),亦或長出了野草的幼芽,我都及時(shí)灑水、松土、除草,按當(dāng)?shù)乩习傩盏脑捳f,我是“把它們當(dāng)成幺兒來盤了”。
毫無疑問,我的青菜獲得了大豐收,除了能夠自給,給我省出不菲的菜錢外,還讓妻子的同事們有了嘗新的去處,也給我的同事偶爾帶點(diǎn)去,博得了一個(gè)好人緣;有時(shí)逢場,恰好又遇到我或妻休息,我們還摘來去場上賣,因我家的青菜葉大梗細(xì),肉頭肥厚,脆嫩新鮮,很有賣相,故特好賣,這也給我家掙下些閑錢,聊補(bǔ)工資度用之不足,也算意外的財(cái)富。吃不完、賣不贏的時(shí)候,我學(xué)著母親的樣子,將青菜葉采來洗凈,劃破菜梗后,于開水中一焯,撈出來在太陽下曬干,使之微黃清爽,很是搶眼。儲(chǔ)藏一段時(shí)間后,需用時(shí)再用溫水浸泡,發(fā)軟,切成細(xì)段,做扣肉蒸用,或與豬蹄、排骨燉食,都是絕佳的美味。以致醫(yī)院的美眉們常來我家蹭飯,直夸我的手藝好,人又外慧內(nèi)秀,可惜她們下手遲了,竟讓妻將我占了去!這極大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讓我更加勤奮地侍弄起這塊土地來,也更加頻繁地贈(zèng)予她們菜蔬,更加頻繁地請(qǐng)她們來我家品嘗我做的菜肴,直到我離開那里二十余年后,每與她們相遇,她們還對(duì)我的手藝念念不忘、夸贊有加。
第二年,我根據(jù)季節(jié)的轉(zhuǎn)換,種辣椒、種紅薯、種黃豆、種茄子、種豇豆、種南瓜……林林總總,品種繁多,巴不得什么都種,只嫌土地窄小了。自然,種出來的蔬菜瓜果,讓我的資金短缺有了更大的改觀。
四年后,我改行進(jìn)了城,然土地我卻沒有丟棄,平日叫妻伺候,每至休息和節(jié)假日,若不加班,我都遠(yuǎn)涉四十余里趕回去,去侍弄“我的”土地,侍弄我的蔬菜瓜果,從中種出快樂,種出成就,種出一世人緣,種出念念難忘的好口碑,也種出與土地的一世情結(jié)。
三年后,妻調(diào)往另一家醫(yī)院,我們?cè)贈(zèng)]有理由占據(jù)那地了,我便將其贈(zèng)予了他人,直到后來那地被新修的房屋擠占,那塊地才無奈地結(jié)束它的輝煌,承受它別有滋味的新的使命。
然而,那塊地與我的走出困窘,與我及他人獲取的快樂,一直息息永存,在于我情深致遠(yuǎn),永世難忘了!
特別的懷想
我是個(gè)很懷舊的人,一旦什么植入我的記憶,我就情感難變,永世不忘了。我對(duì)我曾經(jīng)的幾塊土地就是如此。
我和妻都進(jìn)城后,就丟失了土地,盡管每日忙碌,盡管有不少新的事務(wù)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可對(duì)土地的那份情愫卻難釋懷,在沒有找到新的土地的日子里,我一旦閑空下來,就顯得手腳無措、心慌躁動(dòng)。這就招來一些舊識(shí)的笑罵,說我人賤,好不容易逃離了鄉(xiāng)村,漸漸脫離了泥土的氣味,卻偏又對(duì)土地念念不忘。說現(xiàn)在不少農(nóng)村人都外出打工,遠(yuǎn)離“農(nóng)”字,在城市安家,不事農(nóng)事了,還有不少在校的農(nóng)村小孩只講享受不識(shí)農(nóng)物,而我卻若舊時(shí)的農(nóng)人,老對(duì)土地念念不忘,好似離了土地就不能生存……
我無言以對(duì),我的確如此。
一九九八年,我告別租住房,有了自己的家。在購買新房時(shí),我特意選擇了頂樓,并與開發(fā)商協(xié)商,樓頂歸我使用,在不改變樓層結(jié)構(gòu),不影響樓層承重的情況下,我要在上面栽瓜種菜、植花養(yǎng)草,以之眷戀土地、懷想土地。
搬進(jìn)新房后,空閑之余,我便在樓頂將盆缽缸罐之屬沿女兒墻擺了一長溜,再用塑料袋從郊區(qū)一袋袋地將泥土提回來倒入其中,開始種植起菜蔬花草來。在樓頂?shù)姆N植,由于盆小砵淺,遠(yuǎn)遠(yuǎn)找不到那種在大地上耕耘的那種感覺,那種快慰,真是有勁使不出,渾身憋得難受。這就更加懷念我鄉(xiāng)下的曾經(jīng)的土地來,才真切感受到土地之對(duì)于我的重要。于是,每至耕種季節(jié)、收獲季節(jié),我常常站立樓頂,眺望我曾經(jīng)的土地的方向,想這時(shí)的土地怎么樣了,莊稼怎么樣了,并遐想出土地的如何傾力奉出、莊稼的如何長勢喜人、瓜果蔬菜的如何肥美豐收!以致妻常說我癡了呆了,絲毫沒有國家干部的樣,仍舊是一個(gè)跳不出農(nóng)門的舊時(shí)典型的農(nóng)人。
每至假期,我都相邀妻子回歸老家,走訪尚未外出打工、移民城市的不多的親友,更多的是看看那些土地,當(dāng)看到大片大片的土地被閑置拋荒,我的心中便五味雜陳,有為當(dāng)下農(nóng)人再不為填飽肚子而土中刨食成為新型農(nóng)民而高興,又為曾經(jīng)維系農(nóng)民生命的土地如今被拋棄,只留下滿目的荒涼而悲戚。至此,我便關(guān)注起各種媒體來,從中探尋農(nóng)村土地的出路問題,我便想,除了退耕還林,除了土地流轉(zhuǎn),在不久的將來,還會(huì)有新的讓土地?zé)òl(fā)生機(jī),讓土地回歸本質(zhì)的舉措來的。
我又想,十年后,一旦退休,我是要回歸我的老家,回歸我的農(nóng)民本真的!
因?yàn)椋恋厥俏乙皇赖那榫壈。?/p>
責(zé)任編輯 郭金達(d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