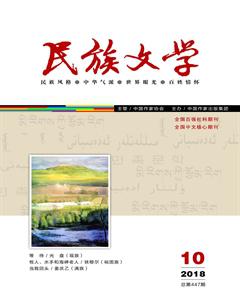道古說今話岜樓
覃瑞恒
岜樓山,又名“紅旗山”。位于大化瑤族自治縣境內古河、百馬兩鄉(xiāng)交界的紅水河畔,因狀似豎立的旗而得名。山中有洞,山頂有巖葬。傳說八年一度盛夏之夜,有兩束光照徹古河街,留下千古之謎。此山奇險無比,在紅水河上乘船可望。(摘自《大化縣志》)
一位外地文友游歷了大化紅水河百里畫廊之后,神神道道地對我說,岜樓山乃北辰鎮(zhèn)水口也。我一頭霧水,不知其所云。問緣由,才知道這是堪輿學的術語,通俗地說,是地理先生談風水的行話。
后來我通過查閱資料,找到了關于“北辰”一詞的解釋。《地理人子須知》卷五上:“北辰者,水口間巉巖石山,聳身數(shù)仞,形狀怪異,當于中流,挺然朝入者是也。”
吳公《口訣》云:“北辰是石山嵯峨,雄昂高插,峭壁巖崖突兀奇怪,生耳,生角,生嘴,如將軍,如判官,如小鬼,如臥龍,如麒麟,如獅象,如海螺,如飛鳳,如仙鶴,如猛虎,如展旗,如堆甲,如涼傘,如走旗,如鋸齒,如槍刀,如幡帶,如排符,如筆架,挺然拔聳萬仞,巍峨屹立,堆疊于水口之間。望之而神驚,就之而心怖,崚嶒峻險、怪異巉巖者是也。”
用這些文獻記載的文字與岜樓山相比對,說岜樓山是“北辰鎮(zhèn)水口”,倒也十分的貼切。源于此,我不禁聯(lián)想到,民國時期隸屬于平治縣(1934—1951年)的百馬鄉(xiāng)為什么被稱為“鎮(zhèn)江”——或許是因為岜樓山鎮(zhèn)住了紅水河的水口而得名的。鄉(xiāng)因山而名,可見這座山在當?shù)厝藗冃闹惺嵌嗝吹闹匾 斎贿@只是我的猜測,并沒有什么文獻記載或民間故事作為依據(jù)。
許多百馬人,或者曾在百馬這一片熱土上工作、學習、生活過的人,他們的心目中,早就把岜樓山作為百馬的象征了,它承載著人們濃濃的“鄉(xiāng)愁”。即使離開百馬許多年,許多往事和恩怨情仇都已煙消云散,物是人非,但只要一提到“岜樓”,人們便覺得格外的親切,人人似乎都有許多故事要對他人訴說,但又不知從何說起。于是大家就想方設法地去追尋有關岜樓山的點點滴滴或只言片語。
關于岜樓山的形成,百馬籍的中學高級教師覃承秀曾做過幾種地質推論。其中一種說法是,現(xiàn)在的岜樓山與對面的古河伏內村幾處巖崖斷裂分離后,地殼能量將它連同南面的大土嶺,一同向南推移。由于運動能量巨大,導致切斷面山崖前騰出了一條溝壑,紅水河便從騰出的溝谷中通過,形成了一套河灣。
另一個推測是,岜樓山是原地冒出來的。由于造山運動,強大的地層能量將地殼板塊隆起形成山脈,山脈的邊緣往往是槽溝。岜樓山往下4公里,原來可能是一條與岜樓山連綿不斷的小山脈。由于這條山脈下面是地下河,其余山脈全部下沉,而岜樓山只有半壁山斷裂下陷,留下了半壁壯麗的石山。
這種地質推論是對還是錯,現(xiàn)在很難得到確切的印證。總之,岜樓山是天地之造化,是大自然遺留給人類的寶貴禮物。
我常常想,如果岜樓山不是置身于交通閉塞的大化,而是居身于諸如桂林等風景名勝區(qū),古往今來一定會有多少文人雅士為之題詩作賦留下墨寶。如今,岜樓山上幾乎沒有留下什么文化遺跡。只有一處石壁勒記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當?shù)孛癖姙樘颖鼙I賊,在岜樓山上修建石寨的文字。
崖刻碑文為正楷體,標題為“克修厥后”四個字,碑的正文為“謹修山石寨以避賊風而安居待太平者也,所費工銀即刻芳名于后,以永世不朽云耳”。接著刻有三十六個捐銀獻勞人員的名單,其中覃海清等三十一人每人捐錢六百文;覃永成等五人以勞代銀,落款為“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立記”。
這段碑文真實地記錄了110多年前當?shù)氐纳鐣L氣和治安狀況,反映了當時壯族人民具有高度的防范意識和公益意識,也形成了較強的凝聚力和創(chuàng)造力。
億萬年過去了,岜樓山依然屹立在紅水河畔,滔滔紅水河依然日夜不息奔涌而去。如何給岜樓山增添些許文化氣息,讓它多承載更多文明信息留傳給后人,是許多有識之士的共同愿望。
時間推移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當時我在岜樓山腳下的百馬中學教書。記得在一個溫暖如春的冬日,我們三位年輕語文老師在韋綏權校長帶領下,登臨了巍然聳立在紅水河邊的岜樓山。站在峰巔,四周美景盡收眼底,令人心曠神怡、飄飄欲仙。這時,韋綏權校長凝眸靜立,不一會,一首七律詩便順著他那低沉雄渾、飽含激情的聲浪里流出來:
擎天巨柱鎖煙霞,醉里登臨嘆物華。
足下悠悠一水過,胸前渺渺數(shù)峰爬。
山門笑對龍風洞,石棧愁連猿畏峽。
尊位版圖何日點?芳名得以遍天涯。
詩中的“龍風洞”“猿畏峽”,是我們登山時杜撰出來的岜樓山“風景名勝”。作者將它們嵌入詩中,景與情融,對稱工整,渾然天成,直令我們幾個格律門外漢擊掌叫絕。
如果說今后岜樓山還能夠存留一些文化元素,我想,韋綏權先生這首詩應該算是其文化源頭之一。
幾年前,我編印了兩卷“內部資料”《岜樓詩稿》,集中收錄了本土幾位詩友的數(shù)百首詩詞。在“癸巳集”的前言里,我對為什么用“岜樓詩稿”作書名做了這樣的說明:
之所以用這個書名,是因為幾位作者都與岜樓山有關,也就是說都與百馬這個地方有關。……我們的詩歌里,也都有“岜樓”這座山。而今,在我們的心目中,“岜樓”已經上升到了精神層面,它是形而上的,成為一個詩歌意象,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和特定的地域色彩了。
而在“甲午集”前言里,我對一些好心詩友提出用“岜樓”作書名,其所涵蓋的地域性太狹窄,與詩集中詩作的內容和水平不相稱,我做了以下的答復:
“岜樓”確實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它獨秀于百馬的紅水河岸邊,除了鐘愛它的詩友吟誦過它,古往今來為它留下詩篇墨寶的不多,它像是“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的小家碧玉,閑看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世間的喧囂繁雜、功名利祿似乎與它無關。岜樓山遺世獨立的特質,恰好與幾位作者心心相印,于是我們初衷不改,仍然把《岜樓詩稿》作為“一畝三分地”。
關于岜樓山,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但夜已很深,睡意來襲,我要夢回岜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