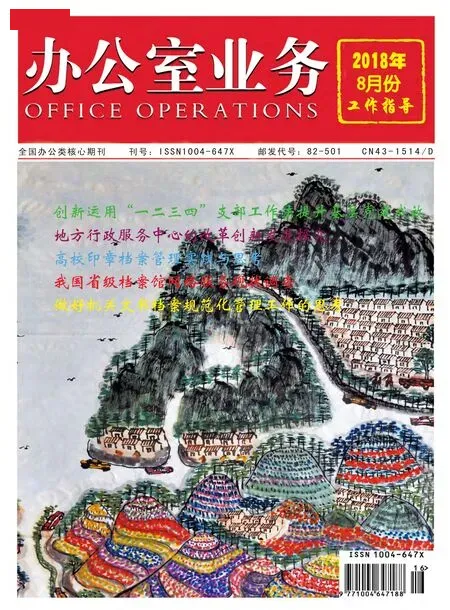互動論視角下的檔案資源建設與檔案文化傳播
在“社會互動論”中,“社會互動”被解釋為在一定的社會關系背景下,人與人、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等在心理、行為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在微觀社會學層面,“社會互動論”又被稱為“符號互動論”,其核心主張是“動態互動”。檔案文化傳播與檔案資源建設之間的關系,應是互動共生,相輔相成。因而,在倡導加強檔案資源建設的同時強調檔案中的文化資源開發與傳播,實為基于“互動”的統一性戰略思考。檔案文化傳播依賴于檔案資源的積累,同時也能進一步促進檔案資源建設的可持續發展,而檔案資源建設也需要以檔案文化傳播為鏡來進一步反思其內核、結構、類型等要素。
一、以“文化價值”為內核的檔案資源建設
(一)檔案資源建設的結構與趨勢。檔案的資源結構本已十分復雜,近年來,伴隨信息時代的跨界與融合,又有越來越多的資源進入檔案視域。從檔案資源建設主體維度,可將檔案資源分為國家檔案資源和社會檔案資源;從檔案資源建設類型維度,可將檔案資源分為行政-司法檔案資源(包括公文檔案資源、民生檔案資源等)和社會-文化檔案資源(包括口述檔案資源、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資源、名人檔案資源等);從檔案資源建設地域維度,可將檔案資源分為城市檔案資源和鄉村檔案資源;從檔案資源建設介質維度,可將檔案資源分為實體檔案資源和數字化檔案資源。在我國,國家檔案資源概念由國家檔案局原局長毛福民在2002年提出。后有學者提出了社會檔案資源的概念,即“由社會組織、家族家庭或公民個體形成、所有并管理”,并認為社會檔案資源“區別于國家檔案資源,傾向于公民個體個性化檔案服務的新型檔案資源,具有明顯的服務性、開放性和社會性”。這與國際檔案界積極倡導的社會-文化檔案資源建設理念相一致。近幾十年來,西方檔案界從強調檔案的司法-行政屬性逐漸轉向重視檔案的社會-文化屬性,尤其注重檔案文化資源的建設和檔案的社會公眾教育功能。按照“符號互動論”的觀點,人們采取行動,或者對別人的行動做出回應,或者以共有和交互的方式行動。社會互動構成了人類存在的主要部分。文化是人們在交流中創造的,但人類互動的形式又來自于對文化的共享。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的共享成果,而這些成果又必須通過檔案的記錄和保存得以傳承。因此,筆者認為未來口述檔案、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名人檔案等社會-文化資源將成為我國檔案資源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讓檔案的官方文化回歸到社會記錄的本質上來,突顯檔案資源的“文化價值”。
(二)檔案資源建設的“文化價值”內涵。國外學者U·O·A·埃思認為:保存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檔案對產生它們的國家的文化價值,檔案是人民的文化財富,在文化領域上占據一定的位置。從文化角度出發,一個國家的檔案是研究社會政治、經濟、歷史和發展的最重要的信息資源。檔案資源建設圍繞“文化價值”內核,將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檔案資源收集的具體實踐缺乏統一性的問題,澄清關于檔案本質屬性及其對社會價值的模糊與混亂認知。符號互動論的代表人物米德認為,人類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意義的影響,并且多數文化意義是象征性的。人類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學習由社會建構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義。人類互動是基于有意義的符號之上的一種行動過程。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的共享成果,這些共有產物不僅僅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而且包括物質對象。檔案資源建設的“文化價值”內涵就包括文化的各項構成要素,符號、價值觀、規范、約制和物質文化等。符號是指一群人所認可的有意義地表達其自身之外的事物的東西,有語言、文字、校徽、旗幟等。如上海市教委通過建立上海話語音檔案,把上海話盡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價值觀是一個社會中人們所共同持有的關于如何區分對與錯、好與壞、違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觀念。價值觀可從民間傳說、藝術、娛樂及其他媒介得到體現。如我國中央檔案館等7家單位共同整理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這些檔案體現了人們熱愛和平、珍惜生命的價值觀。規范是人們在特定環境下被要求如何行動、如何思考、如何體驗的期望。規范包括社會習俗、民德和法律。如云南省曲靖市為記錄和保護“劉興幫把式舞”“彝山上的弦音”等特色習俗,專門建立“曲靖市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影像檔案”。約制是人們被迫遵從社會文化,或者說以一種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去行動。如各級各類檔案館都將部門工作條例、規章制度納入歸檔范圍。物質文化是一個社會普遍存在的物質形態,如書籍、衣服、工具等。如我國眾多高校檔案館設置了實物檔案分類,收集名人字畫、獎杯獎狀、榮譽證書等。
二、以“檔案資源”為基礎的檔案文化傳播
(一)檔案文化傳播新的時代特征。檔案工作的最終目的在于檔案信息資源的社會利用,檔案文化傳播是實現檔案資源全民共享的最有效舉措之一。進入21世紀,伴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跨越式發展,檔案文化傳播日益普遍和活躍。同時,檔案文化傳播也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征。首先,“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為檔案文化的大眾傳播提供了現實性與可能性。近年來,檔案的社會記憶觀逐漸被檔案學界關注并接受。檔案文化的社會記憶與社會建構離不開社會大眾的主體參與。傳統的檔案文化傳播模式是以官方為主體的自上而下式,社交媒體的迅速崛起,可以讓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人群”進行大眾傳播。因而,新型的檔案文化傳播模式將是官方為主的自上而下式與大眾為主的自下而上式的結合。其次,“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檔案文化傳播的途徑與內容。在前互聯網時代,檔案文化傳播途徑主要依賴報刊、電視等傳統媒體,傳播的內容多以文字為主,圖片為輔,形式較為單一。而在“互聯網+”時代,伴隨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社交自媒體的興起,檔案文化傳播的途徑得以拓寬,錄音、錄像將與文字、圖片共同構成立體豐富的檔案文化傳播內容。最后,“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豐富了檔案文化傳播的形式。傳統時代,檔案文化傳播以編研書籍和圖文展覽為主。“互聯網+”時代的檔案文化傳播借力新技術,可通過網上展覽、開放電子檔案信息、及時與大眾互動等形式展開。
(二)檔案文化傳播的基礎資源構成。檔案文化傳播必須依賴基礎的檔案資源,否則就是“無本之木”。新時代“互聯網+檔案”的文化傳播模式,不僅是簡單地通過互聯網“傳遞”檔案文化,而是利用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與豐富性,加深檔案文化傳播與檔案資源建設基礎工作的緊密結合。筆者認為,檔案文化傳播的基礎資源構成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傳統的紙質檔案資源。以文字為主的紙質檔案是檔案文化傳播的“恒定”資源,如果沒有語言文字,大部分人類的思想和文化將不復存在,更談不上傳播。第二,新興的數字檔案資源。數字化時代檔案資源多樣化與豐富化已成為趨勢。電子文件、聲像檔案等資源的形成為檔案文化傳播提供了便利。同時,在“淺閱讀時代”,聲像檔案資源豐富了檔案文化傳播的內容,提高了檔案文化傳播的速度與效果。第三,特色的實物檔案資源。實物資源因其“文物”屬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不是檔案部門的主要資源建設范圍。事實上,由于部分文物和檔案難以區分,一般采用服從事實原則,即由文物部門發掘和保存者,歸屬國家文物部門,反之,則歸屬國家檔案部門。第四,非遺、口述等文化檔案資源。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口述歷史等是檔案文化傳播的重要歷史文化資源基礎,若將對這些資源的保護與文化傳播運用得當,可構成相輔相成的正相關關系。
三、檔案資源建設與檔案文化傳播的“互動”
(一)檔案資源建設與檔案文化傳播的“互動共生”。按照社會互動系統論的觀點,社會系統是一個開放的自組織系統,常常通過與外部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形成自身的結構、功能并發生作用。同樣,檔案也是一個巨大的復雜系統,有很多子系統構成,形成合力并發揮功能。其中,檔案資源和檔案文化都是該系統中的子系統,共同對該系統功能的發揮起著積極作用。因而從理論上來說,檔案資源建設與檔案文化傳播應該是互動共生的,檔案資源建設奠定了檔案文化傳播的基礎,檔案文化傳播的發展又促進了檔案資源建設的實踐統一性。“教育工作坊(Education Workshops)”是英國國家檔案館特色的檔案文化傳播項目,旨在開發利用館藏歷史檔案資源向中小學生傳播英國檔案文化,其教育團隊通過在線數字教育課程可以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學生進行互動。其中,不列顛與大屠殺(Britain and the Holocaust)課程通過向學生展示外交部1942至1944年間收到的電報、無線電廣播和報告等檔案,讓他們了解納粹的侵略事實以及英國政府的反應。浙江省湖州市南潯鎮是中國檔案學創立者和奠基人吳寶康的家鄉。2017年,為紀念吳寶康先生百年誕辰,湖州市南潯區委、區政府充分挖掘檔案資源,拍攝了以吳寶康為主題的國內檔案界首部知名人物紀錄片《他是一座山——新中國檔案教育開拓者吳寶康》,通過鏡頭向大眾傳播了中國檔案學界一代宗師的革命生涯和他為新中國檔案教育和檔案事業發展鞠躬盡瘁的一生。與此同時,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通過采訪吳寶康的多名親屬、同事、學生和生前好友,也留下了大量的口述檔案和聲像檔案,以文化傳播為契機,開啟了檔案界知名人物檔案資源建設的新篇章。
(二)發揮檔案文化傳播對檔案資源建設的反向指導作用。社會互動論的“鏡中我”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自我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主要是通過與他人的社會互動形成的,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態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鏡子”,個人通過這面“鏡子”認識和把握自己。該理論提出者庫利認為,“鏡中我”也是“社會我”,傳播特別是初級群體中的人際傳播,是形成“鏡中我”的主要機制。一般來說,這種以“鏡中我”為核心的自我認知狀況取決于他人傳播的程度,傳播活動越活躍,越是多方面,個人的“鏡中我”也就越清晰,對自我的把握也就越客觀。由此看來,檔案文化傳播猶如檔案資源建設的一面“鏡子”,加強檔案文化傳播,能夠反觀檔案資源建設,隨著文化傳播的廣泛與深入,檔案資源建設的定位也將越來越清晰。2011年,我國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三條規定“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認定、記錄、建檔等措施予以保存,對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由法可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除了采取認定、記錄、建檔等措施予以保存外,還應采取傳承、傳播的措施對其進行保護。江蘇省張家港市在非遺傳承人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過程中發現,為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發展,需要重新審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檔案資源建設。于是,他們將家庭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組織并指導非遺傳承人家庭開展建檔工作,通過文字、聲像、實物及口述檔案等形式,全面、客觀、真實記錄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元的藝術內涵。截止2017年底,張家港市48位非遺項目傳承人已全部建立家庭檔案,并完成檔案的數字化,市檔案局也建立了專門的非遺檔案數據庫,實現對非遺檔案的信息化管理。在第二屆中國(張家港)長江流域民間藝術博覽會上,張家港市非遺項目傳承人家庭檔案更是登上民博展臺,向來自長江流域12個省市的200多位民間藝術家和非遺傳承人展示了檔案在非遺項目傳承保護中的獨特作用。
四、結語
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促進了檔案文化傳播的繁榮,同時也促使檔案資源建設領域產生變革,以適應新時代文化發展的需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談到中國傳統文化,表達了自己對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價值體系的認同與尊崇,也多次提到文化自信。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檔案記錄、保存、保護、傳播文化,是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的文化財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檔案資源建設和檔案文化傳播共同作為“記憶工程”和“文化工程”受到國家上下各級各類檔案館的重視。檔案資源建設重點在于記錄文化、保存文化,而檔案文化傳播的重點則是保護文化、傳播文化、共享文化。若二者能夠建立起長效互動機制,抓好檔案各類原始資源的積累,注重傳播讓全民共享檔案的歷史文化價值,則無論對發展我國檔案事業還是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信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