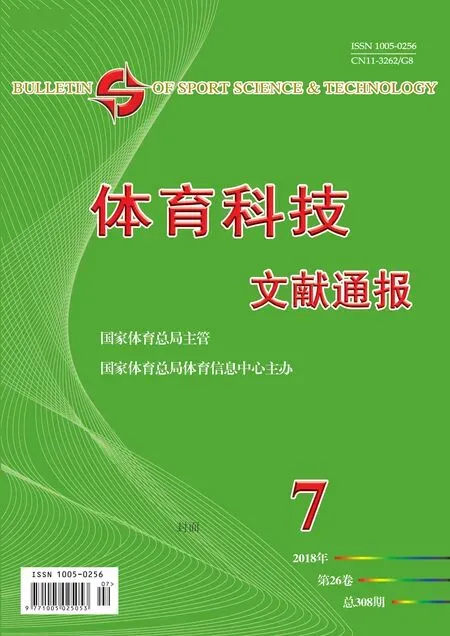武術運動促進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發展的研究
葉灼怡,時 杰
適應與發展是個體人生歷程的基本任務,也是青少年成長面臨的最重要的兩大課題。“不能把個人的生長與社會的變化分開,也不能把個人生活中的同一性危機與歷史發展中的當代危機分開,因為個人的生長與社會的變化、同一性危機與當代危機有助于互相制約,而且確實是彼此聯系著的”[1]。伴隨著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變遷,青少年的價值觀念的變遷、沖突和失范現象也在不斷上演,諸如青少年厭學逃學、網絡成癮、不務正業等越軌和犯罪行為嚴重影響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長發展。研究表明,適度參與體育運動可以培養青少年的自我意識,加速青少年對社會準則的了解,增強青少年的社會適應能力。
武術從人類最初的生存斗爭、防身自衛、保家衛國到健身娛樂,一路發展滲透于人類的生存發展和生產活動中。習練、掌握格斗運動技能本身就是掌握一種生存技能,同時也是習練者進行社會適應的一個縮影。本文以自我同一性發展和社會適應行為理論為分析視域,探析武術運動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自我同一性發展和社會適應的影響。
1 社會化和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是促進青少年成長的重要環節之一。
自我同一性理論是由埃里克森(Erikson)提出的。自我同一性是自我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埃里克森提出“自我同一性是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時間和空間中認識‘自己是誰’‘青少年時期的中心發展任務是同一性對同一性擴散’”[1]。自我同一性可理解為個體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一時間和空間里對自己內在的一致性和連續性的主觀感覺和體驗,這種體驗被描述為“熟悉自身的感覺,是一種知道個人未來生活目標的感覺,是一種從個體信賴的人們中獲得所期待的認可的內在自信”[1],屬于個體因素范疇。青少年發展會受到自我同一性影響,自我同一性是青春期個體發展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也反映了個體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沖突與矛盾,其形成是人格完善的標志。順利發展的自我同一性會使青少年能更好地認識自我,發現自我,對青少年的人格完善和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適應行為源于鮑文(Bowen)提出的自我分化概念,即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個體是受情緒還是受理智支配的能力,是個體社會適應能力的外在體現,屬于環境因素范疇[3]。個體為了更好地融入社會群體中,必須適應外在社會文化、環境的要求和內在身心發展的要求,具備在生活、學習和交往等實際活動中學會選擇和回避的能力。其中平衡自我意識獨立、維持與重要他人親密的行為,就是個體的社會化過程,是一個人角色承擔與學習的過程,一個由生物的“人”轉變為社會的“人”的過程。所以,青少年的成長的過程伴隨著個體社會化的不斷深入,通過干預手段和措施整合個體的自我認知、生活經驗和將來期望,促使青少年積極的“自我投入”,從而引發“將來自我投入的愿望”[1],能夠使其形成或確立自我同一性,成長為一個人格完善、身心健康的個體。
因此,研究體育運動對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和社會適應行為的影響具有現實意義和研究價值。
2 武術中“武德”的教化作用
武術從它產生以來,就被納入倫理之道。而武德作為中國武術重要的內涵,它也是習武之人應共同遵循的倫理道德規范。崇尚武德是習練武術之人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主要表現在練武與修身、立志與習藝、技藝與品德的統一,把修身養己看作立身處世、實現人生價值的根本[4]。《大學》中說“內外兼修”,“內”是品性,而“外”是指技藝。“冬練三九,夏練三暑”,既是提高技藝,更是磨練精神。《少林武術新戒約》中強調:“凡習武之徒,必須以賢為師,謙虛好學,尊敬師長,崇揚武德。武術界非常講究師徒間、朋友間的禮儀,因此拳諺有 “未曾學藝先學禮,未曾習武先習德”、“失禮者不可教之,失德者不可學之”之說,這些古訓教導習武者恃武而內斂,習武而不張揚,尊重對手,謙恭禮讓。具體表現可由武術的“抱拳禮”[5]窺知,其含義為:右手握拳喻“尚武”、“以武會友”;以左掌掩右拳,喻拳由理來,講究“文”;屈左拇指,喻不自大;左掌四指并攏,喻四海武林同道團結,齊心發揚光大武術。在武術的現代傳承中,這種蘊含“內賢外王”精神的儀式性活動升華為具有教化功能的現代文化符號[4]。可見,中國武術在習武之際崇尚體位本能,但決不恣縱放肆—這就是作為武術內在之仁的“德”與武術外在之“武”的身體技術相輔相成的特點,它們一剛一柔,構成了武術運動價值觀念對立的兩極[2]。《論語》言:“仁者無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習武者在習練過程中領悟為人、處世、治學的道理,從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與人文素質,促進個體的人格塑造。
3 武術運動對青年自我同一性與社會適應行為的促進
3.1 武術為青少年的角色體驗提供場域和環境
人類的發展來源于自我意識的覺醒,同時人類的發展也離不開環境因素,更甚的是人與人之間制約關系和影響。在現實生活中,青少年能合理定位、轉換社會角色并且與社會中其他的角色和諧相處是個體走向成熟的基本標志,武術作為一項體育運動為青少年提供了角色扮演變化的場域。武術是以人體作為進攻武器的體育運動,雙方在格斗規則的約束下進行身體對抗,選手個體都希望能夠打敗對手、贏得比賽,向他人展示“我”的強大,同時這也是“探索自我”的過程。其中“我”的存在—自我同一性使得個體“熟悉自身的感覺”,按照“理想的自我”去要求、調控“現實中的自我”[6]。研究認為武術運動中對抗雙方的攻防運動不是由思維和思考的過程來決定的,而是由攻防意識—注意的趨向和注意的集中所決定的,個體的注意對象是對手和自己,個體做出反應的理由是對手和自己的情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要做什么才能應對,才能改變[7]。個體的格斗技術發揮、戰術運用均在進攻和防守角色的變換中表現:近身攻防轉換、躲閃進退不斷地使個體控制自我、調整自我,發揮“我”的對抗潛力來應對“他”人的進攻和防守。武術運動為個體的“我”和“他”出現提供了場域,這就好比為當前競爭型的社會提供了一個類似游戲的模擬場域,使得參與其中的青少年有了各種角色體驗,從而推動青少年個體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社會適應能力的提高。
3.2 “同輩群體”對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社會適應具有積極的影響
通俗來講,那些在興趣愛好、年齡段、家庭背景、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較接近的人們自發結成的社會群體被稱為“同輩群體”[8]。埃里克森認為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及發展離不開社會環境的作用,青少年習練武術、參與比賽要面臨諸多的人際關系適應:在教練和師傅面前,個體應自我定位為“學生”或“徒弟”;在“同門”面前,個體自我定位為“師兄弟”或“師姐妹”;在體育比賽面前,個體自我定位為“運動員”或“裁判員”等。多重角色的身份使得青少年個體在習武環境中對自我行為有著多重定位。一般而言,在上述關系中同門師兄弟作為同輩群體于平時生活、訓練中交往最為密切,其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和選擇傾向。在這種相對民主和較為平等的的環境中,個體和同齡習武者共同進行生活交往、技術訓練、對抗交流等社會行為,提升自我的運動技能和武德修為,塑造個體的行為方式和價值選擇,繼而得到同輩群體的支持及獲取歸屬感。一般認為,青少年個體在習武過程中精神上的愉悅與滿足,超越了單純技擊格斗的直接功利性的局限性,形成一種間接地、潛伏于感性形象之中的精神上的功利性,從而固化了個體自我認可和自我成就感。
3.3 武術的規則意識對青少年的社會行為具有警示和約束意義
武術運動雖然是追求身體直接對搏與格斗的實戰運動,但是出于對參賽者的保護和對暴力的消解,現代競賽規則和裁判法中都對“禁擊部位”和“禁用方法”做出了相關的規定。在這里,我們不得不探討下深植于人類內心的“暴力因子”。暴力是人類野蠻時期的原始生存本能,暴力元素是潛伏于人類心理深處的攻擊性因子。武術運動的技擊性源于人類原始的“求生”意欲,是積淀于人性深處的野性訴求[9]。但當前社會是法制社會、文明社會,人類文明的進步要求人們由原始野性逐漸蛻變為文明理性,不允許個體肆意地攻擊他人。不過,攻擊欲望作為生物體的原始本能又不可避免地蠢蠢欲動,成為一種潛在的誘因在與人的理性斗爭。通過格斗運動的身體對抗—這一載體,青少年內心的原始欲望得到想象性的滿足快感,實現一種以合理的潛在形式發泄攻擊欲的快意,從而滿足“人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會生命”的和諧[9]。
體育運動是有規則制約的,武術亦是如此。武術作為一項現代競技體育運動,其比賽必須按照統一的規則、程序來進行。在現代武術格斗競技中,規則的更迭和演變制約著參賽選手的技戰術發揮和比賽的對抗強度,比賽結果的成敗、輸贏則直接關乎著參賽者的利益得失;但是武術對習武者個體有著武德禮儀的約束。這就導致出現了比賽結果的“成敗”與個體“為人之道”的對壘現象,如同現實社會的虛擬,其實質就是是個體對規則與秩序的考量和沖突妥協的選擇[10]。運動規則和武術禮儀的在場,使得個體在面臨打擊和失利時自我約束,恪守紀律,減少各種“陰招”等不良行為出現的可能性,促進青少年的人格完善和武術運動的健康發展。這對于青少年來講是個體參與進行社會適應的過程;經過個人的成長和環境的熏陶,進而成為一種穩定的個體行為模式。
4 結語
適應與發展是個體人生歷程的永恒的主題,自我同一性的發展可以說直接影響青少年一生的健康成長。現代社會中,青少年在社會適應過程中面對的各種矛盾突顯,面臨扮演多重社會角色的挑戰,個體體驗聚集著諸多困擾。本文通過自我同一性和自我分化理論,結合體育運動的教育意義,闡釋了武術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教育價值和對自我同一性發展的影響。為此,建議學校體育主管部門能夠在當前的體育教學內容中增加諸如散打等傳統對抗類項目教學的比重,同時也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武術格斗項目的推廣創造條件。
[1] 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M].孫名之,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 李軍,解勇.武術的武德和行為規范的重建[J].體育學刊.2002,9(5):65-67
[3] 王輝,大學生自我同一性和自我分化對職業探索行為的影響[D].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
[4] 邱丕相等,武術文化傳承與教育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 蘇勇,武術“抱拳禮”的儒學內涵探析[J].少林與太極.2014(6):9-10.
[6] 劉勁松.高校武術課的教學訓練現狀及改革設想[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5(4):32-33.
[7] 朱榮軍,格斗運動和格斗運動意識[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5-7.
[8] 陳黎,流動兒童“自我”概念形成中的利弊分析[J].當代青年研究,2006(11):9-13.
[9] 孫剛,從“暴力美學”視域審視武術技擊美的心理歸因及和諧思想[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0,27(3):317-321.
[10] 張和等,自我同一與社會化促進:南京青奧會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J].體育與科學,2014,35(3):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