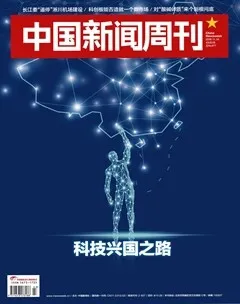“一戰”百年紀念:依然不能永別的戰爭
徐方清
“雙11”那一天,在陰雨綿綿的巴黎凱旋門下,一位當地華裔少女用沉靜的中文朗誦將世界的記憶拉回一百年前:
“忽聞教堂鐘聲、工廠汽笛聲,以及廠外歡呼聲與歌唱聲同時并作,余輩驚問何故,使君休戰條約已簽訂,戰爭從此可以終止!此何日也?記憶永久不忘之,1918年11月11日……”
1918年11月11日,德國政府代表與協約國代表在法國貢比涅簽署停戰協議。此時在法國西北部城市魯昂,在華工團當翻譯的23歲青年顧杏卿,將聞悉停戰的瞬間寫在了日記里。100年后的2018年11月11日,法國總統馬克龍主持了一場高規格的“一戰”結束紀念活動。現場觀眾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德國總理默克爾等70多位各國政要。華裔少女現場所朗誦的文字就出自顧杏卿之手。
始于1914年、結束于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二戰之前人類歷史上破壞性最強、波及面最廣的戰爭,共計約有970萬軍人和1000萬平民倒在了戰火中。遠離歐洲主戰場的中國也未能幸免,“一戰”期間,英法兩國從中國招募華工約14萬人。

11月1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右二)、法國總統馬克龍(右四)、德國總理默克爾(右五)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右六)等多國領導人,出席在法國巴黎凱旋門前舉行的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儀式。
100年后的今天,戰爭依然不曾遠離。對于“一戰”原因的探尋,這100年來從未停止。是德國的驟然崛起與英國的霸權直面相撞?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孕育出了戰爭怪獸?還是民族國家體系歷史演變的結果?都是,又都不盡然。
從歷史視角俯瞰當下,雖然制約戰爭的力量比“一戰”發生前要強大得多,但制度抗衡起伏不定,戰略信任一直脆弱,民族國家間尤其是大國關系中的“囚徒困境”依然存在。
樂觀一點看,“核恐怖平衡”“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經濟全球化,以及理性政治的構建,有可能會讓人類免于又一場世界大戰。但與此同時,“冷戰”“涼戰”“經濟戰”“網絡戰”等等輪番登場。誰又能清晰辨明,在民族主義和非理性思潮抬升的背景下,這些“戰爭形態”與真正的熱戰之間的邊界是什么、在哪兒?無人敢斷言又一次世界大戰不會到來。
馬克龍在現場講話中,呼吁各國銘記戰爭的慘痛教訓,避免歷史悲劇重演。他還抨擊“自身利益優先”的論調,稱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這番話,多少是沖著奉行“美國第一”理念的特朗普而說。
在“一戰”百年紀念活動現場,晚到的普京快速地與并排站立的馬克龍、默克爾和特朗普等人一一握手。他還輕拍了一下特朗普的小臂,笑著沖他豎了下大拇指。只是這種釋放善意的互動,并不能遮蔽美俄間在眾多領域的劍拔弩張。
約20天前,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冷戰前夜誕生的《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其理由是:一來俄羅斯長期違反條約,并扯上和條約并無關系的中國;二是為了讓美國“開發受這類條約限制開發的武器”。
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的方式,映射著大國間戰略信任脆弱和協調機制式微的困局。“核恐怖平衡”也許是避免大規模戰爭的一種威懾手段,同時也讓人類處于一腳踏空就萬劫不復的懸崖邊緣。
海明威在《永別了,武器》中說,戰爭一無是處,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什么事情會比戰爭更糟糕了。但人類至今沒有找到永別武器的途徑,甚至通過武器升級和局部戰爭來謀勢、漁利的思潮還時而抬頭。此時的“一戰”紀念,除了不該忘卻歷史的教訓,更需要在警鐘長鳴中堅守住探尋遠離戰爭路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