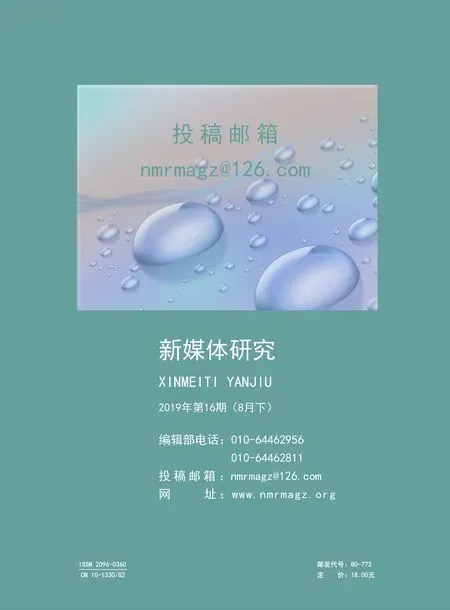中國清朗網絡生態建設研究
宋紅巖
摘 要 立足于當前網絡發展與新時代中國網絡空間治理的現實要求,對網絡生態的內涵、內容建設與運行機制構建進行了闡述。認為網絡生態是由網絡氣候、網絡環境與網絡主體等內外各種要素構成的動態發展的有機整體。在清朗網絡生態內容培育上,提出應從網絡生態傳播氣候頂層設計、網絡環境規制設置與網絡生態主體能力提升三個層面加以建設。在運行機理上,分別從結構層面、功能層面、運行環境層面上探討中國清朗網絡生態運行機制構建。
關鍵詞 清朗;網絡生態;建設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8)16-0006-05
當今網絡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生活方式,已成為社會發展進程中重要的生態變量。網絡生態建設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維度,也是實現國家網絡治國理政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當前中國網絡生態建設,正由網絡強國的理念的提出向社會治理實踐層面落實推進,由國家社會治理向全球共享轉向。近幾年國家密集出臺《網絡空間安全戰略》《網絡安全法》等政策文件,加強了網絡虛擬社會治理的規范化建設。同時,順應數字信息科技發展浪潮,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數字中國與智慧社會治理方略,大力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和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傳統實體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加快物聯網技術和應用,發展數字共享經濟。此外,還提出了建構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主張,推動互聯網領域的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模式中國方案。
1 網絡生態的內涵界定
近年來網絡生態正成為國內外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學術領域,國內外對網絡生態概念的提出都是在世紀之交,在國外最早提出網絡生態概念是在1998年,2003年又有學者做了進一步闡述[1-2]。我國學者張慶峰在2000年第一個提出網絡生態的概念,認為“所有的影響網絡發展的其他社會系統構成了網絡發展的生態環境,網絡與網絡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時,便形成了網絡生態”[3]。隨著網絡技術迭代嬗變,網絡傳播生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互聯網掀起的第四次傳播革命正在重塑世界,帶來傳播模式變革[4],熊澄宇認為新媒體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生產力,傳媒改革的實質便是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5]。但同時,新媒體向移動化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微視頻等新興網絡文化生態的蓬勃發展,使得移動視頻之爭愈演愈烈[6]。黃意武認為網絡傳播生態是在網絡平臺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是文化共融共生、和諧發展的體現,它使網絡文化呈現出一種健康、和諧的發展狀態[7]。還有學者提出網絡已超出了原有的工具理性,網絡生態的去中心化對人的主體性的發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
戰[8],由于網絡信息污染、網絡信息侵犯、網絡信息分布不均勻、信息膨脹與信息短缺等問題,甚至會產生網絡生態危機[9]。同時,網絡傳播生態失衡導致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網絡傳播倫理失范又破壞網絡傳播生態的平衡,二者形成惡性循環[10]。對于網絡危機治理,有學者提出當前我國網絡傳播生態建設面臨官民輿論對立、主流文化缺乏號召力、商業化嚴重、網絡道德建設不足等突出問題[11]。還有學者從復雜性視角對社會秩序的理性設計和社會系統自主演化兩個維度來探討網絡傳播生態建設[12]。
對于網絡生態的發展狀況學者們從不同的領域視角進行了闡述,但對于網絡生態的概念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義。邵培仁提出媒介生態系統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人、媒介、社會、自然四者之間通過物質交換、能量流動和信息交流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構成的一個動態平衡的統一整體,可分為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等[13]。也有學者認為網絡生態是由信息因子、主體因子和環境因子構成[14]。當前網絡生態與傳統媒介生態以及相對“老”的網絡媒體有所不同,網絡影響的廣度、深度與厚度遠遠超過最初主要為人們提供信息交流為主的技術平臺設計,網絡生態的內涵與外延都不斷更新擴大,特別是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引擎的科技發展使得網絡成為涵蓋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與方面,形成全媒體泛傳播形態。網絡生態系統日益龐雜紛繁,其自身由現實與虛擬社會構成,對于現實社會來講,大到全球國際環境,再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況都構成了生態環境與系統運行的主客觀因素,其中每個子環境自身都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發展的子生態子體系。而在網絡虛擬空間中新技術、新平臺、新傳播范式以及網絡主體也不斷地進行著更新、分化與重組,最后匯流到整個網絡生態系統,從而形成動態發展的網絡生態體系。從整體上來看,網絡生態大體上可分為三大構成部分:生態氣候、生態環境與生態主體,如圖1所示。
其中,生態氣候主要是指網絡存在與運行的外部宏觀環境,主要包括國內、國際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自然等條件狀況,其是網絡生態所依賴的客觀存在,也是網絡生態構成的資源與動力源泉,在宏觀上影響著網絡生態的運行。生態環境主要是指網絡自身運行的構成要件,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或決定著網絡生態的質量與效能,它主要包括網絡社交平臺等硬件設施、信息技術發展形態、規則議程設置等剛性條件,以及網絡人文素養、透明民主程度等柔性條件。生態主體主要是指網絡生產者、監管者、分解傳遞者與消費者等,其中內容生產者主要包括網絡平臺生產者(網絡公司、網站、社交平臺等)、技術生產者(網絡協議、技術設置等IT技術人員、科學家等)、內容生產者(虛擬社團、大V、網紅、網絡寫手等)。監管者主要包括網絡管理人員、媒體工作人員、輿情監控人員等。分解傳遞者主要是指粉絲、轉發者等,而消費者主要是指廣大普通網民。從整體上來說,在網絡生態系統中,各個生態氣候、生態環境以及生態主體之間存在著直接或間接聯系,復雜的社會現實情況是影響著整個網絡生態的生存、發展與傳播的前提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網絡生態環境與網絡生態因子的形成、擴張與分布,而生態環境與生態因子之間通過能量流、物質流、信息流、資源流等進行各種要素分子的交換、傳遞與轉換,從而形成聯系緊密、協調運作的動態發展系統,形成具有共融共享、包容聯動的有機體系。
2 中國清朗網絡生態內容培育
在網絡生態系統中,外部生態氣候與環境主要是網絡外化物質基礎與載體,要打造清朗的網絡生態首要的是要有一個健康良好的網絡內容。網絡內容是活水,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網絡內容是網絡氣候、網絡生態環境與生態主體之間的各種能量、信息、要素、資源與物質之間的交流與傳遞的最根本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各個要素都是在具體的網絡內容參與表達實踐活動中得以實現。因此,對于網絡內容的建設與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網絡生態系統的績效。對此,國內外學者做了許多探討研究工作,在國內,喻國明提出應在尊重網絡傳播生態的復雜性、保護多樣性的基礎上,加強網絡內容生產的規制構建與治理邏輯[15]。有些學者則從更廣闊的視角來審視網絡文化的發展。譬如,張靖宜運用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構建了利于我國先進網絡文化建設新途徑[16]。楊文華等研究認為網絡成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發展新的生態環境,二者相互作用,構成統一的網絡意識形態系統[17]。吉樂則認為應該進行全面、深入的文化素養教育,從源頭為我國的文化生態系統注入新的活力[18]。在國外,Kolko運用“界面理論”(interface theory)提出通過技術、協議等規制將人類、文化和數字之間復雜的交互和界面聯系起來,形成具有文化差異、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標準和設計[19]。可見,網絡生態系統不是僅通過改善某一系統、環節或要素就能從根本上改善整體生態,應綜合地具體地考察其內在秩序、形態體系,正確客觀地把握與遵循其規律。同時,要抓住其重點環節、吃透難點生態位,就整個網絡生態來說,其治理的中心環節就是網絡內容,因為網絡內容是網絡生態各個環節要素以及主體共同生成、傳播的場域,是宏觀、中觀與微觀網絡生態各子系統、環境要素以及網絡主體集體演繹的結果,如圖2所示。其中,對于網絡內容而言,其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現實社會情況,技術平臺等硬件條件,輿論人文環境以及管理制度機制等。內部因素主要是網絡生態主體,譬如政府、網絡公司、媒體行業協會、網絡社群、網絡達人和廣大網民等,網絡內外因素通過網絡內容的實踐活動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當前網絡中存在著高品質網絡內容供不應求,低俗化網絡內容大行其道等困局,這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存在著不平衡,因此,應整合傳播學、文化學、符號學、信息學等多學科領域與交叉視角,對網絡生態內容體系進行創新,主要從以下幾個層面著力建設,主要包括:
第一,加強網絡傳播生態氣候頂層設計。從制度性構架視角,審視中國特色清朗網絡空間傳播生態治理的政策供給側機制,需要提出具有聯動性、整體性、前瞻性、科學性的建設機制構架。近幾年來,國家在網絡空間治理上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諸如《微信十務》《網絡游戲管理意見》等,在開展諸如打擊網絡犯罪等專項治理活動的同時,也開展了青年好網民、職工好網民等中國好網民積極正向引導系列活動,網絡生態取得了很大改善。在此基礎上,應加強國家戰略、產業布局規劃、對外交流合作等多層面、多領域的一攬子政策機制建構,注重不同政策制度之間的配套銜接,注重國際視野、國家戰略與本土化操作的有機結合,注重社會經濟與人文價值的有機統一。對網絡生態建設實施以互利共贏為導向的政策關照的同時,健全經濟性規制與社會性規制相結合、支持性政策和限制性法制相結合的協同優化治理體系。要加強構建中國特色網絡生態治理矩陣,規范網絡管理制度建設,暢通網絡不端違法舉報渠道,尤其是對危及國家文化安全、侵權盜版、內容低俗等進行監管整治,使中國網絡生態實現良性科學的動態發展。
第二,建立建全網絡生態內容規制。注重網絡結構、要素、內容的協調發展,有針對地對當前網絡內容診斷出的問題與不足,提出網絡分級分類規制、網絡平臺融合、優質文化內容供給、泛傳播功能整合以及傳播致效評估等網絡生態內容建設方案。有學者認為當前網絡內容主要可分為正生態、負生態與融生態[20]。對于不同的網絡生態內容應根據其性質與類型有區分地加以建設管理。其中對于積極向上的網絡生態內容應加強中國優秀網絡文化建設,培育網絡正生態文化產品,打造網絡文化精品,加強網絡文化產業化建設,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網絡內容生態的主題、話語與傳播體系。應加大網絡主流價值文化的供給,加強主流媒體網絡化融合,培育網絡亞文化和網絡文化共同體。應加強網絡風清氣朗內容的供給,尤其是加強提供與網民息息相關的網絡民生套餐,即包括學習、生活、工作、情感、健康、休閑等多維度多領域的網絡公共文化服務,打造親民、切實解民、貼近民生的網絡內容供給,讓廣大網民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營造弘揚主旋律、激發人民的奮發向上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網絡氛圍。不可置否的是,當前網絡中存在著一定的低劣媚俗的內容,對于這些網絡負生態要加強阻斷與消融,加強信息污染、網絡謠言、低俗網絡業態管理治理等。在優質網絡內容的提供、低劣網絡內容的治理同時,通過網絡協議、議程設置、把關人、危機管理、潛網等環節設計,來規范網絡內容的發布與傳播。此外,對不同級層的網絡生態內容應進行有針對性地分類治理,對于低端網絡內容工作重點應著力放在對網絡低俗內容整治和網民素養的提升上,對于中端網絡內容的工作重點應主要集中對意見領袖等網絡達人網絡社會責任與言論議程設置的安排上,而對于高端網絡層級來講,則應側重于優質網絡內容的提供及其產業化發展,從而帶動整體網絡生態的向上流動。
第三,提升網絡生態主體能力。網絡生態的歸根到底是網絡主體通過網絡參與,調動自身及其周圍網絡要素的社會實踐活動。由于不同的網絡生態主體所處的具體生態位,所掌握的網絡生態資源、要素、能量等各不相同,以及自身參與能力、素養程度也不盡相同,構成了網絡生態主體的差異化與復雜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網絡生態的和諧穩定。對于此,有學者認為要構建高質量的網絡生態文明就應建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模式,提升網絡生態文明主體的綜合素養[21]。但我們要看到,在當前網絡發展不成熟的情況下,在發展多元主體的作用時,更應凸顯各級政府在網絡生態建設中的主導擔當作用,媒體網站作為網絡生態內容建設先行者的引領作用。對不同的網絡生態主體,包括生產者、監管者、分解傳遞者以及消費者進行專項網絡素養提升教育,特別是要將內容生產者與消費者“兩頭吃透”,網絡公司、網絡社交平臺以及網絡達人可能同時扮演多重網絡主體身份,但其作為生產者決定網絡信息源頭的質量,而廣大網民作為網絡生態系統的神經末梢,不僅直接進行網絡消費,其參與、再傳播以及反饋情況也影響著網絡內容生態的微循環,其不良行為甚至可能引發網絡謠言、人肉搜索以及網絡輿情危機傳播等,因此,應加強網絡生態主體的網絡素養教育,提升網絡主體網絡參與表達、甄辨評估信息、信息傳播分享以及創造創新的能力。
3 中國清朗網絡生態運行機制構建
對于網絡生態體系來講,除了建立健全的機制體系、打造清朗網絡內容外,還要有良性的運行保障機制。邵培仁就倡導運用媒介生態學理論,將整體優化、適度調控、良性循環等理念和綠色生態鏈理論應用于網絡生態的優化治理[22]。高元龍等從網絡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高度提出以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交往原則促進中國特色網絡生態文明轉
型[23]。本文認為加強網絡生態治理體系范式構建與改善網絡內容建設的同時,還應建構網絡生態系統協同運行機制。只有注重生態體系運轉機制的建立,才能讓各個級別層面以及整個網絡生態形成良性有序運行。因此。基本協同管理理念,提出中國網絡生態治理的運行機制框架:
第一,在結構層面上嵌入協同生態鏈。有學者認為網絡信息生態鏈是指在社會網絡信息傳播、共享的過程中,多種社會網絡信息角色同多種社會網絡信息環境相互作用而構成的鏈式依存結構[24]。網絡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各種成分要素在一定時空上配置與變化的基本構架。各個國家與地區因其國情與網絡發展狀況的不同,在結構、功能以及作用等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就中國而言,從結構上來講,網絡生態是垂直性結構和水平性結構的融合體,其既有現實社會科層制管理與網絡技術縱向設計協議框架的體現,也有網絡扁平化傳播特質。因此,基于這一現實應將整個網絡生態劃分為不同的生態級層,應對不同網絡生態級層進行有針對性的規劃,進行分級分層管理,對于不同的網絡生態級層再根據網絡內容的類別或突出問題進行集中治理,達到點、線、面、體的分治與集中治理的統一,從而形成多力驅動、互利共生、價值增值的動態平衡競爭網絡生態鏈結構。
第二,在功能層面上導入全程化協同價值功能。作為一個動態發展的組織系統網絡生態是一個不斷解構與再構的過程。生態系統中的各子生態、環境要素之間復雜交互的關系和演變機制,以及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相互磨合的過程中呈現出一定的整體特征和規律性。從功能層面上來說,主要包括技術性功能、信息傳播功能、娛樂功能、社會組織動員功能以及社會認同整合功能。目前許多人只關注到網絡虛擬空間技術的娛樂價值,還剛剛看到它在媒介運營與制度安排的疊加效應所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經濟與人文價值,還沒怎么關注到網絡對社會公眾的文明素養的提升,特別是社會價值與認同的影響作用。因此,對于網絡生態的價值導向,應由現在的泛娛樂的傳播應用轉移到人的全面發展、社會文明進步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綠色生態理念的倫理價值追求上來。讓每個網絡生態構成成分、要素以及主體都得到所需的能量、物質、信息與資源,讓每一個網絡群體與個體都能在網絡系統中找出自我需求、自我尊重和自我實現。在網絡生態系統不同的功能面,應以人文價值關懷為指導充分發揮與調動各個子系統、成分、要素以及主體的資源與積極性,讓它們實現網絡生態信息資源共享、社會認同、文明整合的整體利益最大化。
第三,在過程層面上載入協同管理過程目標。從宏觀上來看,網絡生態系統是自然、社會、網絡與人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從中觀上來看,其是通過信息傳遞、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資源共享而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微觀上來看,網絡生態系統亦可看成網絡生態主體在網絡活動參與過程中與網絡生態內外要素之間不斷進行相互制衡、相互調控、相互博弈的體系。在這一過程中,若沒有任何的規范制度或公共契約精神,整個網絡生態將處于雜亂無章、無序發展和各自為政的局面,這就需要在網絡生態系統中內嵌與外化一系列的技術協議、議程設置以及制度性安排,共同制衡、維系與發展網絡生態系統和諧有序運行發展。目前我國逐步探索建立了法律規范、行政監管、行業自律、技術保障、公眾監督、社會教育相結合的互聯網管理體系[25],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對不同的網絡生態的子生態、子系統、環境要素、生態主體實現協同目標管理,使之形成整體性、連貫性與聯動性。在加強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治理的同時,對于生態系統構成的各個維度、環境與因子都應進行有針對性的統籌規劃與管理,達到各子系統的自治的同時,實現整個網絡生態系統的共治。從而實現網絡生態良性融合與科學發展,形成網絡融合統籌治理創新和智能協同的發展格局。
參考文獻
[1]Jontm,Edwin S E,Kimt.Wide area network ecology.//Proc of the 12th Systems Administration Conference Berkeley,CA: USE-NIX Association,1998:149-158.
[2]Mcfedries P.The Internet ecology[J].IEEE Sepctrum,2003,40(4):68.
[3]張慶鋒.網絡生態論[J].情報資料工作,2000(4):2-4.
[4]李良榮.透視人類社會第四次傳播革命[J].新聞記者,2012(11):3-6.
[5]熊澄宇,呂宇翔,張錚.中國新媒體與傳媒改革[J].清華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1):127-132.
[6]唐緒軍,黃楚新,劉瑞生.移動化新媒體:微傳播改變中國[J].中國報業,2014(13):36-39.
[7]黃意武.網絡文化生態的特征及其建設路徑探究[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1-4.
[8]楊艷斌.網絡媒體的生態文化理性[J].新聞愛好者,2011(11):76-77.
[9]蔡志文,萬力勇.淺論網絡生態危機的表現及其文化之源[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4(1):64-66.
[10]黃明波,沈文鋒.網絡文化生態平衡與網絡傳播倫理規范[J].文化與傳播,2014(6).
[11]劉勝枝.當前我國網絡文化生態的問題、原因及對策研究[J].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30-35.
[12]趙鴻偉.當前我國網絡文化生態問題研究[D].重慶:重慶郵電大學,2016.
[13]邵培仁.論媒介生態系統的構成、規劃與管理[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1-9.
[14]李蓉.傳播學視野中的網絡生態研究[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49-56.
[15]喻國明.把握網絡文化生態的復雜性是搞好內容建設的關鍵[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4):40-42.
[16]張靖宜.現階段我國網絡文化生態問題研究[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13.
[17]楊文華,李韞偉,李鵬昊.網絡生態環境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結構演替及文化轉向[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5(5):16-21.
[18]吉樂.網絡環境下的文化生態素養與意識形態認同教育[J].理論與改革,2015(5):168-171.
[19]Kolko,B.E.:‘Erasing@Race: Going White in the (Inter)face,in B. Kolko, L. Nakamura and G.B. Rodman (eds) Race in Cyberspace,2000,213–32. New York: Routledge.
[20]曾靜平.網絡文化概論[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3.
[21]陶鵬.論網絡生態文明建設[J].生態經濟,2013(10):181-184.
[22]邵培仁.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新視野——媒介作為綠色生態的研究[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135-144.
[23]高元龍,程靜.增強網絡文化軟實力的生態建構方略探析[J].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5):65-67.
[24]馬捷,胡漠,魏傲希.基于系統動力學的社會網絡信息生態鏈運行機制與優化策略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16(4):12-20.
[25]任賢良.推動網絡新媒體形成客觀理性的網絡生態[J].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