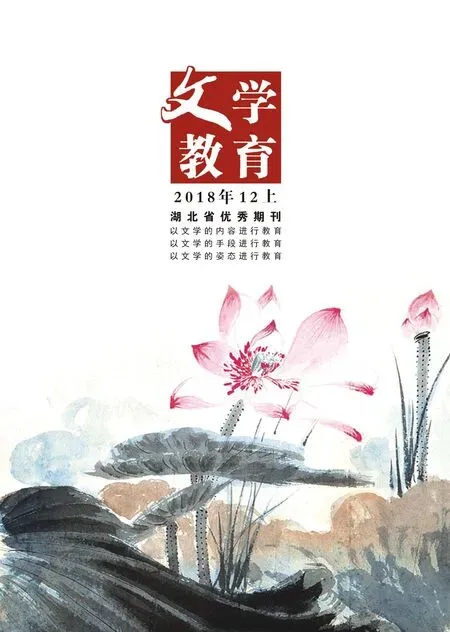論文學經典教學中多元有界策略與運用
聶欣晗
文學經典是實現個體人格完善、民族文化自信提升與國際文化融合三效合一的捷徑,能高效完成大學教育的文化使命。不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西方“后現代”思潮的涌現給傳統文化的生存境遇提出了挑戰,如何應時而變成為經典教學面臨的重要問題。
一.文學經典傳承面臨的困境
文學經典的衰落已是個不爭的事實。或因文化環境改變,或因現代技術發展,或因教學模式的刻板,或因解讀視角的單一,導致遠離經典、遮蔽經典、解構經典甚至反經典傾向甚囂塵上,文學經典傳承陷入多重困境。
傳統經典在時代沖擊下不斷邊緣化。在實用主義盛行的當下,讀者文化心態浮躁,他們的閱讀品位、文化使命感與人文終極關懷跌至冰點,少有人將閱讀經典當作一種境界、精神指向和修養去對待。加之文學經典特定的時代印記與當下時代難免脫節,即便是凝聚文化精華的名著也失去了相當魅力。據相關部門統計,中國近年來家庭戶均年消費圖書不到兩本。據復旦大學調查顯示,大學生閱讀人文社會科學經典的占22.8%。
相吊詭的是,“消費經典”熱潮卻風起云涌。“(消費經典)消解經典文本的深度意義、藝術靈韻以及權威光環,使之轉化為集政治寓義、感官刺激以及商業氣息為一身的平面圖像或搞笑故事,成為大眾消費文化的構件、裝飾與笑料。”[1]一部文學經典本身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基因庫,眾多文化符號均可能成為被消費的對象。廣告、商業、影視劇制作等領域紛紛以經典為題材進行文化消費。僅2005-2011年間,以“四大名著”為基礎產生的相關影視劇就多達20余部,總票房突破15億元。然而,巨大經濟效益的獲得往往是以打碎經典的權威性與神圣性為代價的,大話名著、戲說皇朝、解構正史、制造流行等經典消費對經典的傳承造成損害甚至誤導大眾。影視界惡搞名著成風,電影《大話西游》對原著的顛覆性引起了大話經典的文化熱潮。圖書市場也出現了諸多被改頭換面的名著。如《Q版三國》中桃園三兄弟均配備現代化裝備。“自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三國演義》正在走出象牙塔,在大眾視野中擴大影響,但這種影響是以遠離原典為代價的,從而造成《三國演義》變為我們熟悉的陌生人。”[2]大部分改編的經典都遭遇了這種不幸。
二.多元化闡釋策略的運用
經典傳承面臨的諸多困境,需在經典教學中采用多元化闡釋策略進行化解。高校師生應不拘泥于某種立場、方式與理論,采用多角度、多方式、多視野策略對經典進行解讀,更好傳承經典。
首先,堅持以文本為基礎的多元闡釋。泛政治化傾向的經典闡釋在我國教育體系中被廣泛使用,如解放后對《紅樓夢》、《水滸傳》的批判。這種一元化闡釋思維使教師與學生均囿于一種標準式解釋,以犧牲經典的多元魅力為代價,對我國現行教育影響依然很深。[3]每一部經典都是一個意蘊豐富的認知系統。文本多層次的語言結構系統能提供寬闊的藝術空白,讀者可根據自身的學識結構、審美趣好、人生閱歷來進行個性化解讀,從而實現文本多元闡釋的可能。充分的闡釋空間一直是《紅樓夢》等經典充滿無限魅力的重要因素,即便一個小小情節也意蘊豐富,如林黛玉去世之前所說的“寶玉,你好……”之句,黛玉究竟是想說“寶玉,你好自為之”還是“寶玉,你好狠”,讀者完全可以根據各自情感經驗去填補省略之處,無需強求一致。
第二,闡釋視野多元化。經典的形成與意義闡釋是經典教學的核心問題,可以從哲學、美學、社會學等多維視野中來關照,也可借層出不窮的西方理論視野中討論何為經典、反經典、重構經典等問題,讓中國文學真正融入全球化話語中。教師要以開放的心態,引導學生用多元化理論觀照經典,允許經典解讀中出現多元互諧甚至自相矛盾的現象,從而打開學生的思維空間,開闊他們的理論視野。如花妖狐媚與文士之間的情愛是《聊齋志異》的重要內容,傳統觀點認為在愛情不被承認甚至被扼殺的封建時代,歌頌愛情本身就具有反禮教的積極意義,因此蒲松齡被視為精神啟蒙導師與婦女解放的先鋒。然而,在女性主義者眼中,蒲松齡筆下的愛情女主角都已打上作者強烈的主觀意愿,男女愛情并未獲得平等。有學者甚至認為《聊齋志異》是以男權話語創造出的情愛烏托邦,依然是對以男性為中心的性別秩序的強化。[4]
第三,闡釋載體多樣化。隨著傳播技術的不斷革新,音樂、圖片、影視、誦讀等均各種新技術均可成為經典的闡釋載體。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說:“兩種媒介雜交或交匯的時刻,是發現真理和給人啟示的時刻,由此而產生新的形式。”[5]“百家講壇”的成功與經典闡釋的影像化呈現有直接聯系。影視的直觀性、灌輸性使觀眾可以用最輕松的方式來接受經典,影視化傳播已成為讀圖時代文學經典最廣泛的傳播方式。在以經典為核心催生出眾多文化產品的今天,我們要盡量借助先進的當代文化產品、利用信息技術的教育潛能、設計在線教育平臺、提供大量的電子文化資源與鏈接,建構多樣化經典傳承的鏈接。
第四,多元互動式教學過程。教學就是一場場對話,師生均為對話主體,而教師是經典傳承的把關人,因為擁有豐富的閱讀經驗而處于經典闡釋的制高點,教師需要設計適當的話題、創造合適情境,引導學生展開討論。大學文學經典教學不能停留在繁瑣的解釋、唯一的答案上,也不僅是知識的獲得、儲存,甚至不在于是否能達成統一意見,而是讓師生在自主思考中發現經典的豐富意蘊,又在互動中建構意義。如在導讀《紅樓夢》時設計一問題:“劉姥姥為何三進大觀園?”學生盡可以就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節發展、小說結構理論等方面對這一問題做出各自探究[6]。
三.多元闡釋須有界
經典闡釋需在作品文本內涵、作者創造意圖、讀者閱讀領悟三者中尋找最佳的平衡點,這是闡釋的邊界。隨著闡釋者的作用被無限放大,出現了打破經典的神圣性、拆分經典的完整性、消解經典的深層意義等另一極端趨勢。兩種做法均沒能形成和諧闡釋,如何闡釋多元有界成為經典教學的另一問題。
其一,抵制偽經典。“經典”一詞在中國文化史上引起讀者第一反應的大多是神圣感,因為經典是人類精神高地,能為我們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營養。然而近20年來,傳統經典走下神壇,文學經典庫經歷重新洗牌,許多出版者和讀者在解構經典、反經典的潮流中逆勢而上,炮制出許多華而不實的“傳世之作”。真正的經典是可以對人類文明實現促進、對人類智能予以開啟、對現實存在與終極指向體現雙重關懷。
其二,個性化闡釋要適度,避免過度片面化甚至有意誤讀。“百家講壇”節目的火熱,掀起了一股個性化講解經典的熱潮。但尊重個性化、差異化解讀的同時,還要堅持闡釋的正確性與深刻性,尊重經典的審美價值與教育意義,闡釋者的意義重構不可臆斷。如解讀《荷塘月色》為“意淫說”就走入個性化誤區。“文學作品的多義性只是相對的,它不可能脫離本民族的文化歷史,不可能跳出文人和讀者認可的內涵范圍。”[7]有學者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影響甚大的于丹“不學而術”,“她的‘愚樂經典’對中國文化精神傷害更大,更容易對普通觀眾產生以假亂真的文化誤導。”[8]進行文化教育的專家學者闡釋經典需慎重思慮文化影響。
其三,消費經典要適度,警惕過分俗化、實用化乃至消解經典的傾向。經典的傳承與消費是一對矛盾統一體,這是經典必須面臨的悖論式命運。作為消費品形式出現的經典必然走向通俗化,但通俗不等于庸俗、低俗。當代大學彌漫著反智論氛圍,閱讀經典這樣重要的大學求知活動越來越邊緣化。經典原著閱讀所需要的痛苦思考與慢閱讀的節奏讓許多讀者望而卻步。即便接觸經典,也常以影視、電游、心靈雞湯式或實用化出版物代替原著閱讀。電影《大話西游》開創了解構、重構經典名著的先河,《悟空傳》、《沙僧日記》、《八戒日記》等消解經典的圖書應運而出。《文學名著精縮》這類快餐式讀本也大受市場尤其是年輕讀者歡迎。殊不知,只有痛苦的思考才來帶來深刻的閱讀體驗,積淀成讀者的生命能量。而養成了惰性接受慣性的讀者在創造力與創新思維方面得不到深度挖掘,精神智慧的增長也就相對有限,甚至“解構經典”也是一種奢求。
其四,運用西方理論要適度。新時期以來,運用西方各種文藝理論來解讀中國文學經典成為新趨向,形成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的共生效應。那些反傳統經典的理論,如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的觀點紛紛運用于傳統經典的闡釋中。對這些理論,我們既要有拿來的勇氣,也要學會主動選擇與舍棄。完美的文學理論是不可能存在的。西方各種理論均有自身的缺陷,如接受理論竭力抬高讀者接受的地位,結果還是選擇回歸文本,客觀上說明文本是放逐不了的,這算是接受理論的“死穴”。同時,理論的適應度也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要盡量避免因對西方理論和中國文學作品的雙重“誤讀”而產生偏差,或者淪為替西方理論尋找中國例證的窘境。如美國漢學界利用性別理論突破了“壓迫——解放”的中國婦女史研究舊有模式,得出許多有別于傳統女性文化的認知。不過,筆者覺得需要更精準把握合適度。魯迅早就說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9]正視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和互補,揚長避短才是中國文化特色發展的上上之選。
在經典教學中采用多元有界的闡釋策略,既闡釋經典內超時空的審美、道德價值,又關注當下對經典的解構與建構所帶來的沖擊與改變,帶給大學生有關經典內核與存在本質的思考空間,才能讓經典真正走進大學生的心靈與生活,經典才能真正參與到新的文化建構體系中來,讓我們的文化變得更豐富、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