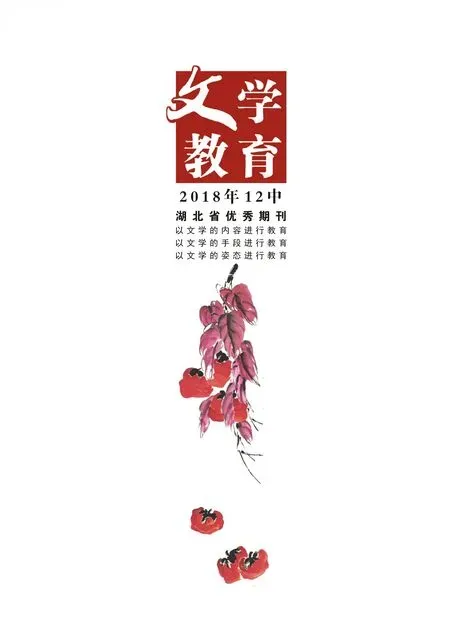邢福義先生語法研究的樸學特性
王 耿
邢福義先生的語法研究浸潤著濃厚的樸學學風,具體表現為:事實考察的全面性;思維程序的邏輯性;研究方法的實證性;所得結論的簡明性;思想內涵的人文性;語言風格的樸實性;學術視野的包容性。
“樸學”一詞本指上古質樸之學,初見于《漢書·儒林傳》:“(倪)寬有俊才,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明清鼎革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對宋明理學“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空疏學風加以針砭,大力提倡崇實致用的新學風,認為欲經世必先通經,欲通經必先考訂文字音義,于是促成了以小學為基礎的考據學,又稱“樸學”,研究范圍一般包括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訂學等。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樸學視為清學正統,并總結了樸學的十大學風,轉引如下:
(一)凡立一義,必憑證據;(二)選擇證據,以古為尚;(三)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四)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五)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六)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七)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八)辨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九)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體貴樸實簡潔,最忌“言有枝葉”。
梁先生所總結的十條樸學學風既概括了樸學研究的方法,如(一)(二)(三)(五)(九),又說明了學術規范與道德,如(四)(六)(七)(八),還指出了樸學研究的文風,如(十)。
乾嘉時期,樸學進入全盛,19世紀后期,隨著清朝的衰落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沖擊,樸學漸趨式微,最終成為一個歷史概念。然而,樸學學風并沒有消亡,直到現在仍影響著文學、史學、哲學、醫學、藝術等多學科領域,漢語語法研究也不例外。
本文結合樸學的風格特點來闡述邢福義先生樸學風格語法研究的七個特性。
一.事實考察的全面性
“孤證不為定說”是樸學的學風之一,樸學語法學家也強調事實觀察、描寫的充分性和全面性,常常通過擴大語料的范圍來不斷修正規律,由此歸納提煉出的規則也較為周全可靠,黎錦熙先生(1924)曾總結過自己做研究的規則:“例不十、不立法。”在過去技術不發達的時代,研究者往往通過卡片記錄整理語料,這需要扎實的專業訓練和極強的語言敏感性,但當今語料庫技術的發展為語料的搜獲提供了便利。
邢福義先生于1990年購買了“奔騰286”電腦輔助自己的研究,2000年以后開始注重使用語料庫搜集、分析語料。他在研究趨向動詞“起去”一詞時談道:“要特別感謝現代科技,電腦的使用,使筆者有可能對現代和古代的作品進行大幅度的搜索。”語料庫技術的應用為邢先生的大量文章提供了精當、充分的事實證據,比如《“由于”句的語義偏向辨》(2002)、《“起去”的普方古檢視》(2002)、《連詞“為此”論說》(2007)、《“X以上”縱橫談》(2008)等等。
二.思維程序的邏輯性
樸學家在研究音韻、訓詁、校勘、辨偽等學問時運用了科學的邏輯思維方法,他們認為正確的思維首先應當是始終一貫,具有內在的自洽性,凡是前后抵牾,上下相舛,則很難斷定為真。趙華、胡永翔(2008)將清代樸學與實證科學的方法進行了類比,指出樸學家具備嚴格的邏輯推理思維,研究所得結論也有可驗證性。
邢福義先生的語言研究處處滲透著邏輯學思維。早在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邢先生的《邏輯知識及其應用》,后來,邢先生在《現代漢語復句研究》(2001)開篇便運用邏輯方法對以往的復句二分法進行了檢視,并獨樹一幟地根據復句語義提出了復句三分法,這種分類方法對廓清復雜的復句語義有重要作用。在對于具體復句句式的研究中,邢先生也注重使用邏輯方法,比如《試論“A,否則B”句式》(1983)、《“但”類詞對幾種復句的轉化作用》(1983)、《現代漢語的“要么p,要么q”》(1987)等大量研究復句的文章都體現出對復合命題邏輯分析方法的運用。俄羅斯國際刊物《語言研究問題》2010年第2期譯介邢先生的論文《復句格式對復句語義關系的反制約》時,稱其為“漢語邏輯語法學派奠基人”。
三.研究方法的實證性
“樸學”又稱“實學”,以“注重實證”為學術特征,清代樸學是對宋明理學好談性理、束書不觀風氣的糾偏,因而樸學家提倡無證不言,論必有據。樸學中的證據,就是古代文獻,如錢大昕的“古無輕唇音”的觀點,就是從《尚書》《詩經》《呂氏春秋》《周禮》等先秦古籍中征引多條例證得出的論斷。
自1994年以來,邢福義先生以“事實”為題的論文有八篇之多,他在《講實據、求實證》(2007)一文中指出:“事實勝于雄辯,不管是討論能不能說的問題,還是討論詞類歸屬、結構性質和歷史演變等等方面的問題,都需要以事實為依據,進行令人信服的求證。”在實事求是、講求實證的學風指引下,邢先生發現了許多前人研究中的問題,并作出了更為可靠的結論。比如關于復合趨向動詞的研究,差不多所有的現代漢語教材都認為可以說“起來”,但不能說“起去”,邢先生考察了普通話、方言、古代漢語中大量語料后認為“起去”的說法成立,而且他還進一步指出“話語場景的條件共容、語義關系的句管控、勻整系統的總體趨同”是“起去”一詞成立的條件。
四.所得結論的簡明性
清代樸學“考據”的目的是對古代典籍進行校勘、辨偽、輯佚,通過文字訓詁來去除宋明理學對經典的穿鑿附會,從而還原經典本義,因此樸學家必須將典籍中文字的意義、詞句蘊含的道理以及科學的音韻規律說明白、講清楚。林文锜(1989)也認為樸學家“主要是靠資料說話,間下斷語和己意,往往寥寥數言,畫龍點睛,便能說清問題”。
樸學風格語法研究繼承了簡明性這一優點,邢先生(2017)在談學風和文風時提出了“文章九字訣”——“看得懂、信得過、用得上”,其中“看得懂”要求文章作者心里要有讀者,所寫的文章要讓讀者讀起來感到通暢易懂。為了讓讀者“看得懂”,邢先生十分注重提煉文章的語言及結論觀點,使之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簡明性。舉一個語言教學的例子。樸學風格語法研究提倡的“歸總性”解釋就事論事,規避了語法理論的闡發,便于語言學習者接受。比如《發展漢語·中級綜合(Ⅱ)》第5課《再平凡也可以活成一座豐碑》中有一句話:“吳慶恒老人生前都想不到的是,他去世10年后,又回到了鳥兒們的中間。”留學生對句子里的“生前”感到困惑,他們按照“死前”將“生前”誤解為“出生之前”。邢先生(2003)對“生前”一詞作過研究,他指出“‘生前’包括活著的所有時間,‘死前’可以只指臨近死亡的極短時刻”。我們認為這一論斷不僅解釋了“生前”的意義,還比較了“生前”和“死前”的異同,在教學中已經足夠。另外,邢先生還指出了“生前”的使用范圍:表示對死者的尊重,不能用于動物。如果再將這一解釋告訴給學生,“生前”一詞的教學就比較完滿了。
五.思想內涵的人文性
樸學承載了豐厚的文化內涵:首先,浩如煙海的古代經典是幾千年中華文明的結晶;其次,為了解讀歷史久遠、內涵豐厚的經典文獻,樸學家必然會推本溯源,對文字、音韻、訓詁進行研究,而語音的流變、文字的理據以及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與文化息息相關。因此,從文化角度解讀漢語自然也成了樸學風格語法研究的旨趣之一,學者們在探尋語言客觀規律時也很重視發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對于語言現象的考察,樸學語法家一般采用“聚焦法”——語表、語里、語值齊頭并進,共同指向研究對象。語表、語里的驗證揭示語法規則,語值的探究則能發掘語言現象中蘊藏的文化內涵。
邢福義先生(1991)在其主編的《文化語言學》的序言中說:“語言是文化的符號,文化是語言的管軌,……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是語言學研究特別是中國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傳統,語言中的許多現象,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比如他曾結合前人研究對“三羊開泰”一詞做了解釋:“‘三羊’怎么會跟‘開泰’聯系起來呢?原來,‘羊’由‘陽’演變而來。《易》中泰卦,下為三陽,表示陰消陽長,冬去春來。‘三羊開泰’本來是‘三陽開泰’,利用同音關系,把‘陽’變換為‘羊’,可以增強言辭的語用價值。年歷上,賀年片上,工藝品上,三羊組畫,比‘三陽’更具體,更形象,更有動感,因而更具感染力。”結合文化學對語言現象進行解釋是邢先生文章的一大特點,品讀先生的文章,常常會感受到其中涌動著的濃厚的文化韻味及人文關懷。
六.語言風格的樸實性
“文體貴樸實簡潔,最忌言有枝葉”是樸學的學風之一,注重條理且不尚雕飾是清代樸學家所普遍共守的為文之道。林文锜(1989)曾討論過清代樸學家的語言特色,他認為樸學學者“治學提倡實事求是、重實證、不尚虛論,影響到文風上,也就形成了簡明有法、不尚華彩的特色……簡約素凈這一特色可以說是樸學家語言風格的基調或底色。”
邢福義先生闡述問題時的“元語言”也質樸平實、深入淺出,鮮有術語的堆砌,其文風與呂叔湘先生一脈相承。邢先生認為“理論越精辟,話語越簡短”,其文章最后一部分往往是一個簡短的“結束語”,用寥寥數語把整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展示出來,極見語言之功力。例如邢先生的《漢語復句格式對復句語義關系的反制約》(1991)一文最后闡明了復句中形式和語義的關系:“在具有二重性的復句語義關系里,客觀實際是基礎,提供構成語義關系的素材,主觀視點是指針,決定對語義關系的抉擇。”這句簡短的總結性話語貫穿了邢先生的整個復句研究,揭示出復句的形式、語義、邏輯、客觀實際、主觀判斷之間的復雜關系,是其復句研究的靈魂所在。像這樣精辟的論斷在邢先生的文章里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舉例。
七.學術視野的包容性
隨著西學東漸的沖擊,晚晴樸學家積極引進西學,嘗試用西方學術理論詮釋經典,強調“會通中西”。安樹斌(2005)在《晚清樸學流變研究》中指出“清末樸學家注重中西結合,但往往‘以國學囊括西學’,即以中學比附西學。而且樸學家從通經致用出發,力求貫通中西政治思想,服務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探索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張允熠(2007)也指出“實證的考據方法,內藏著一種跟西學會通的接應點”。
如果說晚清樸學與西學的會通是在當時社會、政治的巨大危機下被迫做出的選擇,那么新時期樸學風格語法研究在面對西方理論時則顯得更加主動,既包容又自信。
關于引進國外理論,邢先生(1991)明確指出:“國外理論的引進和吸收,對促進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深入開展無疑具有極大的意義。”當然,國外理論的引進需要接受漢語事實的檢驗,做到理論和事實的有機結合。邢先生(1991)更傾向于這類研究:“根據自己語言的特點,不排除接受國外理論的啟示,總結出一套自己的理論”。后來,邢先生(2005)進一步闡述了“引進提高”和“自強自立”的關系,他指出“引進提高”只是一種發展途徑,“自強自立”則是一種原則立場,“引進提高”和“自強自立”應相互補足,相互促進,形成良性循環,我們的語言學科才能夠真正發展起來。此外,樸學風格語法研究的包容性還體現在邢先生對“學派意識”的倡導。正是由于邢先生的寬容和包容,其諸多弟子的研究視野超越了“普—方—古”大三角,在話語分析、生成語法、兒童語言學、語言翻譯、中文信息處理、語言規劃等多個領域取得了豐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