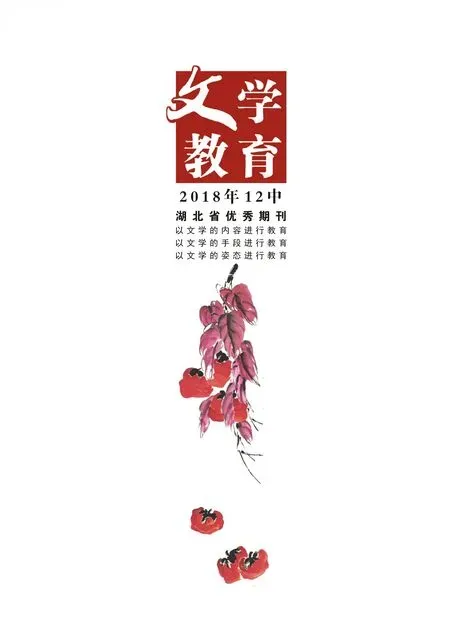百年新詩再出發的現代性之路
王鉆清
“現代性”這個概念的解釋多樣紛繁又與時俱“變”。我認為,“現代性”不僅是相對的時間概念和時間幻覺,而且是一種由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現代”結構所支撐的人類存在方式。換句話來說,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或后工業文明的特征,是對時代進行“批評性質詢”的品格,是面向未來的一項“未完成的設計”。
那么,我們用這種眼光來看看百年新詩的現代性。漢語新詩是漢語詩歌史中所誕生的一種劃時代的詩歌美學類型,它是否完成了這個新詩時代?事實上是沒有——因為新詩現代性的路還沒有走完。從審美機制和藝術規律來看,新詩不完全等于現代詩——現代詩在文體上具有現代元素和創新基因,在內容上建構現代意義世界,許多新詩不具備這些特質。
“現代詩”與“新詩”在誕生和所跨越的時代上,有一個時間劃分:比如在內地詩歌史上,自五四以來,“朦朧詩”誕生以前,這一時段出現的詩歌屬于“新詩”,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翻譯體”使新詩現代性重獲新生,當時“詩人譯詩”和翻譯家寫詩在新詩的發展和語言的變革中扮演著“先鋒”的重要角色,新詩的“現代性”視野、品格和技藝已成為新詩“現代性”藝術實踐的一部分。在“朦朧詩”出現以后,則屬“新詩”與“現代詩”混居的時段。依“現代詩”的第一次真正被中國詩人以較為自覺、準確、明晰、系統的語言來界定,始于1950年代的境外詩人紀弦。后來連現代詩倡導者那批人也沒有堅持下來,新人中有一些現代詩作者,但總體情況仍是“現代詩”與“新詩”混居。
百年新詩再出發,現代性的路如何走呢?我以為,盡管百年新詩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詩歌文本與詩學理論,似乎構成了再出發的基礎;但是姍姍來遲的漢語現代詩,不過是遵循把關注的眼光投向時代巨變下人們的處境、情感以及對人類文明流向的關切這一大趨勢而已;所以從這個向度上講,新詩與現代詩,雖不涉及“好詩和壞詩的判定”,卻更多地涉及到了“是與否的判定”——或者說新詩的合法性問題。
事實上,百年新詩沒有取得合法性地位,所有新詩實驗都是失敗的,并沒有形成新詩傳統;進入新世紀以來,漢語新詩還在“原地踏步”,而且在全民寫詩的潮流中泥沙俱下,在某些職業性寫作當中越寫越離譜(那些作品失去了詩歌精神和自身特質,也缺乏真實情感),在主導推動下“后繼有人”卻新人走老路;比如,90后的詩呈現這樣的情狀:跟著“引導者”(文學刊物和流行趨勢等)走,跟著現今的主流走,形式上是老一套,內容無新東西,語言規范一點卻無新鮮感和異質性,讓讀者感受不到現代青年的那種精神氣質(包括青春的狂氣和沖動)和個性自由(對理想的狂熱,對真理的追求、對自我的完成)等新青年的特征,缺乏獨創性、清新感、批判性等。我們知道,個人自由是現代社會的時代特征。時代賦予我們的現代性本該在詩歌中體現。
中國新詩還要走第二個百年嗎?如何走?對百年新詩是“推倒重來”——即從新詩的多種可能性中提取有益的因素,重建漢語詩歌的新類型;還是承接或延續或革新百年新詩所形成的詩歌機制和詩學實踐經驗,完成或完善新詩既定的類型?或是構建全新的詩學機制,并創造詩歌劃時代的類型?看來新詩現代性的路還有很遠,遠到新詩自然消亡或新生。那么,新詩現代性的路途當中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呢?
——語言仍是最大的問題。我們在今天是否依然需要不斷拓展和刷新我們的語言,是否依然需要保持詩歌的異質性和陌生化力量?回答是我們必需。我們知道,詩歌是詞匯的更新。好的作品是語言的更新。一個詩人要擺脫種種“文化的幻覺”和因襲,最終要抵達的“語言的荒野”;那么,我們現代詩要“橫向學習”,即學習外國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以及現代文學,同時“縱向吸取”營養,即極力發掘漢語的潛能和特性。現代性與自我(個人的存在價值、個性自由、良知發現等)的關系在現代化語境當中會激發并生成新的語言系統;或者說,自我可能引發詩和語言在現代性中的撞擊以及自由表達的欲望,我們要善于提煉。
——文體的革新仍是關鍵的問題。事實上,新詩在形式上并無多大的突破性進展,在語言結構上也沒有多少創新性潛在因素可應用;那么,可以說,與其對新詩講形式,不如對新詩講文體。從寫作的內在情形看,有沒有文體感遠比有沒有形式感更迫切。當代詩的一個大問題是,大多數詩人沒能在文體意識和形式意識方面做出更細致的區分。
——格律的問題仍是不可忽略的問題。詩歌的“機制”是它的韻律和格律。現代詩的顯著特質應是有現代格律,那么就應通過新的嘗試建構完美的詩歌結構,在詩的形式設計上有所突破;因為詩之形式是被音韻和節奏所控制的新的寫作方式的語言運動體,進而讓詩歌的魅力在捕捉詩性的感覺、引爆內在的詩情、觸摸獨立的詩思當中構建新美的詩歌結構,生成優質的語感和韻律。為此,我們可以從中國古典詩歌中吸取有益于新詩成長的元素,比如呈現畫面感的意境和增強音樂性的押韻等,還有必要學習漢語音韻學。
——發現隱藏在知識與理解之間的東西。荷蘭藝術家阿曼多曾說:“漸漸我明白了,不應該去創作那些已經知道的東西,而是應該創作那些隱藏在知識與理解之間的東西!”所以,我們說,生命的沖動與精神的決斷究竟和漢語詩歌有什么關系?這么說吧,小詩人更沉溺于有沒有寫出生命的沖動,大詩人更專注于有沒有寫出精神的決斷。所以,說到底,這是一個境界的問題。那么,我們要有一個智性的審視世界的眼光。從某種意義說,審美現代性有三幅面孔:啟蒙審美現代性、先鋒審美現代性、市民審美現代性。從這些方面來看,新詩現代性就可以理解了。例如,本人創作的長詩《未來啟示錄》用“未來之眼”透視“遠方的門”和“時空之門”,將科學主義和未來學等人文精神融入幻性又理性、詩性又人性的詩中,以獨特的視角審視世道人心和批判抽象現實,并且詩意地、科幻的、自由地入門未知的大自然,讓宇宙星空成為一個人的心靈投影。
我一直在想:漢語新詩現代性的路,如何走好呢?其實新詩本土化或世界性跟現代性是共生的,只要我們面向世界和未來。所以,我以積極、開放的姿態尋找現代詩新的可能。我在廣博地閱讀和大量地寫作中不斷地完善自身的文本意識,通過多年寫作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讓自己的語感在詩歌中自然地呈現,并努力在創造文本的道路上寫詩。我堅信,文學是創造性的言說方式,是不斷更新的語言藝術。所以,我始終在文學范疇內創作,圍繞探尋和對抗這一詩歌的核心寫詩;通過書寫人類精神與宇宙精神交織及碰撞的狀況,或者說以宇宙大發現(即天體運行觀測和宇宙探測等科技前沿成果)的詩思、詩意的時空幻性或時間幻覺,來傳達一種詩性的哲思;同時我還不受傳統的束縛,在詩藝上進行了一些試驗——把極具體的細節和極高遠的玄思結合起來,把細微的與宏大的事物詩性地連結在一起,把新發現或新概念或新感覺通過修辭作用與詩性感覺整合成“實驗性意象”。比如:《太陽灼燒的人心》
人力車拖著過去的趣味曬太陽
數百馬力的蒸汽機同時碾過心路
而電力跟心力同行向著太陽風暴
折向人心黑暗又寒冷處放射幽光
當時間扭曲空間時我們在星際旅行
感受到電磁力的排斥跟吸引在交鋒
強核力將原子中的質子和中子束縛
隨著恒星燃燒的自然力火光沖天
當弱核力造成原子核或自由中子衰變時
我們隨同裂變的粒子穿透未來幻影
然后我們的靈魂伴隨重力自由下落
萬有引力將萬物定律在相互吸引的場內
瞧那夜空劃過一道奇異的光束
載有骨灰盒的追悼飛船進入軌道
環繞地球飛行跟家園不離不棄
可兩年后這飛船回到地球大氣層
最終跟“流星雨”一樣燃燒殆盡
而人的靈魂是否升空進入了天堂
當粒子的飛揚穿透接近光速時
時空以幻覺的形態劇烈壓縮
那一維“弦”振動出基本粒子
四維時空在量子糾緾中變幻宇宙
于是太陽探測器帶著人心發射升空
直入云霄 追逐太陽帽沿的火眼金睛
耐住太陽日冕層比太陽表層還高的熱力
繞著這恒星大氣層觸摸心中最紅的太陽
此刻航天器正抵抗地球太陽之間的引力
還借用金星的引力拼命地接近太陽
直面太陽風去揭開太陽的神秘面紗
讓太陽磁場和高能粒子服從人心
讓世人擁有太陽能跟陽光一樣輕便
然而時間幻想和空間幻覺交媾成癮
當無用階級哭泣時太陽照常升起
當洪荒回歸時所有星系照常運轉
我嘗試創作“大時空詩”,將后現代主義哲學和現代詩學等融合起來,在“大時空”與人類抽象現實的描述以及詩性表達、詩藝探索等方面不斷探索,真正的創新意味著運用你的想象力,發揮你的潛力,創造新的可能性。我就這樣,在自己的寫作中,在未來設計的時空壓縮與時代嬗變的文化反芻中,一邊建立自己與時間幻想、空間探測、抽象現實、人類未來等相關的題材體系——將地表人、外星人、地球、月球、太陽、火星、星系、太空、外太空等作為描寫對象,把光年、光速、量子、粒子、中子、微中子等當作詩歌的“大數據”;一邊建立與“大時空”、人類性、現代性等諸多因子緊密聯系且富有個性的語言體系——科幻的、詩性的、哲思的、神性的、靈異的、奇幻的、混沌的語言體系,即以哲學思維穿越星球之間,以科學幻想審視多個宇宙,以詩性的感覺創造幻性大時空,力求呈現別樣的趣味,構成顯而易見的一套完整的由科幻新感覺、轉喻新概念、眾多新意象組成的前后連貫的體系。
我深知,藝術,你若定義它,就縮小了它的范圍。現代藝術最大的價值是獨立。藝術家憑自信和獨立表達人的意志和情感。其實,藝術是人的介入,人之精、氣、神的介入;最好的藝術作品是前無古人的。藝術需要創造力,而創造力需要經驗,更畏懼經驗。天才,可以說你觸及天,天就賦予你的才;諸如第一個創造電燈、第一個創造飛機、第一個創造電腦的人,或許在當初他們被稱為“瘋子”。藝術也一樣,需要全力觸探那個未知的世界,觸碰那個真實的自我及自我的潛能。讓我們在蒼穹之下,追求日月之光,讓詩歌的現代性趨向最具創造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