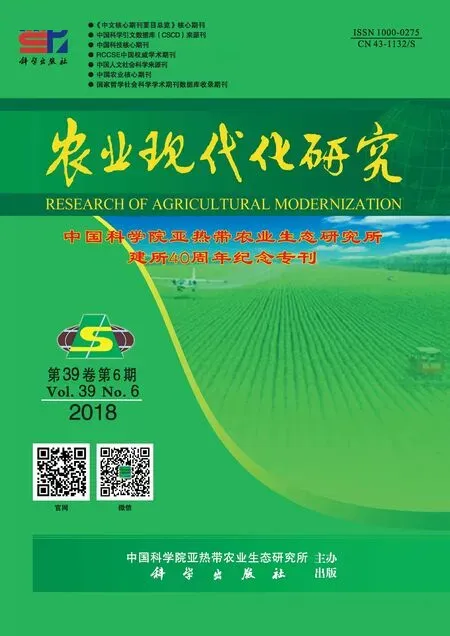西南喀斯特生態系統氮素循環特征及其固碳效應
李德軍,陳浩,肖孔操,張偉,王克林
(1. 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亞熱帶農業生態過程重點實驗室,湖南 長沙 410125;2. 中國科學院環江喀斯特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站,廣西 環江 547100)
氮是構成蛋白質和核酸的物質基礎,因此,一切生命體都需要氮素。然而,由于生物圈中儲存的生物可利用性氮的量非常有限[1],陸地自然生態系統植物的生長普遍受氮素限制[2]。生態系統中的氮絕大部分是以有機化合物的形態存在。由于有機化合物分子中的碳與氮原子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這就決定了生態系統不同組分,如林冠、樹干、凋落物、微生物量及土壤有機質中的碳與氮含量之間存在一定的比例范圍,或化學計量學關系[3]。碳、氮之間的計量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態系統的碳、氮循環密切耦合[3-4]。這一點在全球變化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陸地生態系統固碳被認為是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進而減緩全球變暖的一條經濟而有效的途徑,然而,由于碳、氮循環之間緊密的耦合關系,陸地生態系統固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土壤的供氮能力[5-6]。在氮狀況較好的區域,土壤供氮能力相對較強,生態系統的固碳潛力相對較高;反之,生態系統的固碳潛力則較低[6]。另一方面,由于氮是植物生長的必需元素,也是主要的限制性元素,因此,土壤氮的供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生態恢復的成效[7]。在氮狀況好的區域,土壤氮供應能力較強,植物生長更好,重建的生態系統就更容易或能更快發展到演替的頂級階段;反之,重建的生態系統可能長期停留在演替的早期階段[7]。可見,評估生態系統的氮狀況對預測全球變化背景下生態系統的固碳潛力及生態演替的方向與進程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然而,目前對區域尺度生態系統氮狀況的認識仍非常有限。通常認為溫帶及北方生態系統受氮限制,而熱帶與亞熱帶成熟森林則表現出天然氮飽和特征[8]。然而,這些觀點主要是基于一些間接、零散的證據,而直接與系統性的證據缺乏[9]。
喀斯特生態系統是地表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約占全球陸地面積的10%及我國國土面積的36%[10-11]。我國的喀斯特生態系統尤以西南喀斯特區最為典型,這一區域也是全球三大喀斯特集中連片分布區之一。喀斯特生態系統具有其特殊性,如土壤鈣/鎂含量高、基巖裸露率高、土層淺薄且分布不連續、具有發達的裂隙管道系統等[12]。后二個特征導致喀斯特生態系統非常脆弱,一旦遭到干擾和破壞,水土流失嚴重,進而引發土地退化。事實確實如此,過去由于不合理的人為活動特別是農業耕作,大面積的喀斯特生態系統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退化,甚至石漠化[10]。近20年來,我國在西南喀斯特山區實施了一系列生態恢復工程(如退耕還林還草、石漠化綜合治理等),石漠化擴展趨勢得到了遏制,生態恢復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13]。然而,由于工程實施先行而機理研究滯后,我們至今不清楚喀斯特山區生態恢復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是什么。如前所述,氮是多數陸地自然生態系統植物生長的主要限制元素,也是決定生態恢復成效的關鍵元素,因此,西南喀斯特山區生態恢復工程亟需回答的關鍵科學問題是:氮是否為喀斯特區生態恢復的主要限制性元素?其次,喀斯特生態系統具有一系列的特殊性,其氮狀況與鄰近的非喀斯特生態系統相比有何差異?我們近幾年針對上述問題開展了比較系統的研究,以下將從二方面進行簡要論述。
1 退耕后喀斯特土壤氮狀況隨演替變化特征及其固碳效應
1.1 基于小流域尺度退耕演替序列或不同退耕模式的證據
基于小流域尺度(古周生態恢復示范區和木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退耕后次生演替序列(包括草叢、灌叢、次生林和原生林),以農田作為對照,采用空間代替時間的方法研究了氮狀況隨演替變化特征[7,14]。結果表明,退耕后土壤(表層15 cm)總氮隨演替較快累積,經過70年左右恢復到原生林水平,平均累積速率約為12 g N/(m2·yr)[7]。由于碳-氮循環密切耦合,氮的累積也相應保障了退耕后土壤有機碳隨演替進程快速累積,經過40年左右能恢復到原生林水平,平均累積速率約為138 g C/(m2yr)[15]。我們發現退耕后土壤有機碳和總氮累積遵循以下模式(公式1)[7,15]:

式中:St0和St分別表示退耕前(t0)及退耕后某一時間點(t)土壤碳(或氮)儲量,A表示土壤碳(或氮)儲量在退耕前與達到平衡態之間的差值;B代表增長常數;yrs表示退耕后恢復年限;C表示形態參數。創新性的提出了土壤碳(或氮)儲量達到平衡態所需時間(T,單位為年)的估算方法(公式2)[7,15]:

式中:Sst表示平衡態時土壤碳(或氮)儲量。
土壤總氮快速累積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需要有充足的外源氮輸入。大氣氮沉降與生物固氮是多數陸地自然生態系統外源氮輸入的二條主要途徑[16]。我們發現這二條途徑僅能解釋土壤氮累積速率的40%~76%[7]。進一步分析發現基巖中含有一定量的氮,在基巖快速風化溶蝕過程中,巖石中的氮釋放到土壤中,進而被土壤直接固定或被植物吸收后隨凋落物進入土壤并成為土壤總氮組分[7]。上述三個氮源可解釋土壤氮累積速率的40%~102%[7]。可見,巖石氮釋放是解釋喀斯特山區退耕后土壤總氮累積的一條重要機制[7]。Houlton等[17]基于全球表層巖石的分析也表明西南喀斯特山區碳酸鹽巖氮含量相對較高。另有研究則表明西南喀斯特山區巖石的化學風化速率居于全球高水平[18]。較高的氮含量和風化速率無疑是西南喀斯特山區碳酸鹽巖氮釋放速率相對較高的主要原因。
然而,土壤氮的累積是外源氮輸入與不同途徑土壤氮流失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僅有外源氮的輸入并不足以解釋退耕后土壤氮的快速累積[7]。在土壤對氮的截留/固持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外源氮進入土壤后將很快通過不同途徑流失,并不會導致土壤氮的凈累積。因此,退耕后土壤總氮能快速累積意味著喀斯特土壤具有較高的氮固持能力。經過深入分析,我們發現土壤總氮與交換性鈣及鎂含量之間存在非常強的線性關系[7]。由于土壤總氮90%以上為有機氮,因此,我們提出土壤有機質通過鈣鎂離子與礦物表面生成礦物復合體是喀斯特土壤有機質穩定的重要途徑,進而有助于土壤有機氮(或總氮)累積[7]。這也是解釋退耕后隨演替進程土壤總氮快速累積的另一重要機制[7]。
土壤總氮的累積導致土壤中不同形態無機氮含量隨演替進程而發生變化[7]。在草叢階段以銨態氮為主,而在其他階段則以硝態氮為主。土壤中的硝態氮與銨態氮之間的比值是反映土壤氮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比值小于1意味著生態系統缺氮,而大于1則意味著生態系統富氮。基于該指標我們提出在草叢階段缺氮,而其他階段則富氮。土壤15N比值也支持灌叢、次生林和原生林土壤氮循環相比草叢階段更開放[7]。葉片N∶P比值也是反映生態系統氮狀況的一個常用指標,該比值大于16表示植物受磷限制,小于14表示受氮限制,而在二者之間意味著植物受氮和磷同時限制[19]。我們對不同演替階段植物群落葉片N∶P比值的分析表明,草叢階段植物受氮限制,灌叢階段受氮和磷同時限制,而次生林和原生林階段植物受磷限制[14]。此外,土壤初級氮轉化也是評估土壤氮狀況的有效方法。基于氮同位素稀釋法,我們定量了土壤初級氮礦化速率(GNM)、初級硝化速率(GN)、硝態氮異化還原為銨的速率(DNRA)、微生物對銨態氮固持速率(GAI)和微生物對硝態氮固持速率(GNI)。GNM和GN在退耕后早期速率下降,之后隨演替進程而增加;但其他三個過程速率隨演替進程沒有明顯的變化規律。GN∶GAI比值是反映土壤氮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該比值小于1意味著生態系統缺氮,而大于1則意味著生態系統富氮。基于該比值的分析,我們發現草叢階段微生物受氮限制,而后續階段則表現出明顯的氮飽和特征。
進入土壤中的凋落物所含的氮主要為蛋白質類物質,包括蛋白質、幾丁質及肽聚糖等大分子多聚體,其中蛋白質所占的比例最高[20]。對于這些多聚體微生物無法直接利用,必須經過胞外酶的解聚作用變成小分子有機氮后微生物才能利用,進而經過氮轉化過程生成銨態氮和硝態氮[20-21]。這些生成的小分子有機氮、銨態氮和硝態氮均比較容易被植物吸收利用或從土壤中流失。基于此,我們假定二種可能的情景。第一種情景是進入土壤中的凋落物絕大部分經過解聚及初級氮轉化后生成的小分子有機氮、銨態氮和硝態氮,進而被植物吸收或從土壤中流失。在這種情景下,退耕后隨演替進程土壤總氮的累積速率理論上應非常低。第二種情景是進入土壤中的凋落物僅有小部分經過解聚及初級氮轉化后生成的小分子有機氮、銨態氮和硝態氮。在這種情景下,退耕后隨演替進程土壤總氮的累積速率理論上應比較高。通過分析參與土壤大分子多聚體解聚過程的幾種重要的、與氮轉化相關的胞外酶,我們發現蛋白水解酶活性與初級氮礦化速率顯著相關,表明蛋白質解聚環節是初級氮礦化作用的限速步驟。蛋白水解酶活性也與土壤總氮含量顯著相關。由于蛋白水解酶活性理論上與被解聚的多聚體呈正相關關系,因此,蛋白水解酶活性與土壤總氮含量之間顯著的相關關系意味著被解聚的多聚體有機質與土壤總氮含量呈正比例關系,即次生演替過程中隨著土壤總氮增加,不同演替階段的土壤總氮按一定比例被解聚成小分子有機氮。基于此,我們認為多聚體有機質解聚過程受限制也是解釋演替過程中土壤總氮累積的一條重要機制。
基于不同退耕恢復模式的研究也支持退耕后土壤總氮與有機碳能較快累積,但退耕模式對總氮與有機碳累積速率具有重要影響[22-23]。長期退耕模式試驗地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古周村小流域,包括三種退耕模式,即種植經濟樹種香椿、種植牧草桂牧一號及任豆與桂牧一號混種,以未退耕的玉米-大豆輪作地為對照。退耕16年后,所有退耕處理的有機碳水平均得到了顯著提升,但種植香椿處理的土壤有機碳增加最顯著;種植香椿和任豆/桂牧一號混種二種退耕模式下土壤總氮與總磷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基于磷脂脂肪酸(PLFAs)分析的結果表明,三種退耕模式下土壤微生物及其不同功能群豐度均顯著增加[22]。
1.2 基于區域尺度的證據
為了探明基于小尺度演替序列的結論是否適用于區域尺度,我們在桂西北區域開展了不同巖性下土壤碳、氮隨演替或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包括三種巖性(白云巖、石灰巖和碎屑巖)和五種土地利用類型(耕地、草叢、灌叢、次生林和人工林),其中草叢、灌叢和次生林代表退耕后不同演替階段[24-28]。總體上,土壤有機碳和總氮隨退耕后演替進程而增加[24-25],這與基于小尺度退耕演替序列的結果一致。然而,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巖性對土壤有機碳和總氮隨退耕后演替的變化特征具有顯著影響[24-25,27]。在白云巖區,自然生態系統轉變為耕地后土壤總氮與有機碳流失相比石灰巖區更嚴重;反過來,白云巖區退耕后土壤總氮與有機碳累積相比石灰巖區更明顯[24-25]。造成白云巖與石灰巖區土壤總氮與有機碳隨土地利用變化存在差異的主控因素為土壤交換性鈣水平。如前所述,交換性鈣是決定喀斯特土壤有機質穩定的重要因素,交換性鈣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土壤有機碳和總氮的水平[7,15]。一方面,白云巖和石灰巖的溶解速率存在很大差異,后者是前者的3-60倍[29]。另一方面,喀斯特耕地土壤侵蝕速率相比其他土地利用類型較高[30,31]。在白云巖區,由于耕地土壤侵蝕過程中鈣流失速率大于巖石溶解過程中鈣的釋放速率,導致耕作過程中土壤鈣含量下降嚴重,土壤總氮與有機碳水平相應下降;而石灰巖區由于巖石溶解過程中鈣釋放速率高,耕作過程中流失的鈣能得到及時補充,土壤鈣含量在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之間差異低于白云巖。退耕后,土壤侵蝕速率下降,鈣的淋失速率相應降低。在白云巖區,土壤中的鈣通過巖石溶解釋放而逐漸得到補充,土壤總氮與有機碳相應增加;而在石灰巖區,土壤中鈣由于在耕作過程中維持比較高的水平,因此,退耕后變化不大,土壤總氮與有機碳含量變化幅度不如白云巖區[25]。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巖性不僅影響土壤有機碳含量,也影響有機碳的穩定性;但退耕后的演替僅影響土壤有機碳含量[26]。
植樹造林被視為增加土壤固碳、減緩全球變暖的有效途徑[5]。然而,目前關于造林影響土壤有機碳庫變化的內在機理的認識尚不充分。為了探明植樹造林對土壤碳、氮和磷含量的影響是否受巖性的調節,在典型喀斯特區采用配對采樣的方式,分別在石灰巖和碎屑巖區采集了農田和人工林表層土壤樣品(0~15 cm),分析了土壤有機碳、全氮和全磷含量[27]。結果表明,造林對土壤有機碳和氮庫的影響受巖性調節,但對土壤全磷的影響不受巖性調節。相比石灰巖區,在碎屑巖區造林短期內對土壤有機碳庫的提升效果更明顯。相反,在石灰巖區,造林導致土壤氮庫顯著下降;而在碎屑巖區,造林對土壤氮庫沒有顯著影響。在兩種巖性區,造林均會導致土壤磷庫的下降。此外,在兩種巖性區造林都會引起土壤碳、氮和磷元素的摩爾比增加,這表明造林后土壤固碳會逐漸受土壤氮和磷的限制。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在二種巖性條件下,造林后土壤穩定性碳組分在總有機碳中的比例均顯著下降,意味著造林后土壤有機碳穩定性下降。我們的研究表明植樹造林對土壤有機碳和氮庫的影響受巖性調節,為解釋造林對土壤碳和氮庫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化影響提供了新的機制[27]。
通過對無機氮(DIN,銨氮+硝氮)、可溶性有機氮(DON)、凈礦化速率和凈硝化速率的分析,我們發現土壤硝氮、總可溶性無機氮、凈礦化速率和凈硝化速率均隨植被正向演替(即從草叢到次生林)而增加[28]。土壤NO3-∶NH4
+比與DIN∶DON比在草叢階段與1無明顯差異,之后隨演替進程而線性增加,在灌叢與次生林階段(特別是后者)上述比值均顯著大于1。因此,基于區域的研究支持基于小尺度演替序列研究得到的結論,即在草叢階段缺氮,而在次生林階段則表現出明顯的氮飽和特征[28]。
土壤微生物養分限制性分析也是評估生態系統氮、磷養分狀況的重要依據[32-35]。通過對桂西北峰叢洼地區域不同演替階段生態系統土壤胞外酶活性化學計量特征的分析表明,喀斯特生態系統土壤微生物主要受碳和磷的限制,而不受氮限制。進一步分析表明,微生物受碳限制程度在不同演替階段或巖性條件下存在差異,農田和森林最高,而草叢最低;白云巖區域比石灰巖區域微生物受碳限制程度更高[32]。微生物磷限制隨演替變化特征也受巖性影響,在白云巖區域,微生物受磷限制程度從農田至次生林逐漸增強,但在石灰巖區域受磷限制程度在不同演替階段之間無明顯差異[32]。
2 喀斯特與非喀斯特森林氮狀況比較
土壤初級氮轉化是反映森林氮狀況的重要指標。我們前期的研究表明退耕之后喀斯特生態系統土壤總氮快速累積,在森林階段表現出明顯的氮飽和特征。但是僅針對喀斯特生態系統的研究無法判斷氮飽和是否是喀斯特森林的獨有特征。基于此,我們采用氮同位素稀釋法研究了典型喀斯特森林及其鄰近紅壤區的非喀斯特森林初級氮轉化特征[36]。除銨態氮同化速率外,其他測定的初級氮轉化速率喀斯特森林均高于非喀斯特森林。非喀斯特森林的初級氮礦化速率較低而銨態氮同化速率與喀斯特森林相似,導致非喀斯特土壤產生的銨態氮能被較好固持。同時,生成的硝態氮大多被DNRA和GNI二個過程有效固持,導致非喀斯特森林硝態氮凈產生速率非常低。而在喀斯特森林,生成的銨氮僅有小部分被固持,加上硝化速率高而固持速率低,導致土壤硝氮凈生成速率較高。非喀斯特森林的氮飽和指數(GN∶GAI)與1無顯著差異,但喀斯特森林則遠高于1,意味著喀斯特森林表現出氮飽和特征,而鄰近的非喀斯特森林則受氮限制[36]。土壤酶活性化學計量關系能反映土壤微生物對碳、氮和磷的需求狀況,從而間接反映土壤養分的可利用狀況[34-35]。基于此,我們研究了典型喀斯特森林及其鄰近的非喀斯特森林土壤酶活性化學計量特征[33]。基于向量長度的分析表明,喀斯特森林土壤微生物受碳限制程度高于非喀斯特森林。基于臨界C∶N比值的分析表明,喀斯特森林土壤微生物受碳限制,非喀斯特森林土壤微生物受氮限制。基于臨界C∶P比值和向量角度的分析,發現喀斯特與鄰近非喀斯特森林土壤微生物均受磷限制,但非喀斯特森林受磷限制程度高于喀斯特森林[33]。基于區域尺度土壤酶活性化學計量關系的研究表明在區域尺度上喀斯特森林土壤微生物普遍受碳限制,而不受氮限制[32]。
3 結論
我們的研究表明西南喀斯特山區退耕后土壤總氮能比較快速累積,退耕后土壤可利用氮水平隨演替進程而增加,喀斯特森林表現出明顯的氮飽和特征,而鄰近的非喀斯特森林則表現出氮限制特征。我們的研究意味著西南喀斯特山區退耕后的生態恢復僅在早期短時間受氮限制,而中后期則不受氮限制;充足的氮供應可保障生態恢復工程的固碳效應。喀斯特森林氮循環具有其獨特性,在全球變化背景下,其響應與適應性也可能異于其他區域/類型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