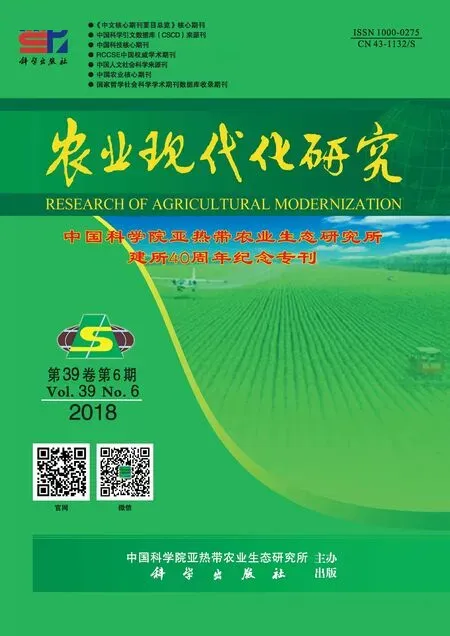氣候變化及人為活動驅動下的西南喀斯特生態水文研究評述
劉梅先 ,徐憲立 *
(1. 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亞熱帶農業生態過程重點實驗室,湖南 長沙410125;2. 中國科學院環江喀斯特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站,廣西 環江 547100)
喀斯特在全球廣泛分布,約占陸地總面積的12%,供應了世界上約1/4人口的水源[1],在社會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和生態環保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特殊的地質、地形和地貌形態,喀斯特地表持水能力弱,呈現“山(地)高水低”、“石多土少”、“土薄易旱”等特點,水資源利用相對困難。我國是世界上喀斯特面積最大、分布最廣的國家之一,其中西南喀斯特連片分布區面積達54萬km2。限于人口壓力以及認識的不足,以往過度且不合理的開發利用,加劇了當地水土流失,使得大面積地表呈現基巖裸露的石漠化景觀[2],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為遏制喀斯特地區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國家先后投入巨資,并同時整合國家相關部門及地方政府的生態修復和環境治理項目與資金,推進石漠化綜合整治,實施了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生態扶貧、石漠化綜合治理等一系列生態建設工程,已然卓有成效。然而,地表水分虧缺依然是喀斯特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的主要因素,也是限制農業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因子。
生態水文循環是地球生物物理化學循環的核心環節,其關鍵過程如產流、入滲、蒸發、污染物遷移轉化、泥沙形成與輸送等,密切關系到水分分配和水資源質量,影響到水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問題,一直以來備受關注[3-6]。尤其在全球氣候變暖和人口激增的普遍背景下,人們對氣候變化和人為活動協同驅動下的生態水文問題關注持續增強,喀斯特地區也不例外[7-8]。目前圍繞喀斯特生態水文的研究,涉及了包括水文地球化學[9-10]、坡面水文過程[11]、植被水分來源[12]與耗散特征[13-15]、喀斯特水文模擬[1,16]等多個方面。這些研究從尺度上可以概括為中微觀尺度機理(植株、坡面過程)、宏觀尺度(流域、區域)表現和生態水文模型構建與應用幾個方面。以下主要結合本研究組近5年的相關成果,從這幾個尺度來簡述國內外的主要研究進展與發展趨勢。
1 喀斯特生態水文過程與機理
中微觀尺度生態水文過程是形成宏觀生態水文表現的基礎。中微觀尺度上的現象以及觀測,是闡明生態水文過程基本規律及機制、理清宏觀尺度生態水文過程的基礎手段。從根本上講,喀斯特生態水文過程及其機理與非喀斯特地區是一致的,如植被根系生長改變土壤水文性質[17-19],不同冠層結構、需水耗散特征等改變降雨分配(如冠層截留)[20]、地表蒸發等過程[21],從而改變喀斯特坡地水文過程,影響地表和地下徑流形成、土壤水分變化和分布[22-24]等。但是,喀斯特地表介質巨大的空間異質性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喀斯特地區生態水文過程與非喀斯特地區存在明顯差別。通常來講,發育良好的喀斯特地表介質包括地表土壤、表層巖溶帶和深層徑流帶(地下河網)三種形式[25]。淺薄且滲透速率高的土層以及大量地下裂隙、管道的存在,使得喀斯特地區水文過程、水文—水質(溶質、顆粒物等)耦合過程、植被耗水過程等,均與非喀斯特地區有所不同。如喀斯特地表徑流遠低于其他地區[26-27],而地下徑流是徑流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11,28-29]。喀斯特地區生態水文過程與其他地區最主要的差別,可能首先體現在地下快速滲漏過程[15,29]。如研究組基于模擬降雨(40~120 mm/h)的結果表明,西南喀斯特坡面水文過程以地下水文過程(包括土壤—巖石界面壤中流、表層巖溶帶蓄水、深層滲漏)為主(占降雨70%左右)[29]。然而,由于喀斯特地表的復雜性,地下水文路徑不明,在坡面尺度上直接無創觀測地下滲漏過程目前還難以實現。
同時,復雜的地表介質也決定了喀斯特地區植被水分吸收消耗的復雜性。由于土壤淺薄、儲水能力低,喀斯特地表土壤水往往無法滿足植物正常的生長需求。為獲取足夠的水分,深根植物根系會扎入表層巖溶帶裂隙中吸收其儲存的水分[30]。因此,喀斯特植物水分來源是表層巖溶帶裂隙水和土壤水的動態組合(當然其最初來源于大氣降水),植物對不同介質中水分的吸收取決于植物水分需求和介質水分含量的狀態。但是,受到喀斯特地表復雜性以及觀測手段的制約,目前對這兩者的認識仍然有限。以喀斯特地區蒸散發為例,目前的研究有三個特點。第一,成果總體偏少;第二,主要偏重在宏觀(景觀)尺度和植株個體尺度,其測定主要采用的是不(甚)依賴于地形的渦度相關法[13]和熱擴散液流探針法[14-15]等;第三,在植株尺度上,主要考慮了較大的喬、灌木,較少涉及矮小植物(如草本等)。但是,矮小植物是喀斯特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西南喀斯特區農、牧業的主要體現形式。
為觀測復雜地表條件下矮小植被蒸散發,基于通量守恒原理設計了一款具有較高精度的風室蒸散觀測裝置(圖1)[31]。基于該觀測裝置并結合TDP探針,研究了喀斯特地區不同農林系統的耗水規律與控制機制,發現不同農林系統蒸散發的控制因子有所差異,其中耕地系統和草地系統的主控因素是氣溫,而林草混合系統的控制因素則是葉面積指數。同時,蒸散與氣象因子之間存在明顯的滯后現象,其滯后時間呈現明顯的季節特征并取決于氣溫、相對濕度和飽和水汽壓差等的變化速率。更為重要的是,幾種典型人工生態系統(大豆玉米輪作、牧草和任豆牧草)對土壤水分基本不敏感,說明正常情況下土壤水分可能不是喀斯特生態系統的控制性因素[32-33]。而基于氫氧同位素方法的研究也指出,典型喀斯特生境優勢植物種對不同類型水源的利用比例存在明顯差異,穩定的深層巖溶水是維持旱季植物水分消耗的關鍵[34-35]。

圖1 風室蒸散觀測裝置示意圖(a)、對比效果(b)和野外實物(c)(引自:劉梅先等[31])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T chamber (a), comparison results between the chamber and weighting method,and installation of the chamber in field (c)
2 喀斯特流域生態水文
區域(流域)尺度上的生態水文,多基于遙感、生態水文模型的手段來進行。在嚴峻的氣候變化和人為干擾背景下,人們更加注重氣候變化和人為活動(調蓄,大壩建設、農林業活動等)的生態水文效應。
由于實際記錄所示的“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度和強度增強”和以往文獻中所得出“西南地區氣候變化不顯著”的矛盾,研究組首先探討了西南地區氣候變化情勢,并基于概率模型和聯合概率模型(copula)引入(聯合)風險的概念,明確了氣候極值風險和變化趨勢之間的差異,證實西南地區(廣西、貴州、云南)年降水量逐漸下降但極端降水事件逐漸增強的事實[36],并發現大雨量、暴雨天數和暴雨量等極端降雨因子控制了喀斯特流域的徑流量[37]。隨后進一步發現,雖然當地極端降水事件變化具有明顯的空間差異,但受到大尺度天氣系統變化的影響,其空間差異正逐漸降低,而局地因素的影響力正逐漸下降[38-39]。同時,降雨是影響西南喀斯特流域蒸發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相對于非喀斯特流域而言,喀斯特流域蒸發對降雨變化的敏感性較大,并指出在過往的氣候變化條件下,喀斯特流域生態系統可能受到更大的退化壓力[40]。與徑流和蒸散發不同的是,喀斯特流域泥沙主要受到人類活動的控制。研究發現,西南喀斯特地區流域泥沙量呈現顯著下降趨勢,而這種減沙速率與流域大壩有效控制面積比例呈顯著正相關關系[41]。
除水量水質以外,氣候變化和人為活動的影響還表現在地表干濕條件方面。例如生態恢復可以從多個層次上影響降雨—徑流以及土壤—植被—大氣連續體內的水分交換過程,它導致水分消耗和水分截留的變化(蓄水和耗水平衡關系),會進一步改變當地的干濕條件。而相對于徑流而言,地表干濕條件與植被生長和生態系統安全可能有著更加直接的聯系。針對此,構建了一個地表干濕度模型,基于不同的參數可以甄別人為活動和氣候變化對流域干濕度的相對影響。同時發現,在水分限制地區,退耕還林對地表干濕條件有明顯影響(變干),而在能量限制區域,退耕還林對地表干濕條件的影響相對較小[42-43]。
3 喀斯特生態水文模型研究
生態水文過程的模擬和預測一直都是生態水文學的研究重點和前沿,也是生態水文學在政策實施、水文水資源管理評估等實際應用中的必要途徑。喀斯特地區由于其獨特的地質條件,其產流、匯流過程不僅受地形、土壤控制,而且受巖石裂隙走向、分布以及喀斯特漏水洞和漏斗等巖溶地貌控制,水流具有多孔介質達西流、裂隙管道非達西流等多重水流特征,還具有地表水系與地下水系特征[25]。這些高度異質性的地表介質特征,極大地增加了喀斯特生態水文模擬的難度。目前喀斯特地區的水文模型多采用在集總式水文模型中增加地下水流計算方法[44]。而對于所有喀斯特生態水文模型而言,喀斯特關鍵帶導水介質的定量刻畫是首要面臨的難點問題。目前主要有離散裂隙網絡模型、離散管道網絡模型、等效連續介質模型、雙重連續介質模型和多重介質模型等[1]。這些模型主要用于具有詳細資料的地下水動態模擬中,如3DKFLOW[45]、CFP模型[46]、管網模型[47]和DHSRVM模型[16,48]等。
喀斯特生態水文模型中若要考慮生物地球化學過程,模型將變得更加復雜。一方面對水文模型的時空尺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水中化學成分及其與土/巖作用,需要確定降水入滲后滯留時間和路徑,以及流出出口斷面水流中“老水”、“新水”[49-50]。另一方面,關鍵生態水文要素(養分、泥沙)在循環中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及其與水文過程的耦合過程復雜,至今仍未完全摸清其原理或機制,如巖石裂隙和巖石吸附在總磷、活性磷和硝態氮輸出中起關鍵作用[51-52]。常規上,生態水文模型對于生態系統中養分要素(溶質)和水文過程的耦合模擬,一般以水流方程(如Richards方程、圣維南方程等)與對流彌散方程為基礎,綜合考慮不同溶質的吸附解吸、生物降解和吸收等轉化過程、地表徑流泥沙過程以及不同界面間的水分和溶質交換過程[53]。總體上,這些生態水文模型之間主要的區別還是體現在包含過程的多少、空間離散方法、要素交換方式、溶質轉化過程數學描述和參數化等方面[54-57]。
但是,相對于此類模型框架的確定而言,模型所需要的大量地表、地下巖溶結構和觀測資料,包括裂隙分布、結構、導水性質等參數的獲取可能更為艱難。如何有效地概化喀斯特地上地下二元結構特征,特別是建立土壤—巖石裂隙中水分儲存和運動與植被系統之間的水文連接,以及關鍵要素間的相互作用的準確數學表述,仍然是喀斯特生態水文模型研究面臨的難點。為規避參數獲取困難的問題,結合新型參數優化技術(如貝葉斯,蒙特卡洛、遺傳算法等)的集總式模型備受學者青睞。這類模型雖然回避了一些具體的水文過程,難以反映喀斯特地形、地貌及植被分布對水文過程的影響,但可以準確地模擬降雨—徑流關系、地下水補給過程[1],如較為流行的VarKarst模型[58]。目前我們也已經構建了基于動態植被的喀斯特生態水文模型,可準確地模擬西南喀斯特流域徑流和蒸散發過程[59],并基于該模型計算出了喀斯特地區植被可利用的最大有效水量,定量回答了喀斯特流域表現出更強的氣候敏感的原因[40]。除此之外,基于統計、人工神經網絡(ANN)、支持向量機(LSSVM)等方法來預測喀斯特流(泉)域生態水文過程也是學者常用的手段。這些模型基本完全回避了參數獲取的問題,而且往往具有較高的精度。如研究發現,最優狀態空間方程可以有效的模擬喀斯特流域泥沙過程[60-61],在表層巖溶泉流量模擬中也具有良好的效果[62]。
4 研究展望
喀斯特地表關鍵帶極其復雜,目前對喀斯特地表關鍵帶中水文—巖石—生源要素的遷移轉化過程仍然不夠清晰。要準確描述喀斯特生態水文過程,了解地上地下水文結構是先決條件,但這也是喀斯特生態水文研究的難點。目前或有地球物理的方法確定孔隙和管道的走向與結構,但對于較小孔隙仍然無能為力。較小孔隙的分布以及水文連通性,可能是地表關鍵帶水分蓄存和排放的決定因素,密切關系到污染物遷移以及植被可利用水量。因此,未來應首先加強水文地質和生態水文學的聯合研究,充分利用地球物理、化學的手段,理清并定量刻畫關鍵帶結構。
其次,應更加重視喀斯特生態水文化學過程,亦即水質問題。由于人類社會的干擾和介入所引發的水質污染,如肥料(有機、無機)施用、垃圾堆放和污水廢水排放等造成的點源、非點源污染(如化肥、殺蟲劑、病毒、細菌、抗生素),是造成水質性水資源短缺的罪魁禍首。相對于非喀斯特地區而言,喀斯特地區水文過程迅速且缺少細顆粒沉積物的吸附,污染物擴散快速、危害更大。加強喀斯特生態水文化學過程方面的研究,揭示污染物遷移轉化規律,是完善喀斯特生態環境保護策略的基礎,也是國家重大需求。
再次,應加強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生態水文效應研究。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是影響生態水文過程的主要外在驅動因素。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的干擾能力逐漸增強。如大型水利工程措施、地下水開采、農田耕作灌溉、城市化(海綿城市)、森林破壞與退耕還林還草等,都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界的強行介入。這些干擾改變了地表結構以及物質輸入的組成與數量(如化肥),對生態水文物理和化學過程具有深刻的影響,甚至成為控制因素。為了生存與發展,人類對自然的干擾是不可避免的。特別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氣候變化加快,極端氣候事件頻發,這種嚴峻氣候變化情勢,可能會進一步放大人類活動的負面效應。加強對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生態水文效應研究和評估,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是探討如何實現喀斯特地區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的必經之路。
5 結語
西南喀斯特地區土層淺薄且持水能力弱,地下裂隙多而滲透速率快,導致地表水分虧缺頻繁、生態脆弱、污染物擴散快速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喀斯特地區的合理開發利用,離不開對其生態水文過程的深刻理解。目前,喀斯特生態水文研究已經獲得了喜人的進展,大大提升了人們對植被水分耗散、水分來源與植被適宜性、水文快速過程及機理等各方面的認識,并構建了多種生態水文模型,為喀斯特生態環境治理、水資源高效利用等提供了堅實的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撐。然而,喀斯特地表關鍵帶結構十分復雜,空間異質性巨大,局部觀測或個別流域所得出的結論往往具有一定特殊性,相同的生態水文參量在其他地方(流域)或有不同表現,因此,“因地制宜”、“特殊問題特殊分析”在喀斯特地區顯得尤其重要。
在未來,喀斯特生態水文研究應進一步結合收水文地質的相關方法,加強與遙感、生態學、植物學、地球化學等學科的交叉,同時提高對生態水文化學過程以及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生態水文效應方面的關注,多尺度、多角度地研究喀斯特生態水文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