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炊煙
唐鎮河
好久沒有聞到炊煙的味道了。每當看見裊裊飄揚的炊煙,心中總會驀然升起一種親切溫暖的感覺。那是飯菜的清香,米粿的甘甜,以及親人深情的呼喚。
小時候,即使是貪玩的孩子,遠遠的,只要朝著家的方向看到冉冉升騰的炊煙,就知道那是母親在呼喚兒女回家吃飯的信號。兒女們知曉,炊煙升起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家園,炊煙升起的地方便有親人的等待,媽媽正在家中盼望他們歸來。于是,親情在炊煙里飄蕩,溫馨在炊煙中彌漫。多情纏綿的炊煙,它牽回童真的步履,了卻母親心頭的牽掛。
少年時代,放學回家, 我第一眼看見的總是灶堂前金紅色火苗映照著母親清秀的臉龐,看見母親凝聚著寄托和期盼的眼神。我知道,母親在燃起灶火的同時,也把心中的慈愛傾注在她的廚藝之中,每一頓可口的飯菜都是母親精心烹制的“佳作” 。炊煙的味道,是一種鄉風民俗的味道。每逢農歷傳統的重大節日,裊裊的炊煙帶來灶臺前熱氣騰騰的金色米粿和甜糕,對于我們更是魅力深深的吸引和誘惑。在母親的辛勤勞作中,饞涎欲滴的我們一次次飽享豐收的盛宴。在我的印象中,炊煙和家庭、親情緊緊聯系,簡直可以說,他們之間水乳交融、渾然一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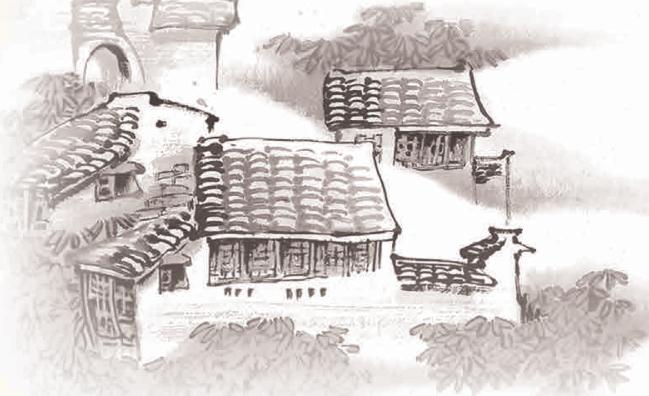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下鄉到莆美鎮上坑村當知青,因此,我們把養育成長的小山村當成終生眷戀的故鄉。清晨,故鄉的炊煙是溫存柔軟的,淡藍色的炊煙,在農家小院的屋頂輕盈彌漫,它時而亭亭玉立,時而款款彎曲,讓人聯想山野樹林遙相連接飄飄欲仙的霧靄與云霞。晨風吹來,村莊脫去輕紗般籠罩的睡衣,裸露出處女般初醒的羞澀與清純。這時,拍翅的雞,遛噠的狗,蹣跚的牛,蹦跳的孩子,拾糞的老漢,散淡的炊煙,到處生機盎然,醉人眼眸。特別是那些正當發情的公雞,它們驕傲地翻拍著矯健的翅膀,迅速地躍上竹籬邊的矮墻、石墩,自豪地炫耀幾聲亮麗的歌喉以后,往往要糾纏看上的母雞調戲一番,更是渲染著遠離鬧市的山村獨特的氣氛。這樣的早晨,怎么不讓人神清氣爽,愉悅涌蕩。
黃昏的時候,炊煙從高低不一的房頂裊裊升起,在晚霞的照射下,炊煙繚繞的村落升騰著一種樸實和單純,顯得格外幽雅、恬靜。那輕輕拂動的炊煙是山村的消息樹,點燃它們的是在灶間忙碌的老媽媽。田間地角勞作的兒女,每當看到這飄飄裊裊的炊煙,心中會突然萌生一種天然的歸屬感。在炊煙的召喚下,他們紛紛走上回家的路途,有的荷鋤挑犁,有的擔筐背簍,有的牽牛趕羊,慢悠悠地行走在鄉村的田埂上……頓時,村姑的民俗小調,牧童的嘹亮竹笛,人們的放縱笑談,牛羊的咪哞歡叫,混合成一闋多姿多彩的交響樂,將炊煙下村莊的黃昏點綴得充實而富于韻味。
夜晚,當炊煙悄悄擴散,勤勞樸素的莊稼人團團圍坐在堆滿稻桿的場院里,一邊品茶嗑瓜子,一邊聆聽老人講述年代久遠的歷史傳說。每逢空檔的時候,那些英俊后生常常不失時機地插播幾句逗樂的葷話, 個別大膽的小伙趁機對心儀的姑娘偷偷捏摸一下豐滿的屁股或胸脯,這些,看來稍微出格而又懂得節制的放浪行為,總是恰到好處地引爆響徹云霄的歡聲笑語。屢屢回眸,這是一幅多么溫馨美好、令人神往懷念的畫面啊。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城鎮和一些鄉村逐步推廣液化氣或電磁爐代替柴草做飯煮菜的功能,原來隨處可見的炊煙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可是,不管世道如何變化,歲月深處的炊煙依然固執地占據記憶屏幕的一角天地,燦爛著我繽紛的思緒。
漂浮在故鄉的炊煙,是那么自然、親切,舒展而纏綿,總讓人有一種歸家后的甜蜜和疲憊時的撫慰。好想再聞一聞故鄉炊煙清純微醺的味道,好想再嘗一嘗老家灶前甘甜沁心的米粿和年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