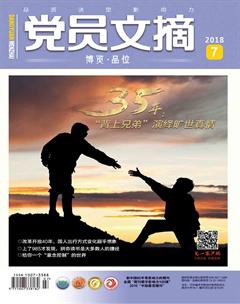金融危機十周年,我們該反思什么
范文仲 黃益平 張幼文 徐忠

2008年,一場源自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危機爆發,并迅速在全球蔓延,其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至今猶在。
如今,研究者仍拿著放大鏡反觀十年前的那個秋天,想搞清楚那場危機是如何發生的,人們該如何避免噩夢重現。
金融界的七個“迷信”
范文仲(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部主任)
近代金融危機盡管在人類的金融發展史上表現方式不太一樣,但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大多是資產泡沫和人性狂歡的結果,每一次金融危機前,往往伴隨著金融體系的迅速膨脹,金融機構的冒進擴張,金融市場亂象頻發。
我總結了全球金融界常見的一些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迷信“這次不一樣”。金融危機往往爆發在人類的經濟和社會進入一個新階段之后,這時人類的生活方式發生很大改變,都認為這一輪的經濟繁榮是由科技的推動力來實現的,不用受到以前傳統的金融規則的影響。
在這種心態下,大家就會進入一個特別喜歡消費或向未來借貸的生活方式,所以,從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擴張,發展到金融體系的資產負債表擴張,進而擴大到國家的資產負債表擴張。全社會都進入了一種高杠桿的狀態。
但實際上每次金融危機都一樣,它的主要特征都是高杠桿和持續的價格上漲。
第二個錯誤是在金融危機前迷信“好日子永遠會持續”,流動性過剩是常態。
第三個錯誤是認為金融要“做大做強”。在金融危機前十年,歐美國家的金融業產值占GDP比例提高了2%,很多國家在競相打造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但繁榮是建立在表象上的。金融的核心功能是提高資源分配的效率,跟它的規模和在GDP中占多大產值沒有關系。背離了這樣一個實體經濟的目標,肯定會出問題。
第四個錯誤是迷信“混業經營是必然趨勢”。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之前,大家都在打造“金融航母”,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做地域和業務的擴張。但其實混業經營不是趨勢,是輪回。每次危機之后,輪回就會變。所以,不要認為混業是一個方向,它是階段性選擇。
第五個錯誤是金融機構追求股東回報的最大化。怎么讓股東回報最大?當然要把收益提高,所以,在資產端,為了做高股權回報率,在每個業務利潤很薄的情況下,無限放大杠桿倍數,人為提高股權回報率。這變得非常薄的利潤,卻借了一大堆錢,把它做成了很大的生意,出現了巨大的期限錯配。
第六個錯誤是迷信華爾街創造出來的所謂金融創新產品。華爾街的一些機構出于利益驅動,把一些不成熟的金融理論和模型應用于實踐。
第七個錯誤是迷信市場調節的無形之手,提倡無為監管。人們在危機之前認為,對那些拿有錢人的閑錢進行投資的,如對沖基金,不需要監管。但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活在真空里,高風險機構的錢盡管是有錢人的閑錢,但它的交易對手完全可能是養老金、共同基金、商業銀行。它們的倒閉也會把其他機構拉下水。
雖然金融危機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但人類社會對危機的記憶常常是短暫的。當傷痛剛開始減弱的時候,監管放松的思潮就會起來。當大家都忘掉這個教訓的時候,當人性又開始狂歡、資產泡沫開始形成的時候,下一場危機的序幕也就拉開了。
不透明的交易很危險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在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包括我在內的全球經濟學家有一個相似的觀點,認為次貸危機很嚴重,但對整個經濟來說問題不大。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美國國會聽證的時候給大家講了一個道理:美國的次債市場出了問題,但次債的規模一共就6000億美金。這是什么概念?相當于所有在美國上市的商業銀行資本金的0.5%。他的意思是說,市場出了問題,但不用擔心系統性風險。當然,最后我們看到的不是這么回事。
什么是次貸?銀行把按揭貸款發給傳統意義上來說不符合貸款資質的客戶,無資產、無收入、無職業的人,這個風險可想而知。正常的銀行家怎么會做這樣的事情?但很多銀行做了。為什么?我覺得就是和后面的資產證券化有關系。
資產證券化最大的好處是,次貸發完之后,移到一個特殊的平臺上打包出售,從我的資產包中移離出去,風險跟著移離出去,從“次貸”變成“次債”,風險看上去不那么清楚了。所以,不透明的交易其實是很危險的。我們發展衍生品市場,推進資產證券化,一個客觀的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看清楚?如果不是很清楚,是否要大力推動?后果是什么?這個我們可以思考。
過去,我們長期的金融穩定依賴兩條,一是長期持續高速增長,在發展中解決問題;二是政府兜底。有的銀行問題很多,但因為覺得有政府兜底。即便不良率高達30%-40%,也沒有人在晚上睡不著覺,只要政府扛得住,銀行的錢你不用擔心。這樣的做法,從表面來看是不太有效率的。但從直接的后果來說,我們確實支持了金融穩定,沒有發生很大的金融危機。
現在碰到的問題是,這樣的做法是不是能持續下去?我覺得政府到底在這個過程中要發揮什么作用?我們要靈活對待。
為什么金融資源不流向實體企業
張幼文(上海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我們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中國的金融資源、資金不流向實體經濟,而在金融系統自我循環越做越大?
其實是實體經濟缺乏有效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所以,資金在金融系統當中自我循環,泡沫越來越大。
金融要支持實體。雷曼兄弟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最終還是引發了整個美國和世界的金融危機。也就是說,不在于整個的金融產業資產資金規模多大,關鍵在于產生問題的企業,這個火種會導致危機,在于能不能及時發現和處置危機企業。
我非常贊同對問題企業的有序清償。這才是問題的根本。舉一個例子。如果這個房間里堆滿了易燃物品,有效的方式是控制亂扔煙蒂,不允許火種進來,或者堆得整齊一點。如果沒有辦法把這些東西移到其他地方去的話,只有這兩種辦法。
這當中也包含了對金融的監管,監管的是違法亂紀的行為,而對于合法的、做大金融市場和做大杠桿的,應該是調控而不是監管,因為它本身是在合法范圍里做的。
金融體系需要新陳代謝
徐忠(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勢政府是我們的優勢,但是,如果過度使用會有很大的道德風險,使得整個經濟效率低下。
人有生老病死,金融體系也要有新陳代謝。我們現在的金融體系,由于沒有新陳代謝,20年前海南發展銀行關閉了、清算了,到現在清算組還沒有做完破產。沒有市場機制,金融機構也會有過度承擔風險的意識、會加杠桿,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監管體制,除了監管架構進行改革,監管理念要進行改革,更大程度上是要形成一個激勵約束的監管體制,使得金融體系有新陳代謝,該破則破。但這個“破”是有序的,要避免產生系統性風險。美國次貸危機的時候,倒閉了530家金融機構,一點問題都沒有,因為人家的存款保險制度發揮了作用,而且是在資能抵債之前給你關掉。
當中,監管如何到位、如何問責,與存款保險制度如何結合,是一系列的問題。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