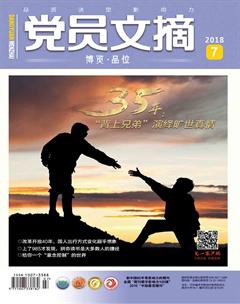這些人和書影響了當代中國
張光芒

周梅森:《人民的名義》——人民的心聲與期盼
《人民的名義》成為刷爆全網的現象級作品。“厲害了,我的‘人民!”電視劇甫一播出,便收獲觀眾熱情的點贊。劇集熱播期間,《人民的名義》原著紙質書銷量增長21倍,電子書增長191倍。除了跌宕的劇情,精彩的表演,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它反映著當前中國反腐敗斗爭的實踐,回應著反腐敗的民心所愿。
周梅森以《人間正道》《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政治小說為人熟知,《人民的名義》里的很多情節,不僅來自真實的社會新聞,也源自他的生活。周梅森坦言:“《人民的名義》是他迄今為止最滿意的一部反腐小說。”當然這也是一部讓人民群眾滿意和欣慰的作品。因為作品道出了人民的殷殷心聲和真心期盼,向腐敗分子亮出了正義之劍,讓風清氣正的社會風氣宛如一股清流。
陳忠實:《白鹿原》——彰顯民族的歷史內涵
電視劇《白鹿原》播出,又一次激起讀者閱讀《白鹿原》的熱情。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精美插圖版《白鹿原》,讓人想起當年《白鹿原》剛一問世,其暢銷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學生必讀”系列,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影響中國人的30本書”,在權威的“改革開放30年10部長篇小說”評選中名列第一。
正如陳忠實所言:“小說展示了這個民族生存的歷史和人的這種生命體驗。”主人翁白嘉軒代表著最樸實淳厚的農民形象,土地就是命根子,他恪守耕讀傳家的傳統禮法,用“仁義”挑起白鹿村團結同心的明燈。腰板挺直的族長能夠處理好兄弟反目、族人互毆、鄰人相騙的生活瑣事,卻在封建禮教與宗法文化崩塌時空余悲愴。這也印證了中國傳統文化為什么經歷這么久沒有中斷。
閻崇年:《御窯千年》——尋求解讀歷史新突破
閻崇年的《御窯千年》認為,“一帶一路”中的絲綢之路,實際也是一條瓷器之路。他坦言,以一種優美器物即瓷器作為中國的英文國名,既是瓷器的驕傲,也是中國的自豪。書中,他通過“瓷器之路”傳遞中華文化,以歷史啟迪智慧,還原了歷史的本真與殘酷,分析讓人感到深刻真實,使人感到歷史的厚重與滄桑。
在閻崇年看來,宮廷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要了解其精髓,則必須通過其載體——御窯。皇宮有御窯,能成其大;御窯為皇宮,更能顯其貴。閻崇年立足千年中國歷史,品味御窯瓷器的傳世精品,縱論御窯的興與衰,透視瓷器的情與趣。歷史的觀察,人文的敘述,以小見大,寓理于器,淋漓盡致地展現御窯及瓷器對于中國文化的作用,以此窺見中國歷史的獨特一面。
梁曉聲《: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見證人性光輝與尊嚴
作家梁曉聲一直被當做平民的代言人,他與共和國同齡,用文字見證時代變遷。無論是回望過去,還是刻畫當代,他都悲憫底層命運,筆指官僚權貴,秉持道義。《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此心未歇最關情》《中國人的日常》,通過他的作品,可以看到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們的追求及幻滅,他們的執著與無奈,他們的默默無聞所孕育的憤怒和反抗。
梁曉聲的風格,一如十多年前,依然保持著他那種罕見的真誠,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義憤和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以及他對中國人、對中國的殷切希望。他認為中國民間具有極其本能的、蠶絲被套般的向善維護系統,以影響自己的兒女們不變惡劣,這個系統從未被徹底摧毀。他說,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里,我們需要愛與被愛,需要理想與擔當。所以,梁曉聲不僅屬于一個時代,更屬于他生活的一切時代!

王蒙:《王蒙談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文化的自信
王蒙先生是文化自信的提倡者,他是當代具有標志意義的作家、學者,其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其文化言說具有不一樣的眼光和品格。
王蒙一貫堅持文化的自信,《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講孔孟老莊》《王蒙談文化自信》《中華玄機》。讀他這些書,不僅理解和認識了“文化自信”的深刻含義,更能懂得文化自信是最基礎、最廣泛、最深厚的自信。一個民族的文化要不斷發展和充滿活力,必須要有“對自己文化更新轉化、對外來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適應全球大勢、進行最佳選擇與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謀求發展的能力。”
黃亞洲:《紅船》——永不泊岸的紅船
“紅船精神”就是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作家黃亞洲的《紅船》,是對“紅船精神”的文藝解讀,尊重歷史而又不拘于小節,鋪陳紅船而又不止于建黨。
黃亞洲是一位有著嚴謹創作態度的作家,他創作的《開天辟地》《建黨偉業》《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等作品,繼承了當代歷史類文學中以細節還原歷史面貌的寫作范式。《紅船》中,以真實歷史事件為依托,塑造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百余位個性鮮明、命運迥異的歷史人物,寫他們在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思索與進取、沉浮與抉擇。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提倡紅船精神,至關重要!
畢淑敏:《帶上靈魂去旅行》——旅行是心靈和解的過程
《帶上靈魂去旅行》,畢淑敏在用一個個腳印丈量這個世界的同時,向世人展示,旅行是心靈和解的過程。
畢淑敏說:“書與旅行,是飛向天堂的兩翼。”既是醫者又是作家的身份,讓畢淑敏一次次目睹生命的青春與蒼老、健康與病痛,對珍視生命與靈魂有了獨特的領悟。“一個人走了多遠的路,去過多少個地方,見過多少人……這些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曾在旅途中看到過什么,曾想到什么,歸來后你若隱若現地感到改變了什么。”在都市人都渴望逃離束縛、獨自旅行的時代,畢淑敏應該會帶給我們更多的共鳴。
(摘自《做人與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