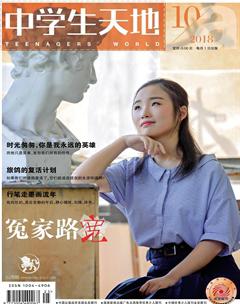旅鴿的復活計劃
蘇澄宇

1914年9月1日下午1點,一只叫瑪莎的老鴿子在辛辛那提動物園去世。作為旅鴿一族最后一名幸存者,它的離去代表了旅鴿整個物種的滅絕。
旅鴿曾是北美數量最多的鳥類。它們在鼎盛時期,數量多達數十億,遍布整個北美大陸。旅鴿遷徙的過程堪稱一場生物風暴,猶如懾人的烏云呼嘯而過。“烏云”往往要數小時甚至數天才能散去,留下的只有遭殃的莊稼與干涸的土地。
當一群旅鴿逼近城鎮的時候,許多村民會以為末日要來了。美國鳥類學家約翰·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曾在《鳥類學傳記》里描述了他在1813年觀察到的旅鴿遷徙景象:
……烏云籠罩了城市上空,白晝轉成暗夜。人們講話得吼出來,不然就會被如雷的振翅聲所掩蓋。一只鷹試圖在鳥群的后方碰碰運氣,一瞬間它們像激流般聚成緊密的一團,伴隨著雷鳴巨響;這個幾乎實心的鳥群沖向前方,劃出一道道波紋線條……日落時我已抵達路易威爾,距離哈登斯堡 55 英里,這些鴿子還在飛過,數量絲毫不減,如是持續整整 3 天。重見天日的市鎮宛如鬼城。觸目所及都是鴿子糞,就像融化的雪花一樣。
旅鴿數量如此之多,看起來似乎不可能會滅絕,但在處于食物鏈頂端的人類面前,這都是彈指間的事。在18世紀和19世紀,人們認為旅鴿具有藥用性。它的血液被認為對眼睛有好處,胃壁被研磨成粉之后用來治療痢疾,甚至糞便也被用來治療各種疾病,包括頭痛、胃痛、嗜睡等。農民、獵人全都想抓鴿子賺點外快,他們便開始大肆捕殺旅鴿。
不到一個世紀,旅鴿就滅絕了。對于美國人來說,旅鴿的滅絕是個令人警醒的教訓,復活旅鴿就成了人類贖罪的一個方法。
說到復活滅絕動物,也許你最先想到的就是《侏羅紀公園》,正是通過分離蚊子琥珀里的恐龍血液,科學家得到了恐龍的DNA,才得以將恐龍復活。但實際上,由于滅絕的恐龍的DNA實在太過古老,已超過其DNA的半衰期而無法恢復,這意味著它們已經徹底滅絕。DNA的半衰期,是指一個已經死亡生物的DNA核苷酸骨架(核苷酸骨架是DNA鏈的基本結構)之間的化學鍵半數降解掉所需的時間。如果一個生物的DNA在一定時間之后處于半衰期,則意味著這一生命體的遺傳信息有一半已經丟失。根據研究人員推算,DNA的半衰期為521年。
旅鴿雖然已經滅絕,但它們的DNA還一直保留在博物館的標本和化石中,距今也就百年時間。隨著基因工程技術的飛速發展,旅鴿的復活成為了可能。
Revive and Restore是一個致力于通過基因工程技術保護瀕危動物、復活滅絕動物的保護組織。在復活滅絕動物的項目中,旅鴿是重中之重。
問題來了,為什么旅鴿是Revive and Restore的首選復活對象?
除了復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復活旅鴿有利于保護美國東部森林的物種多樣性,也會大大豐富地球基因庫。
和許多森林生態系統一樣,北美東部的森林生態循環依賴于環境擾動。在生態學上,“干擾”的定義多是對生態系統的“自然災害”的解釋。但其實,周期性、輕度到中度的擾動,對森林生態系統的再生是有積極作用的。生態干擾通過調整物種間的相互關系,促進生態系統演化。例如,有的干擾能降低一個或少數幾個物種的優勢度,為其他競爭相同資源能力較差的物種增加了資源,為物種的分化和資源的分配提供了有利條件。
通過研究,科學家發現數量龐大密集的旅鴿群,是數萬年來森林擾動的重要驅動因素。雖然美國東部在過去75年里經歷了大規模的重新造林(這是一個較大的干擾因子),但就整體而言,干擾因子已經減少到只有天氣事件、野火和伐木活動了,連續周期性的積極干擾因素的減少,導致許多本地物種數量減少。通過復活旅鴿,在美國東部森林將其恢復到一定種群數量,就能讓旅鴿成為積極的干擾因子來刺激森林的再生循環,使森林生態系統更具生產力和多樣性。
旅鴿瑪莎成了復活的關鍵。首先,拿旅鴿標本瑪莎的DNA與相近的現存物種斑尾鴿的DNA作比較(斑尾鴿與旅鴿都屬鳩鴿科)。然后,確定斑尾鴿基因組需要編輯的區域,通過基因工程技術編輯斑尾鴿的生殖細胞,人工繁育新一代旅鴿。最后,將旅鴿種群重新引入野外。
雖然只有三步,但實現起來可沒那么簡單。在此之前,就有科學家做過復活克隆動物的實驗。1999年,全世界僅存一頭活著的比利牛斯野山羊,科學家給這頭母羊起名“塞利婭”。塞利婭死后,它的細胞被保存在馬德里和薩拉戈薩的實驗室里。隨后幾年,研究人員嘗試“復活”塞利婭。他們把它的細胞核注入被剔除DNA的普通山羊卵細胞中,然后植入成年母山羊體內。2003年7月30日,研究人員接生出塞利婭的克隆體。但這只新出生的野山羊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在出生7分鐘后因呼吸困難而死亡。可見復活動物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
當然,另一個需要回答或解決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把旅鴿復活了,它們能適應現在的生活環境嗎?如果適應了現在的環境,旅鴿的數量又很快恢復到過去數十億的級別,它們會對現代城市造成沖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