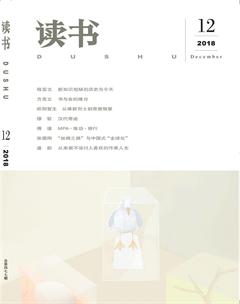MPA·練功·修行
傅謹
七月初,我在廈門大學文學院給本科生上一門講座課,接在我后面上課的是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鐘明德教授。我不記得我們是不是曾經見過面,但是感覺挺熟,他希望一起聊聊,于是我們就有兩次很長也非常愉快的聊天。鐘教授是臺灣著名的后現代戲劇觀念代表人物,但他要和我談的是戲劇表演。他有備而來,送我他的新著《MPA三嘆:向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致敬》。
如果用相聲做比喻,他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他負責闡述理論,我負責“破”。我們恰好對同一話題感興趣,那就是戲劇演員的訓練。
一
鐘明德新著的重點,是他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簡稱“斯氏”。想必鐘明德也覺得俄國人這么長的名字太費篇幅吧,所以簡稱“史氏”)MPA(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鐘譯為“身體行動方法”,大陸學者一般譯為“形體動作方法”)理論的理解。他認為斯氏被后人誤解甚多,不過他是通過波蘭導演格羅托夫斯基(以下簡稱“格氏”,鐘譯為葛羅托斯基,故他簡稱其為“葛氏”)引入對斯氏的介紹與評價的。格氏被公認為斯氏最好的傳人,他把斯氏晚年的戲劇表演理論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對西方當代戲劇的影響其實遠大于布萊希特和梅耶荷德。在中國,格氏以“貧困戲劇”或“質樸戲劇”聞名,當代西方最重要的戲劇理論家尤金尼奧·巴爾巴和近年在中國極具影響的導演彼得·布魯克都是格氏的衣缽傳人,對他的理論推崇備至,不過關注重點并不是貧困戲劇。這些重要戲劇家都在歐洲,但鐘明德并不在歐洲學戲劇,他一九八二年進入美國紐約大學表演研究所,后來還成為美國著名戲劇理論家、教育家謝克納的學生,在中國大陸,謝克納更多是因為他的中國傳人孫惠柱翻譯并介紹的“人類表演學”而聞名,但鐘明德對謝克納的興趣點不是這個譯成中文后名字有點奇怪的“人類表演學”,而是表演與真正的人類學相交的那部分。
在中國話劇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論體系的統治地位依然是無可動搖的,除斯氏外,話劇界并沒有任何其他理論有如此覆蓋性的影響,當然也沒有形成過自己的有影響的完整理論。數年前李默然、徐曉鐘兩位前輩試圖推動這一現象的改變,邀集同人舉辦了一次“中國表(導)演理論體系研討會”,會上只聽我們在熱鬧地談戲曲表演,在話劇表(導)演理論方面反而沒有什么令人關注的研究成果。近年話劇界喜歡談論“中國學派”,然而無論理論還是實踐,要真正成形并獲得國際戲劇界公認,還有漫漫前路。所以在中國話劇領域,斯氏仍然是唯一的表演理論“體系”。斯氏體系在中國最為戲劇界熟知的,是對戲劇演員心理體驗的重視,體系的第一要義,就是讓演員在導演啟發下通過心理體驗“進入角色”。焦菊隱總結其為“心象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鐘明德在此登場。他說,斯氏后半生的探索與追求,其實與他前半生所創立的、重視“心理體驗”的理論有很大出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斯氏變得更重視形體表達,尤其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心臟病突發后的養病階段,他開始對戲劇表演和導演的規律有了全新的認識。這就是他在《演員創造角色》里強調的“由外而內”的形體動作方法,他要求演員在排練時首先考慮“在這種情境下他將要在形體上做些什么,也就是將怎樣動作(絕不是體驗,在這個時刻千萬不要想到情感)……當這些形體動作清楚地確定下來了,給演員剩下的就只是在形體上加以執行(注意:我說在形體上執行,而不是體驗,因為有了正確的形體動作,體驗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演員創造角色》,中國電影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38頁,下引此書只標注頁碼)。這里的斯氏的理論和我們一般的理解簡直有天壤之別,而這里所說的“形體動作方法”,就是鐘明德所說的MPA。
把MPA作為戲劇表演的核心,從重視“心理體驗”轉向重視“身體行動”,斯氏個人戲劇觀念的這一變化,后來成了后現代戲劇最主要的理念,所以,說他的這一變化引領著二十世紀后半葉西方戲劇表演理論的重大轉向并不為過。然而,如鐘著所引與大陸學者的私人通信所說,斯氏理論的這一部分,在尊奉斯氏體系的“長期以蘇聯老大哥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為師的大陸戲劇界”,幾乎沒有影響,斯氏理論的這部分完全消失了,“談的都是早期的理論與實踐”(42頁),即使是二0一三年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專門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中后期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依舊如此(其實,鄭雪來翻譯的《演員創造角色》前面兩位蘇聯學者寫的導語,對斯氏的這一重大轉變有很清晰的介紹)。不過鐘著并不認為這是中國大陸戲劇界的偏差,如他所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格氏突然走紅前,歐美戲劇界也并不太理解斯氏的這些學說;其實鐘明德自承他也這樣,一九八六年他回臺灣后投入小劇場運動,主軸還只是布萊希特的政治劇場或阿爾托的劇場美學,“鐘后現”的雅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這可是件有趣的事。我是在梳理一九三五年梅蘭芳訪問蘇聯的相關資料時開始注意到斯氏的這一變化的,尤其是他那又愛又怨的學生梅耶荷德與梅蘭芳的關系。從我們新發現的資料看,蘇聯戲劇家之所以重視梅蘭芳的演出,是由于梅蘭芳(或者說是戲曲)的表演美學,在這個最恰當的時間點,為他們艱難地尋找戲劇表演突破口提供了一個最好不過的范本,并給了歐洲戲劇理論家重要的啟發。蘇聯戲劇家厭倦了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現實主義原則”,恰好在此時來了梅蘭芳。以梅蘭芳為代表的戲曲表演,在舞臺上始終刻意保持著與現實生活強烈而明顯的距離感,但是卻具有更強的戲劇表現力。既然梅蘭芳的表演是精彩的,說明戲劇表演不應該只有現實主義這一條道路和一種模式。眾所周知,布萊希特就是由此開創了他的新理論,梅耶荷德看似背離現實主義傳統的表演追求,似乎也從梅蘭芳這里獲得了實證的奧援。二十世紀后半葉西方著名戲劇導演和理論家,幾乎一邊倒地追求非寫實主義的、非幻覺的表演,實與梅蘭芳訪蘇這個重要契機關系密切。
梅耶荷德的追求很快夭折,他被送進了集中營并死于非命,但是與他相近的努力在蘇聯之外逐漸開花結果。梅耶荷德、格氏與梅蘭芳的關系幾乎沒有什么人提及,從鐘著我找到了一條可能的通道,那就是斯氏的MPA。我在想,這些蘇聯、東歐戲劇家對梅蘭芳的興趣,或許并不只在非寫實的表演形態,更在于戲曲的訓練方法與MPA的內在關聯,斯氏對梅蘭芳的興趣,背后或就是由于MPA與戲曲演員的職業生涯的相似性?因為戲曲演員的訓練與表演就是從身體行動開始而非從心理體驗開始的,斯氏苦苦思索一生,到晚年才仿佛明白的道理,在中國戲曲領域早就成功實踐了數百上千年。
戲曲演員自幼接受艱苦的訓練,完成從素人到演員的轉換。戲曲演員的訓練內容,壓腿、倒立、跟斗、圓場、水袖等(其實也包括喊嗓),全部內容都與且只與身體行動相關。戲曲演員的培養過程只訓練身體,即使在劇目表演階段,教的仍然是一招一式,是招式本身,是身體行動方法,MPA!其實,不僅戲曲,所有以身體為媒介的藝術,比如舞蹈,都必須經歷長期、艱苦且系統的訓練,目的就是提升演員對身體的控制能力,包括身體的柔軟性、爆發力和動作的準確度等,最終它們所導向的都是且只是身體的表現力。斯氏體系進入中國后,戲曲界頓時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覺得只關注身體表達不講人物心理體驗的傳統訓練方法太落后啦,于是就開始追求“進步”,不想斯氏自己倒先變了。前面所引斯氏《演員創造角色》里的那段話,仿佛就是為證明從身體行動出發的訓練方法的合理性而寫的:“有了正確的形體動作,體驗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他自己已經把心理體驗看成“舊劇場”該淘汰的方法了。
鐘著沒有提及是什么導致斯氏發生了這一變化。戲劇表現人物,戲曲演員常說的“裝龍像龍,裝虎像虎”只是第一步,解決的是“像”的問題;表演領域更重要的或更高層次的,是演員如何吸引觀眾,調動觀眾的情感,與之產生共鳴。因此,表演不只是為了讓觀眾認可演員與角色之間的相似性,更要通過有特殊魅力的表演,讓觀眾受到感染,情不自禁地進入演劇所提供的那個與現實生活相異的世界。這樣簡單的道理,斯氏怎么可能不懂?然而,他早期強調的心理體驗、進入角色等,所解決的問題似乎只是讓演員演得“像”,這當然是不夠的!戲劇表演不能停留在模仿現實人生的層面,亞里士多德說,藝術模仿的不是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而是人“應該有”的樣子;演員的工作不只是讓舞臺上的角色“像”戲劇作品里的人物,而是為人物塑形,讓觀眾覺得那個戲劇人物“應該”是這樣的——梅蘭芳讓觀眾覺得《貴妃醉酒》里的楊貴妃“應該”是這樣的,裴艷玲讓觀眾覺得《夜奔》里的林沖“應該”是這樣的,張火丁讓觀眾覺得《鎖麟囊》里的薛湘靈“應該”是這樣的。即使觀眾心目中對楊貴妃、林沖和薛湘靈的形象早有預設,優秀的演員也能通過舞臺表演改變甚至顛覆觀眾先入為主的預設,這樣的戲劇和表演才令觀眾癡迷。然而,無論是梅蘭芳還是裴艷玲、張火丁,戲都是師傅教的,師傅教的就是形體動作,就是招式,是MPA。他們學會了,于是用在舞臺上,用得精彩。
這就有趣了,黃佐臨一九六二年不是提出“梅蘭芳戲劇觀”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觀、布萊希特戲劇觀之不同(所謂“世界三大戲劇體系”就是從這里以訛傳訛成為“常識”的)嗎?斯氏晚年的戲劇觀居然和梅蘭芳為代表的戲曲表演殊途同歸。只不過按繼承了斯氏衣缽的格氏的說法,斯氏沒有來得及按他晚年的這一理論創見建立一套新的戲劇演員訓練體系,“斯氏的MPA探索并沒有真正完成,原因是他死了”(《MPA三嘆》,79頁)。
鐘明德坦言,他在美國學習戲劇時還不明白這些。臺北藝術大學原校長邱坤良在為該書寫的序里說,他親身見證了“鐘后現”學術立場的大轉折——近年來鐘明德開始熱衷于講述各種超驗的與靈異的感受,我想邱序大約是不好意思直接說鐘明德開始變得“神道”了。按鐘的自述,那是由于一九九八年他偶然參加臺灣原住民的一場祭祀,在凌晨突然體驗到令自己震撼的“狂喜”,心靈仿佛突然升華。接著他持續在類似的相關儀式里獲得這樣的體驗,他把這些神秘的感受與斯氏的表演理論聯系起來,認為這就是MPA所應該追求的效果。
二
我和鐘明德有關戲劇表演的理解,就在這里出現了分岔。鐘著認為斯氏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戲劇理論家,他最偉大的貢獻是MPA,而不是我們熟知的要求演員從心理體驗出發的戲劇觀念。他同樣推崇格氏晚年的演員訓練方法,格氏希望能通過某種方法,訓練出具有天生魅力、“會從內部發光”的“神圣演員”,這樣的演員能夠通過表演調動和激發觀眾的情感,使劇場進入觀演一體的理想演劇狀態。優秀演員都有這樣的氣場,鐘著說裴艷玲就是這樣的演員,那么,梅蘭芳就更是了。然而格氏的訓練和梅蘭芳、裴艷玲所接受的訓練并不是一回事。
我隱約覺得鐘明德所說的“神圣演員”,多少有些像是通靈的薩滿,實際上他就是這樣暗示的,鐘明德認為通過斯氏所倡導的“身體行動方法”,就可以訓練出這樣的演員,因此他對MPA的價值深信不疑,尤其因為他先后親身參與了臺灣高山族的矮靈祭、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和云南景頗族的目瑙縱歌的過程,在這些群體性的劇烈“行動”過程中,身體被誘發出超越極限的能力,在狂歡中進入出神忘我的境界。
各類“出神”的超現實體驗都很有震懾力,當年的氣功師就這樣真真假假地吸引了無數信眾,鐘明德也因這一奇特經歷改變了學術方向。他突然對斯氏的MPA有了新的領悟,把信眾們隨媽祖大轎狂奔數百公里的神奇經歷,解釋為在媽祖的精神力統率下進行的“超越身與意的表演訓練”;認為景頗族目瑙縱歌的歌場里,舞者通宵達旦的鳥步讓他們“借由反復的、專注的、松沉的、長時間的行走……從日常的意識狀態走入非日常的、當下的、自在的‘動即靜狀態”(153頁)。他更聯想到,格氏強調的訓練方法就是“力量的走路”(Walk of Power)。我把它比喻為帶有宗教意蘊的馬拉松,其結果據說確實能讓人產生精神逸出肉身的“感覺”——其實我這里想用“幻覺”,但我不確定那是真是幻,對于實際經歷者而言,大約是不“幻”的。從心理學角度分析,簡單、機械且長時間、超強度的運動令人極度疲憊,我猜是多巴胺分泌過度,容易導致人精神恍惚,獲得神秘與超驗的心靈感受,仿佛靈魂出竅,有人把這種狀態稱為“靈感”,有人說此時人可以進入潛意識領域,有人認為這就是創造偉大的藝術必不可少的前提,反正鐘明德覺得,這就是MPA的真諦。于是他開始在臺北的大學課堂上講授MPA課程,非常受歡迎。他越是深入思考和研究,越深感斯氏晚年的MPA理論與格氏(同樣是晚年)的MPA實踐之偉大,不免為珠玉蒙塵而感慨,立志要為戲劇界做個薦寶人。
對于滿腔熱情邀我對話的鐘明德而言,我是個煞風景的人。我知道人類對世界(包括對自身)所知甚少,所以不敢不信鐘明德所說的矮靈祭,不敢不信媽祖繞臺時信眾們的神奇體驗;我從小就聽說家鄉附近九華山的神奇,經常有鄰村老太太,在平地里走路都顫顫巍巍,居然能用小腳登上陡峭的山頂,這些都是我不敢不信的;而且我深信鐘明德是個誠實的學者,他看起來甚至比誠實還更多一點,稱其“忠厚”才合適。我完全沒有理由懷疑他的敘述,但是既然涉及戲劇表演以及演員的訓練,我想我還是有話要說。
我不喜歡怪力亂神。其實按鐘著的敘述,格氏對演員的要求與訓練完全無涉超驗領域。比如說,他認為演員最好的表演狀態是“不扮演角色”,更重要的是“將記憶中的身體行動發掘出來并建構成一套‘表演程式”;而導演的功能,就是協助眾多演員將他們各自的“表演程式”與劇場元素一起組合一出戲的“表演文本”,“演員們只要適當地執行他們各自的‘表演程式,即能夠進入有機的、自發的‘最佳表演狀態,而觀眾不僅可以看到角色、劇情,甚至可以感受到一場不可能或不可言說的表演”(81頁)。這段話簡直與戲曲表演的規律太接近了,如果我們不太健忘,還應該記得數年前京劇演員李玉聲就說,戲曲演員“不刻畫人物”,只是展示玩意兒,表現四功五法。格氏說的這個道理,戲曲演員天天都在臺上實踐,但我不相信戲曲演員都有通靈的功夫。
三
鐘著所述的所有與表演相關的體驗,都是在集體性的狂歡里個體的“出神忘我”狀態。如他所說,格氏晚年的演員訓練,目標就是用表演把所有觀眾帶入這種柏拉圖式的“迷狂”狀態。但我不知道格氏的成果如何,他用瑜伽式的訓練方法培養出了多少理查·奇斯拉克。我只想說格氏晚年已經對劇團演出沒有興趣了,或者說不屑,他講“藝乘”,訓練不是為“藝術展演”,只是為了獲得超驗的感悟,這是在修行。
鐘先生甚至想用他寫書的神速,說明他的“出神”體驗確實有效,在我看來近乎狡辯,畢竟他并沒有因此成為優秀演員。至于MPA,當然是重要的,如鐘著所說,巴爾巴培養了卡瑞莉,不過更重要的是,卡瑞莉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一直在刻苦練功;他甚至還舉了北京的陶劇場為例,陶冶就是這樣讓他的舞者日復一日地接受簡單枯燥的形體訓練,才有那些回歸身體的抽象舞蹈。其實他滿可以舉更多例子,每個戲曲演員在學戲過程中,都是每天無數遍地重復簡單枯燥的動作。這樣長期、艱苦的訓練,賦予演員自如地控制自己身體的能力,使之在舞臺上有超乎常人的表演能力,然而并不需要“出神”和“迷狂”。這是個持續與漸進的過程,我從未聽說哪位演員練功時突然發生蛻變,頓時成了大師。
我還想說得更實際一點,表演既是藝術,更是職業。舞臺表演是演員的職業,是日常人生,所以他不可能一直沉浸在超驗世界里。其實文學也是如此,盡管很多小說家都喜歡談論靈感,但我相信小說寫作是個漫長的過程,就算有靈感閃現也只是寫作過程中的瞬間。哪怕有作家和藝術家聲稱他們最優秀的作品是靈感來襲時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下筆如有神”,但我們每天所面對的文學藝術活動,卻基本上不是超驗領域的現象。優秀的演員,天賦、資質都重要,勤奮重要,全神貫注的投入重要,這些都在現實的層面上,無須涉及那個不可知的靈異空間。
所以我們才要討論訓練方法。我非常佩服鐘著對斯氏MPA之價值的洞察,說這是對斯氏的再發現也不為過。晚年的斯氏希望為話劇演員找到一套讓他們“從外而內”地解決表演難題的“身體行動方法”,然而從格氏始,他的傳人的繼續探索卻走上了另一條路。鐘著指出:“我們發現二十世紀幾位現代劇場大師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阿爾托、格羅托夫斯基、布魯克、謝克納到巴爾巴等,的確都受到東方劇場的感召或直接到東方取經……”(102頁)不過他說的“東方”,是印度的瑜伽,是濕婆,不是梅蘭芳。
我感覺從探討演員訓練方法陷入追求超現實的體驗,那是走火入魔了。我更希望把斯氏的MPA從天上拉回到地上,從濕婆回到梅蘭芳。它可以是一個既簡單又普通(或許有些殘酷)的訓練體系,通過有規律的、枯燥的身訓,讓演員掌握扮演各類戲劇人物的能力。戲曲演員接受的就是這種訓練,假如按斯氏的遺愿,能為話劇演員設計一個提升形體表現力的訓練體系,豈非很好。
然而,這是練功,不是修行。
我相信,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戲劇演員在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里,都只是在從事表演這個職業,那些神乎其神的靈異現象就算真有其事,也只是偶然中的偶然。這就是個技術活,所以要練功。練功是戲劇演員的必修課,如果講修行,大師才有份,那不是戲劇理論家發言的地方。美學或藝術理論,大到藝術學基本原理,具體到戲劇表演體系,不能只討論極端狀況,應該解釋與歸納最具普遍性的、常態化的現象;不能只關注大師,更應該從最平常的文學藝術活動中總結規律。所以,我們可以談MPA,但是把它看成是練功,不要將它變成修行。
(《MPA三嘆:向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致敬》,鐘明德著,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二0一八年版)
《定鼎中原之路——從皇太極入關到玄燁親政》(精裝)
姚念慈著定價:75.00元
本書關注皇太極入關、多爾袞攝政、福臨親政改革和玄燁結束四大臣輔政等滿族入主中原的重要歷史片段。歷史上的疑案或具體的事件其價值如何,在史學日益多元化的趨勢下,不可一概而論。同樣一件疑案,研究者的需要和目的不同,其價值亦迥異。價值判斷的前提是確認事實,后者必須建立在史料的鑒別和分析之上,即屬于實證。清代歷史上的許多疑案,原因不外是于統治者利害攸關,其原始過程和直接證據被當時的記錄者或后來的編纂者有意湮滅。若能還其本來面目,不僅可以揭示當時復雜的政治關系,往往也是破解歷史表象背后深層原因的關鍵。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