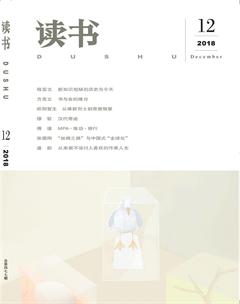在使用價值之內
徐敏
在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里,“在使用價值之外”是書中的一個章節名。按鮑德里亞的觀點,商品,是以其符號價值,成為構建當代西方消費社會之核心特征的。這一觀點,來源于馬克思對于商品之交換價值與其使用價值無關的分析,承接了盧卡奇、本雅明對基于交換價值的商品拜物教之論述。商品生產及其消費行為,在其深刻地影響著社會與文化的意義上,實則與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無關。這一觀點,是當前消費文化研究的一個理論基礎。
那么,商品的使用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功能與效用就真的與社會與文化之構成及其核心特征無關嗎?它只是作為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總體財富的物質承擔者,和商品交換價值的一個載體?而在日常生活領域中,各類商品所發揮的功能與效用之意義是什么呢?我們又能夠對社會生活中特定商品功能所導致的變化與影響進行理論論述嗎?或者進一步說,商品的使用價值就真的毫無理論意義嗎?針對這些問題,可能需要深入到商品交換已經結束的日常生活之具體形態中,也就是商品的日常使用過程中,重新思考特定的商品——比如家用電器——“只是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的東西。這就是汪民安《論家用電器》一書的基本理論主題。
家用電器是一類具有獨特使用價值的商品,其誕生,可以看成是一種由福特式工業生產方式、新型材料、電子與智能控制技術等不同產業整合制作出來的產物。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先是電燈,隨后是收音機、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微波爐以及新近的電腦、手機和空氣凈化器等等,逐次成為人們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耐用消費品。其中的一些,諸如錄像機或影碟機等已被淘汰或不常使用,更新型的家用電器產品還在源源不斷地到來。在西方發達國家,幾種主要家用電器全面進入到人們的衣食住行之中,并構成日常生活之基本配置,大約發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而在中國,家用電器的普及剛好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從八十年代初的黑白電視機、半自動洗衣機等開始,直到九十年代晚期,中國城市家庭才基本配備起了重要的家用電器產品。而在今天,如果把電腦與手機也算成是廣義的家用電器的話,那么,可以說,它們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數量與種類比以往更大更多了,它們在日常生活的意義也更為加強了。顯然,我們近幾十年來日常生活乃至社會之整體變化,都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種家用電器之使用價值的發揮,有著密切的關系。
家用電器不同于快速消費品,是相對比較昂貴的耐用消費品,且往往具有家庭固定資產的特征,有著更長的使用年限和更迭周期,能在較長的時間里給日常生活帶來一種相對穩定的形態。作為耐用品,它們也與家具等不同,是一種需要在使用過程中持續交納電費、自來水費、有線電視費、網絡費用的物品,有時還需要維修或保養。這導致其日常的使用過程具有了一種生產的特征,讓家庭室內空間呈現出一種工廠廠房的形態。同時,不同的家用電器還需要分設于家庭住宅的不同區域,比如電視機需要放置于客廳的顯著位置,洗衣機需要固定安裝在衛生間。這就意味著,不同的家用電器,還會對當代住宅的空間功能區分以及日常生活之時空分配產生一種相互協作的雙重影響。此外,家用電器都需要分別與電網、自來水管線、有線電視網及互聯網等更大的社會體系發生關聯,在不同的宏觀體系中,家用電器讓安裝與使用它們的家庭或個人,獲得一個固定的位置。人們在購買它們時,總要寫明家庭住址與聯系電話,以便連接上各類服務網絡。因此,不存在獨立且不依賴于社會體系的家用電器,這是一種存在于家電消費品與社會經濟及文化形態之間持續不斷的遠距離互動行為。我們購買了一臺電視機,就必須為之付出額外的電費與有線收視費,否則,電視機的使用功能就無從發揮。不僅如此,當我們購買了一臺冰箱時,外在市場形態就已經提供了食品超市,以及各類熟食、半成品及速食食品的產業。一般而言,冰箱的社會擁有量及其覆蓋形態,由于與城市住宅區的分布形態有關,這是導致超市如何選址的決定性因素。顯然,冰箱通過大量存儲食物而免去了每天的買菜行為,也重塑了人們的飲食方式與習慣,還非常明顯地影響到了城市的商業形態。冰箱由此讓家庭與一個工業化及全球化的食品工業構成了緊密的關聯。所以,家用電器顯著地增強了人們日常生活與宏觀社會形態的依賴。
家用電器之運轉,就是以其更高的便利性與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家務勞動的肉身化行為,減弱了日常生活行為的重復感與瑣事感。在今天,成套的家用電器,是現代家庭的標準配置。有了它們,日常生活就能獲得高度的自治與自足,這是一種隱藏了與社會宏觀體系之強化關系的自治與自足。或者說,使用電器同時在日常生活的個體化與社會化兩個看似相反的方向上,都進行了強化。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傳統的日常生活行為消失了,而一些新的日常行為則出現了。電視機、手機與電腦讓人們長期保持坐著觀看屏幕的姿態,這些電子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內容,總是使得工作、生活與娛樂的傳統區隔變得模糊起來。“洗衣機解除了衣服和婦女的勞動關聯。……甚至將婦女從一個勞作形象中解放出來,最終將婦女從這一受難式的被壓抑的文化視角中解放出來。”與此同時,洗衣機也大量減少了人們用手親觸家人的衣物的機會,而“電視的喧囂之家注定慢慢轉向一個電腦的沉默之家”。電燈讓家庭成員圍坐于油燈下分享故事的“獨特光暈”消散了,洗衣機瓦解了在河邊洗衣服的田園牧歌,還有睡前的捧書閱讀,以及大街上人們東游西蕩的漫游等等過往生活中各種細膩而珍貴的手工化、人際化與社群化事物都在悄然失去。
不止如此,家用電器讓肉身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要依賴于機器的程序與符號,而越來越不需要現場化的人際互動。它們在為人們提供更多的心靈自由以及更為復雜、更受外界符號信息影響的情感之時,又給人帶來了大量沉溺于純粹感官的無聊時光。經由電視機運作的“世界外在化”趨勢,讓人從中所獲得的娛樂,卻又是源于一個外在于我們的符號化與景觀化的表演世界,而并非一定是切身于我們的真實生活。這樣,家用電器確實在重塑一系列新型的家庭人際行為、人際關系以及主體之功能,人在家庭生活內部的主動性與自主性,開始下降為對于各種機器的高度依賴,各種人一機互動的家庭生活行為,讓人深陷于機器的程序及信息的編碼之中。事實上,家用電器之使用價值的發揮,導致日常生活在結構與功能方面產生了全新的雙重演變。在這種持續的演變中,電視機、電腦及手機,已經在為當代人建構出新的感知系統,冰箱、洗衣機、煤氣灶等等,則是我們的肉身工具,個體生活領域的主體性從而與包括家用電器的各種高科技商品的使用價值之功能密不可分。用拉圖爾的話來說就是:機器,尤其家用電器,在生活事務中承擔起一種“準主體”的功能,它們總在默默地從事家務勞動,是家庭的物質基礎。反過來說,使用家用電器的人,則相應地“淪為”,或“進化”為“準客體”。我們看似因這些物的環繞而變得更為完整與自足,同時又更是受宏觀社會體系的控制或制約。這樣一來,商品與其消費者,同時演進到一種相互依賴、難辨你我的“準”狀態之中,我們被以家用電器為代表的各種商品之使用價值所改造。
實際上,購買與使用家用電器,是當代社會對于人們日常生活提出的一種強制性要求。沒有家用電器,就沒有現代性的生活方式,這不只是從家用電器之功能角度而言的。在家用電器的符號價值方面,它們也是一種高度符號化的商品。它們都有獨特的物品形態、材質及各種標有符號的按鈕和屏幕,還總會附有使用說明書,使用者只有在仔細閱讀之后才能正確使用它們。由于大部分日常使用者對它們的內在技術原理并無深入了解,都只是家用電器“最初級的使用者”,家用電器的各種文本都是指令性的,它要求人嚴格按其符號標識來操作,這些規定行為是新型的生活技能,我們只是家用電器運行規則的一個遵循者而已。不僅如此,家用電器還會負載著特定的社會符號意義,比如一部標價昂貴的最新款智能手機,經常會是特定社會階層、文化品位與生活方式的象征。家用電器的內在技術體系及其演進,更會與社會基于技術的進步神話聯系在一起,似乎只有緊隨電子產業潮流,盡快購買與使用最新型的家用電器,我們才不會被迅猛發展的時代所拋棄。而家用電器制造商,又總是花費巨資,以大量的廣告及精心布置的店鋪而讓人們能夠隨時隨地地與之相遇,一部分的家用產品,本身就是符號信息的傳播中介。這樣一來,家用電器,在其符號價值上就構成了一種主導意識形態,即,只有擁有了家用電器,才能進入到不斷發展與進化著的現代生活之中。這種意識形態不僅暗含著對于生活世界及其文化形態的技術決定論,而且還發展為一種新型拜物教。這樣一來,家用電器就被理所當然地當作當代生活之核心代表性物品。
回過頭來再看當代中國家用電器的演進史與普及史,還能看到其中與西方國家不一樣的獨特社會及文化變遷軌跡及生活現象。那個沒有普及家用電器的計劃經濟時代,并非都如田園牧歌般美好。而在八十年代初,當中國民眾的商品生活仍處于全面短缺之時,一些人卻會花費巨資去購買一臺黑白電視機或半自動洗衣機。在隨后的市場進程中,收入不高的中國民眾也踴躍地花費更多的錢去購買大尺寸電視機、大容量冰箱以及其他各類新型電器。擁有家用電器,曾經是中國民眾擺脫長期的貧困生活,在物質與文化娛樂上獲得基本滿足的重要寄托。而在生產領域,通過在家電生產方式上吸引外資、技術與管理方式,如在深圳蛇口電子區,當代中國構建出了較為先進的生產力,逐步發展出了一個全球家用電器的第一大生產大國及全球最大的家用電器單一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家用電器,是中國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進入到經濟與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最重要領域之一。所以,家用電器之生產方式、交換形態及其使用價值,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又具有積極的歷史變革意義。
由此觀之,家用電器凝聚了中國當代日常生活世界之傳統與現代、貧窮與富裕、先進與控制的多重糾纏,只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基于交換價值的生產與交換形態,或是只從鮑德里亞的符號政治經濟學角度,闡明其控制性的消費意識形態,都會顯得忽略掉了當代中國獨特的歷史經驗與境遇。家用電器既是一種商品,是研究當代經濟及其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一個細胞,也是一種生產力,它具備著變革宏觀社會形態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潛能。這種潛能,本身就包含于家用電器的使用價值之中,而非處于其使用價值之外。
(《論家用電器》,汪民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