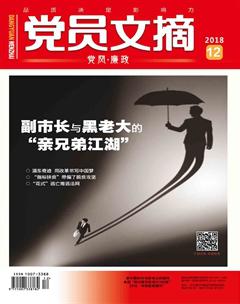貪官為何喜歡讀法學
滑璇 孫茜茜 朱岱臨
“億元戶”落馬高官的法學學歷
2016年10月14日,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金道銘因犯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大約20年前,金道銘在擔任中央紀委外事局局長、副秘書長期間,曾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班學習。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接受紀檢部門調查的副廳級(含)以上官員中,至少20人具有法學背景。以與法學相關的最高學歷計算,其中,博士6人,碩士11人(含在職進修),本科2人,另有1人參加過為期三年的法律專修科學習。
雖然這些官員的落馬與法學背景并無直接關聯,但懂法者知法犯法,以及個別官員被查后暴露出來的學歷摻水等問題,則值得深思。
“戲不夠,曲來湊”
頭頂法學博士、碩士光環的落馬官員,并非人人真正學過法律。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畢業于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專業;重慶市長壽區區委原副書記韓樹明,畢業于中央黨校黨建專業。但二人均為法學碩士。
這是因為,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發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里,法學不只是法律專業,而且包括了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公安學6個一級學科及其下42個二級學科。

法律科班出身的不多。最高法院原副院長奚曉明、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馬建、廣東省佛山市政協原副主席廖東明,這三人均畢業于“五院四系”(中國、西南、華東、中南、西北五所政法大學,北大、人大、武大、吉大的四個法學院),且多年從事法律職業。有些落馬官員的法律專業素養曾受到業界肯定。
有相當多的人的學歷出自中央或地方的黨校系統。比如,天津市委原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河北省委原政法委書記張越先在中央黨校函授學院學了本科政法專業,又在該學院在職研究生班法律專業深造。
“這里面似乎有一個規律,官員工作前的學歷、學校越差,深造、讀博的積極性越高。可能他們覺得有必要搞一個聽起來很嚇人的頭銜,戲不夠,曲來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祝守正認為,重慶市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便是這方面的典型。
據媒體公開報道,王立軍雖沒有法學學位,卻在十余年間成為國內外29所大學或研究中心的兼職教授、碩導、博導等。連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這樣的老牌法科院校,都曾向他伸出橄欖枝。
在法學圈里“摸爬滾打”30年,南方某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凌遠觀察到,官場刮起到法學院讀書風,要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說起。
當時正值中國高校擴招潮,研究生隊伍亦呈高歌猛進之勢。許多公務員選擇在職深造,一些剛剛獲批法學二級學科碩士點、博士點的高校則借機擴招。
與此同時,隨著國家的法治化進程和整個社會法律意識日益提高,法學在中國逐漸成為顯學。頂個法學博士頭銜的“學者型官員”,更是會被期許有法治思維、法治理念。
在趙凌遠看來,官員們喜歡讀法學,主要是因為它是當下顯學,與社會比較貼近。還有一些官員認為法學難度小,“相對好混”。
“門當戶對”
除“五院四系”外,官員就職所在地的大學常是首選。
季建業從擔任昆山市委副書記起,開始在蘇州大學進行一系列進修、深造,最終讀完碩博。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在保亭縣(當時保亭仍屬廣東省管轄)任職時,讀完了中山大學法律系的干部專修課程。
在法學理論、訴訟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國際法學等10個法學二級學科中,官員往往選擇宏觀抽象的法學理論專業,或與政府工作關聯緊密的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經濟法專業。
行政法方向尤其受歡迎,比如周本順、季建業。官員的工作經驗、對行政系統運行方式的了解,本身就是學術優勢,再適當融入一些理論分析,“把工作報告改一改就可以當論文了。有時候秘書就能完成。”趙凌遠說。
一些官員喜歡與自身行業相關的專業。在“大法學”內,安全機關出身的樂大克選擇國際關系專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湖南醴陵市委原書記蔣永清任職株洲時,讀了華中師范大學的中國現代化與城市發展研究方向研究生,獲法學博士學位。“小法學”內同樣如此。環保部門的官員,可能讀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博士;外事部門的官員,或許傾向國際法專業。
楊棟梁在中國政法大學讀博時,任天津市委常委兼市國資委主任。他的博士論文以天津開發區企業作為樣本進行分析,算是資源上的得天獨厚。
導師方面,較受官員青睞的,首先是輩分高、年資高的老教授;另一種是具有某些官方身份(如全國政協委員)或兼職的導師。
對此,祝守正將之稱為官員與學者間的“門當戶對”,“跟著一個在官場上地位較高的導師讀書,不僅可以獲得一個學位,或許還能找到某種庇護”。
這種具有政府背景的導師常與官員相識,可能是黨校培訓班的同窗,可能因為某些項目、課題、評審結緣。久而久之,那些愿意招收官員學生的教授已是口耳相傳、名聲在外。
利益層疊
在高校,碩士生、博士生常常被一些人認為是導師的“廉價勞動力”;但對于在職讀書的官員研究生,導師可能反要勞心費神地為其錄取、論文、答辯操心。
據北方某大學教師透露,幾年前,該校法學院開設了一種只招收司局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博士培養模式,報名者不僅要達到職級要求,還要出過專著或得過省部級獎項。為將某個不符合條件的領導干部收入門下,一名教授疏通關系創設了一個省部級獎項。此后,該領導干部順利進門。
“這里面肯定有利益,要不哪個老師愿意花費精力干這個?”曾在某高校法學院就職的劉穎告訴記者,導師門下的學生就業、官員親朋的子女入學、項目課題的申報審批、官場之中的勢力博弈……很多都涉及利益。
眾多利益中,最常見的便是給課題、拿項目。在法學領域,一個課題往往涉及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元的經費,課題分給哪個院系、哪個老師,經費也隨之轉移。雖然大部分課題分配前要經過招投標式的評選,但最后花落誰家,有時就是某個領導一句話的事。
隨著反腐形勢持續加壓,趙凌遠感覺到,十八大以來,官員進入法學院讀書的口子有所收緊。教育部及高校均出臺了一系列管理舉措,把關不嚴的現象近年來有所好轉。
記者曾梳理39所985高校的博士生招生章程,有21所高校明確限制在職博士的錄取,有的出臺控制比例,有的甚至明確“不招收”或“原則上不招收”。
在趙凌遠看來,一個學者一輩子帶一兩個官員博士生足夠了,“畢竟有損學術聲譽”。對于那些有學生落馬的導師來說,這種不慎重的、趨利性的選擇,很可能成為終身的污點。
(祝守正、趙凌遠、劉穎為化名)(摘自七一客戶端/《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