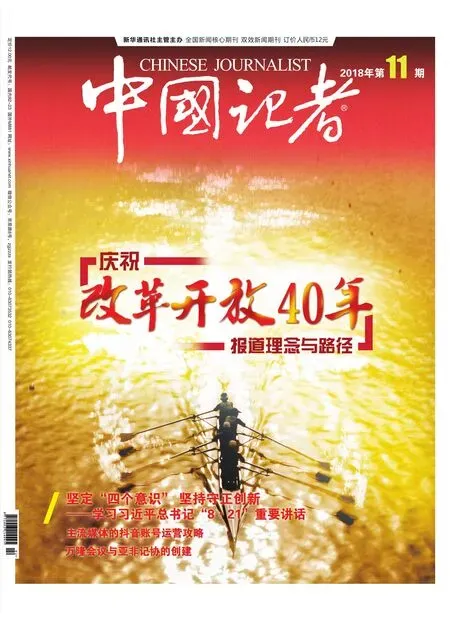移動短視頻的發展趨勢與思考
□ 文/王舒懷
內容提要 本文對移動短視頻市場的現狀與發展趨勢進行梳理,并對短視頻行業的發展提出建議。
2016年以來,國內先后經歷了短視頻熱和小視頻熱。關于兩者的區別,行業并沒有確切的定義。通常認為,所謂“短視頻”是相對于傳統的“長視頻”而言的,是指時長在10分鐘以內(多數在3分鐘左右),橫屏拍攝為主,專門為移動端創作或從影視作品分段碎剪而來的視頻內容。所謂“小視頻”,通常指那些手機拍攝,以豎屏為特征,時長在10-30秒的視頻作品,以快手、抖音、微視等平臺上的內容為典型。
無論短視頻還是小視頻,可統稱為“移動短視頻”。移動短視頻的興起,是近年國內互聯網內容的一個顯著趨勢。移動短視頻高速增長的背后,是移動終端的普及、數字技術的進步,是視頻生產、消費門檻的大幅降低,也是用戶視覺文化消費升級的需要。
一、視頻:從“傳統”到“移動”
先看數據,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全國移動短視頻用戶的MAU(月活)從1.54億增長至3.58億,增長132%[1];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全國在線綜合視頻的用戶總時長從6980億分鐘增長至7617億分鐘,僅增長9.1%,而同期移動短視頻用戶總時長從1272億分鐘增長至7267億分鐘,增長471%[2]。結合即將到來的5G時代,一個判斷是:移動短視頻市場正在經歷、并將持續處于高速增長的“風口”。
與“傳統”視頻相比,“移動視頻”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一)消費場景遷移
“移動”是這一波視頻熱潮的顯著特征。視頻消費的場景從電視到手機,發生了巨大的遷移。用戶從客廳走出來,走向豐富多彩的、基于碎片時間的移動場景。從而,用戶對視頻的消費需求,無論是數量還是內容本身,也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
(二)內容形態變革
從6秒到15秒、30秒,數分鐘……,不同于傳統視頻的敘事結構、表現手法,在移動端被創造出來。尤其過去一年間,以互動、豎屏、10-30秒長度為特征的小視頻發展勢頭猛烈。相對于傳統視頻樣態,小視頻更強調用戶生產、互動性更強、更能促進快速連續海量消費。從快手、抖音到微視,小視頻的內容更貼近網民生活,表現形式更豐富,生產門檻相對更低,尤其是在經歷了初期以個人秀、才藝表演為主的階段后,小視頻正在走向內容類型多樣化:新聞類、知識類、影視類、體育類、美食類等各種豐富的內容樣態被創造出來,參與生產者也從普通網民,擴展到機構和組織。
(三)分發鏈條創新
社交+算法,是這一輪移動視頻內容潮背后主導內容分發的力量。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內容產品,依賴以人際關系為核心的社交網絡獲得傳播。關注、推薦、點贊、分享等行為,在視頻傳播鏈條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信息流產品開始應用算法分發技術。個性化、“千人千面”大行其道。
無論算法還是社交,都意味著傳統的、單一的編輯主導的運營模式已經成為過去式,這是內容生產者必須面對的現實。
(四)生產生態重構
一方面,UGC內容越來越重要。今天,在越來越多的新聞事件中,我們看到,用戶上傳視頻成為傳統媒體的重要素材來源。某種意義上,今天的新聞工作者擁有人類歷史上數量最為龐大的視頻通訊員、攝像頭和義務拍客隊伍。另一方面,網絡原生的移動短視頻頭部機構初成格局,聚集了新興的視頻生產力。
過去兩年間,我們看到類似梨視頻、我們視頻、小央視頻,以及一條、視知等短視頻生產機構的興起。這些機構,無論是作為傳統媒體的新媒體項目,還是新興的商業公司,其共同特點是從出生起,就面向移動互聯網進行視頻生產,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傳統視頻生產的模式,基于互聯網進行生產組織,搶占了頭部內容,也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品牌。

□ 短視頻行業MAU增長突飛猛進用戶規模增長1億僅用半年,2018年4月MAU達3.6億。
二、“算法推薦”背景下,優質專業內容稀缺
如前所述,算法推薦的本質,是為了解決海量內容的分發。算法的本質是分發效率的提升,是海量長尾內容的傳播價值最大化。反過來,分發能力的極大提升,也反襯出優質內容供給的嚴重不足。
一方面,用戶在高度便利的技術工具的幫助下,創作出大量UGC內容,一個廣為引用的數字是,2017年,單單一個快手就創造了3.6億條視頻,其總時長是當年電視劇產出總時長的2850倍。但另一方面,針對移動端生產的優質專業視頻內容卻顯得格外稀缺。
其一,從生產主體看。傳統的專業視頻生產集中在各級電視臺手中,近年來,盡管各地電視臺也在大力推動媒體融合發展,積極靠攏新媒體,創造出類似“小央視頻”“時間視頻”“閃電新聞”等移動視頻品牌,但從整體看,電視臺內部“大屏”優先于“小屏”的思維慣性依然普遍,人才、機制的束縛始終存在,從傳統視頻向新興移動視頻的生產范式轉變尚未完成。一言以蔽之:大量的專業視頻生產力被束縛在廣電體制內部,并未得到充分釋放。事實上,新一輪移動視頻的競賽中,從梨視頻到“我們視頻”“澎湃視頻”“青蜂俠”,這些格外活躍的力量均來自傳統報業,本身便值得深思。
其二,從內容標準看。移動端重構了視頻生產的標準。變化了的消費場景,需要變化的內容。移動視頻并非簡單的長視頻分割拆條,而是在“短”時長下的敘事方法、剪輯手法的重構。過去兩年,市場上涌現了一批以梨視頻、我們視頻、一條、二更、視知等為代表的專業短視頻生產機構,這些機構生產的內容,以短時長、強現場、素材原生態、快節奏、標配字幕、社交化傳播為特征,在某種意義上重新定義了移動視頻的表達方式,也拓展了移動視頻表達的邊界。但是,從全網的角度看,這樣的內容依然高度稀缺。
其三,垂直化、地域化的內容稀缺。算法的應用,使得長尾海量內容的分發成為可能。今天的個性化分發,完全可以做到針對一個人群、一個地區,甚至一條街、一幢樓的精準推送。然而,分發顆粒度的極大精細化,對應的卻是專業內容不足的窘境。源于普通用戶、攝像頭的海量視頻內容,并沒有得到專業而有效的處理;三、四、五線城市及廣大農村地區的豐富突發事件、生活場景、人物故事、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專業化的視頻記錄。這些內容,原本可以在“本地化”的標簽下,為用戶提供貼近身邊的優質視頻。
三、視頻生產機構:去專業化與再專業化
對于傳統媒體和機構視頻生產者來說,適應移動視頻時代,激活自身生產力,推動自身融合發展,需要重視如下幾點:
一是生產組織上,需高度重視與UGC的結合。討論移動互聯網條件下的視頻生產,不能離開UGC內容極大豐富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專業拍客、政府及企業宣傳員、攝像頭還是視頻平臺的普通用戶,都在源源不斷地生產并上傳大量視頻素材。對于機構生產者和專業視頻生產商而言,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基于UGC內容,建立一套全新的組織、收集、核驗、再制作、分發運營的流程,如何將UGC內容納入原有的專業標準通道并實現兼容。
事實上,梨視頻最核心的資產,正是其拍客體系的組織建立。充分依托互聯網提供的組織能力利用好UGC內容素材,而非固守要求所有的素材都由機構自身生產,這是一種清晰的轉變。
二是生產標準上,要針對移動端特點進行重新定義。所謂“時長確定語法”“場景決定體裁”。移動視頻時長短、消費場景碎片化,決定了其生產專業標準必須依照移動端的特點進行優化。相較于傳統視頻,移動視頻天然更傾向于那些強現場、強轉折、強沖突、強視覺選題類型,而拒絕口播、演播室、空鏡等傳統視頻制作的常用場景;在剪輯手法上,必須開門見山,直奔主題,快節奏、高密度,以便在相同短的篇幅內轉達更多信息,而無法做到傳統長視頻那樣的從容敘事。在此過程中,新的視頻生產標準有待重新定義。
三是生產運營上,需高度適應移動端特點。一是要適應算法分發的需要,從選題確定、標題制作、標簽填寫,都要考慮算法分發的需要;二是適應社交傳播的特點,充分考量視頻作品在社交網絡中如何激發用戶的社交傳播欲望,尤其是分享欲、參與欲、收藏欲。三是高度重視用數字指標指導精細化運營,并進一步指導內容生產。無論從內容標準、生產組織還是運營方式看,對機構生產者而言,移動視頻發展都面臨一個去專業化和再專業化的過程。舊的規則在打破,唯有整個行業不斷創新,才有可能建立新的共識。
(作者是騰訊新聞視頻運營總監)
【注釋】
[1] Trustdata: 2018年短視頻行業發展簡析,2018年5月
[2] QuestMobile:中國移動互聯網2018半年大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