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制造的真實幻覺
☉[英]克萊夫·詹姆斯 著 喬曉燕 譯
開始時的海明威
上一次讀《太陽照常升起》的記憶已經(jīng)模糊,腦海中只留有一些零星的細節(jié)。但這些細節(jié)栩栩如生——巴黎的栗子樹、潘普洛納奔跑的公牛——足以讓我記起彼時讀它的感受:那種鮮活而生動的強烈沖擊,昭示著一位年輕的作者正邁開大步殺入文壇。第一次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也是一名年輕的寫作者,但那時尚沒有找到自己的寫作之路。這本書曾讓我心生妒意。
多年以后,我的寫作生涯即將結(jié)束,重讀此書,心中的妒火已然漸漸淡去——顯然,海明威那獨特的個性讓他一次次想要了卻自己寶貴的生命——但他平實而簡潔的寫作風格仍然叫人著迷。書中的對話一再重復(fù),似乎每個角色都是彼此的回音壁。更糟的是,每遇喝醉,他們連自己說過的話都要一遍遍重復(fù)。盡管這不免讓人有些煩躁,有時卻也恰到好處地使人不禁莞爾一笑。例如邁克,作為書中始終如一的酒鬼中的酒鬼,當他第二次對那個老婦人說“你的包砸到我了”,就讓人感到滑稽。因為不過幾秒鐘之前,他已如此說過一遍。他或許是已經(jīng)全然忘記了自己曾說過同樣的話,又或許是覺得沒有人能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才會一再重復(fù)。年輕人對于酒精的威力沒有概念,渾然不覺中已經(jīng)爛醉如泥,接著便往往這樣絮絮然念叨。五十年前,我也曾如此。
書中的主角個個年輕,幾乎沒有過去。因為年輕,他們活在當下,并且也只能如此。因而他們反而裝出一副久經(jīng)世故的樣子。書中的主角杰克·巴恩斯是海明威的化身。與海明威不同的是,他的過去并非由謊言編織而成。杰克或許是作者自我形象的投射,但這不僅僅因為杰克在性功能方面的障礙。當然,海明威相貌英俊、充滿活力,如果他有這份心,女人們都會趨之若鶩,但他卻常常在女人面前手足無措。杰克在美麗放蕩的貴族夫人布萊特·阿什利面前也感到無能為力,毫無疑問,這正是海明威內(nèi)心欲望和現(xiàn)實沖突的真實寫照(在現(xiàn)實生活中,海明威第一次去潘普洛納時,即便有第一任妻子哈德莉陪伴,海明威還是被達芙·特懷斯登夫人所吸引,并與一個名叫哈羅德·洛布的猶太人爭風吃醋,大打出手,原因是洛布曾成功勾搭上特懷斯登夫人)。與海明威不同的是,杰克的性無能更多地體現(xiàn)在身體機能而不是精神層面上。他的身體究竟受過怎樣的傷害,書中并無交待。海明威在后來偶然談到,杰克在一次飛往南方前線的戰(zhàn)役中受了傷,并做了截肢手術(shù)。正因為如此,杰克和布萊特彼此吸引,卻無能為力。對于杰克和布萊特是否有過其他的親密行為,書中并無描述。只有一章頗為神秘地指出,兩個人給予對方很大的滿足,卻最終讓彼此心里更覺沮喪。

豪飲中的海明威
今天的讀者或許認為這是作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現(xiàn)。但海明威讓杰克成為戰(zhàn)斗機飛行員,這一寫法倒是充滿了想象。海明威對這種想象樂此不疲,正如盡管曾被莫里·卡拉漢打倒在地,他還是把自己想象成拳擊冠軍(卡拉漢的《在巴黎的那個夏天》我也必須重讀一遍)。海明威本人在戰(zhàn)爭中是在陸軍服役,盡管不是空軍,卻也承擔著身負重傷的風險。即便如此,他在講述的時候,也編織了不少謊言。談及每一次戰(zhàn)役和自己的受傷情況時,必然都添油加醋一番。在后來的《永別了,武器》中,海明威讓主角受傷慘重,奄奄一息,似乎天使護士凱瑟琳是將他從死神手中奪回。不過實際上,在《太陽照常升起》中,海明威已然在這方面走得更遠。氣質(zhì)高貴卻又有著性功能障礙的杰克,海明威在塑造這個自我投射形象時,不僅給了他更多的傷口,還給了他翅膀。
海明威并非唯一一個把自己寫成優(yōu)秀飛行員的作家。福克納也想這么做,但是真相最終敗露了。事實上福克納是開過飛機的,然而從未開過戰(zhàn)斗機,但他有意誤導(dǎo)人們,讓讀者以為他曾當過戰(zhàn)斗機飛行員。海明威的做法則是總為讀者留下想象的空間,使讀者相信,在二戰(zhàn)期間,他曾解放巴黎,并英勇作戰(zhàn),以至于人們不免為他身邊人的安危擔心,希望他能離開戰(zhàn)斗。他在戰(zhàn)斗中為自己設(shè)定的任務(wù)多半匪夷所思、不合常理,但在敘述過程中他總能給讀者留出想象的空間,讓他們相信自己瘋狂的行為是出于戰(zhàn)略目的,是同盟軍重要的軍事行動,甚至使人相信他曾徒手擊沉德國潛艇,使其沉入海底。
現(xiàn)實生活中,很多作家都是撒謊大師。也許在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他們都會這樣——畢竟現(xiàn)實生活不可能像小說那么跌宕起伏、多姿多彩。詩人詹姆斯·迪基在二戰(zhàn)期間曾駕駛過P-61黑寡婦夜間戰(zhàn)斗機在太平洋海域執(zhí)行任務(wù)。你可能覺得這樣的服役記錄已經(jīng)足夠浪漫主義了,但迪基不滿足于此。他暗示讀者自己曾經(jīng)參與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以此經(jīng)歷來裝點自己的門面。不幸的是,這樣自編自導(dǎo)的傳奇故事影響了他的寫作生涯,莫須有的負罪感讓他不堪重負。即使在描述事實的時候,為了增加自己的重要性,他也要極力渲染。海明威有同樣的癖好,當他發(fā)現(xiàn)看似客觀的敘述風格能給現(xiàn)實生活中的自己增光添彩時,他就習慣性地故伎重演了,在本該踩剎車的時候,他卻踩下了油門。結(jié)果,他后期的作品因此而大打折扣,即便在需要低調(diào)陳述的地方,他也顯得高調(diào)夸張了些。但在寫作《太陽照常升起》時,他尚在測試這樣的手法對讀者究竟具有多大的吸引力。
在海明威筆下,羅伯特·科恩這個角色并無多大魅力,讀者可能會覺得他有些反猶太傾向。除此之外,海明威一再使用“黑鬼"這個詞,也讓人感到些許不安——當然這要由教師和出版商來做最后定奪。他們當中很多人是非洲裔,對海明威的做法卻似乎不太反感。或許他們認為海明威這本小說不過就是加長版的短篇小說,只是流行讀物而已。這本小說是否能作為經(jīng)典流傳下去,還有待爭議。當然,在我的有生之年,它確實是一部經(jīng)典之作,但我的歲月將要走到終點。雖然如此,在我的生命之光熄滅之前,我愿意再讀一遍這本小說,再感受一下杰克和布萊特之間那種古怪、克制,卻又充滿情欲的對話,仿佛話語就是對彼此的一種愛撫方式。整部小說都是個隱喻,可在這書中,你幾乎很難找到明喻或者暗喻。海明威只在一句話中將一個事物比作了他物。他說,在杰克心里,布萊特可愛的形體有著賽艇外形的弧度。理智告訴我們,將女人的身體比作船只會讓人覺得頗為怪誕,可這一不同尋常的比喻卻俘虜了我們的心。
海明威最后的日子
卡洛斯·貝克的《海明威傳》是我閱讀的第一本關(guān)于海明威的傳記。后來的日子里,各式各樣的海明威傳記不斷涌入我的書房,其中有些作者是在海明威成名之后才出生的,而現(xiàn)在的一些作者,則是在海明威自殺之后才出生的。有些學者在研究海明威之前,是講授美國文學的教授,現(xiàn)在則全力投入到了對海明威的研究事業(yè)中。一直以來,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總能夠不斷推出新的海明威傳記,書中偶爾還會出現(xiàn)一些新的人物史實。
依照我的經(jīng)驗,即使你不去讀這些書,也至少會購入其中的五六本。我想,讓我不停閱讀海明威傳記的原因大概和其他作家不停為他寫傳記的原因一樣:他是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除了海明威之外的作家,即便是鄧南遮,也不過是個小丑而已。海明威的個性復(fù)雜而奪目,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只能說是他生活中一角。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件好事。美學追求也從來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不僅通過射擊和捕魚來衡量自己的男子氣概,也通過寫作來驗證這一點。射擊暴怒的獅子,或者坐在椅子上和馬林魚搏斗一天之后,再用沖鋒槍掃射那些聞到血腥味前來的鯊魚,這些對于海明威來說,都不足以證明他的勇敢。他希望我們羨慕他那將最后的手稿修改323次的勇敢精神。這個數(shù)字是他自己說的,如果我們懷疑這是他編造的,他會感到憤怒,非常憤怒。因為誠實和精確正是男子氣概的一部分。
但對于海明威來說,他是雙性同體的,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他的男子氣概與敏感脆弱正是他性格的兩極。作為一個作家,他想要將這兩種迥然不同的精神特質(zhì)統(tǒng)一于一種風格之中。在某種程度上他成功了,尤其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即便在沒有成功的時候,他也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這風格是一種病毒,有志于寫作的年輕人以為這些都是真實的生活,但事實卻是,海明威在編造的時候總是非常具有說服力。
《永別了,武器》中有一個著名的場景,叫做“卡波雷托撤退”。這是海明威的經(jīng)典片段,和短篇小說《大雙心河》里的場景一樣富于真實感。其實,海明威從來沒有目睹過卡波雷托撤退,那是發(fā)生在他去意大利前一年的事情。他只是擅長將自己讀過的或聽到的事情寫成令人信服的故事而已,甚至有些謊言也能如此改裝。總之就是,他善于制造真實的幻覺。
這樣做的時候,海明威能讓自己的追隨者身不由己。我剛剛讀完保羅·亨德里克森的《海明威的船》,講述的是1934到1961年間,海明威和他的漁船“比拉號”在基韋斯特和古巴漂流的故事。這艘船帶著它的主人經(jīng)歷了與大魚和德國潛水艇之間搏斗的種種險境。魚是真實存在的,而關(guān)于德國潛水艇,作者只是宣稱可以提供其位置的有用信息——其實純屬子虛烏有。
這本書足足有700頁之多,但我全部讀完了,也并不后悔自己在上面花掉的時間。亨德里克森是個很有毅力的“硬心腸”,對海明威的夸大其詞窮追不舍,也沒有被海明威的名氣嚇著而認為海明威根本不需要吹牛。當然,偶爾會有一些瘋狂的小矮人夢想自己成為巨人,而海明威,他是夢想成為巨人的巨人。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古巴的時候,那時候卡斯特羅還在到處演講,我去過方卡西亞的海明威故居看到了他筆下的“比拉號”。因為房屋地板正在塌陷,禁止參觀者進入,但從窗戶望去,可以看到里面的整面書墻。地板上有一雙松幫鞋,如兩只小船大小,并排擺在那里。從這些可以看出,海明威是從大人國來的。
盡管亨德里克森了解到關(guān)于海明威的事實,并以此為傲,他還是不可避免地被海明威的風格所感染了。當海明威捶胸頓足地吹自己時,亨德里克森忘記指出,如果普通的作家如此大言不慚,即使并不過分,通常事實也會證明他寫作技巧之低劣。不管怎樣,亨德里克森在與海明威的精神碰撞之中,保持了神智的完好。而海明威的大腦,則早在自殺之前,已經(jīng)如同一團亂麻了。
肯尼思·S·林恩1991年出版的《海明威》又是一本長達700頁的謊言。盡管林恩的這本書沒有擺出婆婆媽媽的寫實姿態(tài),讀來卻更令人感到沮喪。它讓你徹底失去信心,不再寄希望于海明威是漸漸地患上了某種疾病。是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存在。和里爾克一樣,他那神經(jīng)質(zhì)的母親對他十分溺愛,把他當作小女孩一樣撫養(yǎng)長大。在他提前結(jié)束了的整個一生中,海明威一直充滿著性別焦慮,即使將自己塑造為一流的運動員和動物殺手都無濟于事。酗酒當然也對他毫無用處。實際上,最讓人痛心的正是他的酗酒惡習。酒精在損傷他的大腦,這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jīng)初露端倪。其他作家與海明威相比,即使是爛醉如泥的福克納,也像是個禁酒主義者。奇怪的是,我們一直認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才是酒鬼,而海明威則是個自律的硬漢。海明威在《乞力馬扎羅的雪》中寫了“可憐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幾個字,像魔咒一樣,在之后的數(shù)十年里,它削弱了菲茨杰拉德的形象。這個形象甚至在他離世之后數(shù)年里還在通過媒體傳遞給世人。在現(xiàn)實當中,海明威才是那個不可救藥的酒鬼。但他卻如此善于塑造自己的硬漢形象,他那自律的形象已然深入人心,或許還會一直持續(xù)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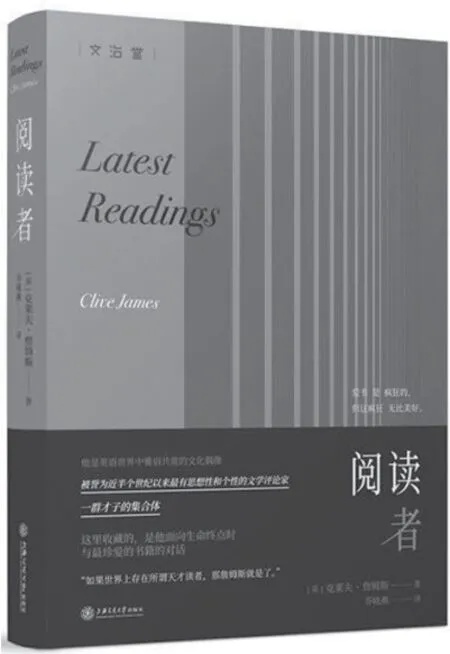
這其中自有緣由。德懷特·麥克唐納所言不虛:《老人與海》的矯揉文風的確緣起于人們所謂的“自律”,但在其過分追求簡單的浮夸風格之下,視覺化的寫法的確生動有力,具有恒久的吸引力。海明威不是深諳此道的唯一作家,勞倫斯在描寫山間清澈的溪流時也同樣出色,但仍無法與海明威媲美。這也是閱讀海明威時不可錯過的。用年輕人的話說,海明威對此頗有一手。
不幸的是,當你繼續(xù)深入下去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致命的缺陷:性別的雙重性是一個他永遠不會去直接面對的問題,只會隱約暗示。對于一個反抗一切限制的作家而言,他自己的內(nèi)心卻是一個禁忌的話題。他最大的悲哀在于,他永遠無法去書寫自己的終場,而這終場上演的時間之久,完全可以成為作品的一大主題。
對于一個沒有突然離世的作家而言,體力日衰可以是他的一個新的寫作主題。但海明威即使有時間,也無法處理這個問題。一次次的頭部受傷讓他無法集中注意力。他站在皇家打字機旁猛擊(他都是站著寫作),一遍又一遍地敲出相同的句子,這就是他吹噓的所謂修改了無數(shù)遍的手稿。即便他的身體狀況良好,他的內(nèi)心也抵觸自己的真正需要——誠實。
因為這真實的現(xiàn)狀會被寄生蟲一樣的媒體視為軟弱的象征,而他害怕這一點。所以他選擇的出路是毀滅自己。但他不應(yīng)當這樣做。他留下的殘局,需要他所愛的人去清理,而對于這些人,他知道自己是個負擔。這樣的行為無法稱之為勇敢。然而,如果論及他的偉大不朽,能說的也就是,我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