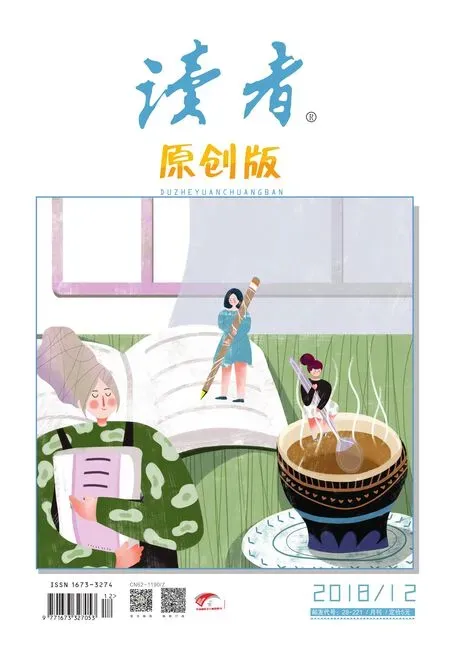父親的存在感,是需要用心刷的
文|刮刮油
一
我兒子兩三歲進入第一個叛逆期時,我對他嚴厲過幾回,表情兇,聲調也高,事后又覺得自己有點過,于是第二天便會買糖和玩具回家,以示補償。
有一回,他因為把飯扔了一桌子而遭到我的嚴厲批評。晚上,我聽見我愛人教育他:“你這么浪費飯菜對嗎?”
“不對。”
看來批評還是有點效果的。哎,剛才態度有點嚴厲,畢竟孩子還小。我心里泛起些許憐惜,我的耐心還需要修煉啊。
“那你還浪不浪費了?”我愛人繼續問。
“還浪!”我兒子回答得很干脆,“我爸會給我買吃的。”
你以為你是孩子的良師益友,其實孩子只當你是“傻瓜提款機”。
二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這個人對“男人可以不修邊幅”“男人以做家務為恥”之類的想法相當抵觸,于是,很早便決定從我做起,做一個絕不湊合的人。這是對他人的基本禮貌,也是起碼的生活態度。
我總說每個孩子都是父母的“照妖鏡”,從孩子這面鏡子中看到的是神還是魔,大多是自己的映射。所以,我希望我在兒子心中是一個干凈整齊、樂于參與家庭建設的爸爸。

一年多以前,我帶兒子去參加一場籃球比賽,因為他當時頭發比較長,所以我給他打了點兒發蠟。教練看到他后說:“你頭發怎么這樣?你看看別人,老爺們兒不留這種頭發!”我環顧四周,男孩子們果然是一水兒的寸頭。其他孩子聽到這話,開始擁上來摸我兒子的頭發,并以此開他的玩笑—這讓他很尷尬,我則很難過。
于是,我開始留起頭發,最長時幾近披肩,到現在也沒有剪。
我對外一直說,蓄發是我面對中年危機前的最后一搏,但實際上我是想傳遞給我兒子一些信息。
首先,一個男人“爺們兒”與否不是靠發型來判斷的,你完全可以說男人要追求勇敢、善良、正義,要有愛心、有同理心、有擔當。但可惜的是,一些淺薄的標準依舊橫行于世。
其次,你做出的選擇,要源自自己的內心。面對同一件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你如果全要聽,那么勢必會走上“父子抬驢”的老路。
還有,大多數人在做的事并不一定就是正確的和適合自己的事,要堅持自己的原則。就像足球隊里那一片“和尚頭”,你也去學,你一個頭小、腿長、頭發軟的人,除了把自己整得像火柴,并沒有什么好處。
我的良苦用心果然取得了成效,因為我在某一天發現了這么一幅畫—畫上我手拿吹風機,頭發在風中飛舞;旁邊配有一行字:我爸爸他每天chui(吹)頭發。
拋開錯別字和這么大的人了還用拼音的問題,我敢肯定我這段時間的努力確確實實被他看到了—畫上我那滿足的笑容、幸福的眼神,那隨風飛舞的頭發,無一不將我內心的驕傲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