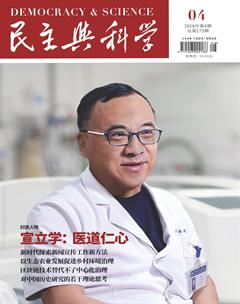陸侃如,何妨吟嘯且徐行
余江 李楠
當重病在床的九三學社社員、著名學者陸侃如聽到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消息時,他用顫抖的手奮筆寫下“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精神”、“迎接五屆人大的勝利召開”以及“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等話語。1978年12月1日,陸侃如逝世,享年75歲。“以言教訟,以身教從;得經師易,得人師難。”這是陸氏門生對陸侃如先生最深切的懷念。
“我忍不住要來嘗試一嘗試”
“胡先生以為《天問》是后人雜湊的,因為‘文理不通,見解鄙陋。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天問》里有許多很深刻的疑問,如‘登立為帝,孰道尚之之類,決不是后代腐儒所能偽造的……”(《陸侃如和馮沅君》,許志杰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第36頁)這是1922年,年僅20歲的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陸侃如,對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胡適的觀點的批評。胡適先生看到后,覺得陸侃如說的很有道理,但未曾想到這樣的“挑戰”竟出自一位只有20歲的大一新生,陸侃如的名字給胡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陸侃如的“挑戰”并非故作驚人之語,在他看來研究要有一定目的,要解決一定問題。在北大,陸侃如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先生的影響;在清華研究生院,陸侃如在課堂上曾受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大教授的影響,思想上融合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開闊了他的視野。然而,當陸侃如開始反思中國文學史的現狀,感受到“個個人都詛咒中國無好文學史,個個人都希望中國有好文學史,然而沒有一個人肯自己動手做一部文學史”的危機時,陸侃如忍不住要來嘗試一嘗試。《中國詩史》這部近60萬字的皇皇巨著便應運而生,這是陸侃如與妻子馮沅君共同的“結晶”,在論述一些作家作品時,常常能打破傳統,解決無人改正的問題,這非一般意義上的“嘗試”,更是一種“挑戰”,體現了一種敢為人先的勇氣!
為探尋更多的未知,1932年,陸侃如與馮沅君共同告別了當時任教的上海中國公學,來到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留法期間,陸、馮二位先生一同參加了法國著名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領導的“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同盟”運動,他們與戴望舒、李健吾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都是其中“中國留學生支部”的重要成員。他們積極宣傳反戰思想,并把中國文化傳播到法國。陸侃如將《左傳》用法文譯作《左傳考》,在歐洲發行;同時,他又將法文版的《法國社會經濟史》譯成中文,在國內刊發。此舉,讓法國人了解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讓更多中國人了解到法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對學術、對工作的熱愛,也讓陸侃如開了很多風氣之先。任山東大學副校長期間,陸侃如參與創辦了全國高校第一本學術刊物《文史哲》,深受讀者喜愛,陳毅曾說:“大學就是要通過教學與科研,為國家培養合格而又對路的有用人才,而學報正是檢驗這一成就的標尺。山東大學創辦《文史哲》是開風氣之先,已引起全國各大學的重視。”正是因為當時的“嘗試”,時至今日,《文史哲》這部學術刊物,仍然發揮著標尺的作用。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20世紀的中國,從來不缺少傳奇和悲劇。陸侃如也與這個風云變幻的時代交相呼應,見證了中華大地的滄桑巨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在燕京大學任教的陸侃如積極投身到抗戰活動中,因為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單,他不得不離開自己熱愛的學校。誓死不當亡國奴的陸侃如攜妻南下,來到安徽大學任教。不到一年時間,戰局進一步惡化,只得再次遷徙,經上海、香港至云南昆明。到昆明后,陸侃如接到中山大學的邀請,陸、馮二先生又折回廣州,任中山大學師范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42年6月,日本侵略者攻占粵北山區小鎮坪石(中山大學于1940年遷至此)。同年秋天,陸侃如與馮沅君被迫離開廣州,來到因戰遷至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任教。直至抗戰勝利后,才隨東北大學遷回沈陽。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這是杜甫在《詠懷古跡五首》中抒發的感慨,抗日戰爭期間,陸侃如與馮沅君歷經大半個中國,借用這一詩句來描述陸侃如伉儷在抗戰時期的人生經歷,似乎頗為恰切。
1942年,由廣東入川,受邀任教東北大學的陸侃如與馮沅君,不僅教書育人,而且一如既往積極投身救亡運動,深受廣大愛國師生的擁戴。抗戰期間,除陸侃如與馮沅君外,眾多知名學者如高亨、楊榮國、姚雪垠等均內遷任教于東北大學,四川三臺縣遂成為重慶、成都、桂林之外,國統區的一個重要文藝據點。1945年1月6日,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務部主任老舍先生委托,“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川北分會”在三臺成立,陸侃如為川北分會主席,馮沅君與趙紀彬先生為副主席。作為川北分會會長的陸侃如,常號召大家舉辦多種多樣的活動來宣傳抗戰精神,如組織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五五詩人節”以及慶祝作家茅盾50壽辰的活動等。位于三臺東門內陳家巷的陸侃如與馮沅君的家作為諸多活動的策劃地,熱鬧成為了常態。
即便在流徙播遷的戰爭年代,陸侃如也心心念念著他的文學史研究,他常反思自己過去所做的研究:“經過若干年的摸索之后,深深感到過去走過的路都不十分對。”即便已完成取得無二成就的《中國詩史》,他仍然在思考、嘗試著如何才能寫出一部更好的文學史著作。他認為文學史的工作要具備樸學、史學與美學三個步驟。所謂樸學的工作,是初步的準備,是“對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訂,字句的校勘訓詁等”;所謂史學的工作,是進一步的工作,是“對于作者的環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當時社會經濟的情形,必須完全弄清楚”;所謂美學的工作,是最后一步,是“對于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說明作者的寫作技巧及其影響”。三者融合才能寫出一部完美的文學史。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從1937年到1947年,陸侃如在其人生最不安定的十年間,精細考證、旁征博引,搜集論證了大量資料,初步完成了那部82萬字至今仍影響著中古文學研究的巨著——《中古文學系年》。這部著作,全面考證了上自公元前53年,下至公元340年這400年間152位文學家的生平事跡。
給后人留下點什么
陸侃如身后,留給世人的是豐厚的精神和物質遺產。
對于一生致力于教學、研究的陸侃如來說,并沒有想刻意留下什么,但他的著作已為中國文學史的現代研究提供了豐厚的養料。
《中國詩史》問世不久,即產生較大影響,在當時數十種文學史著作中,魯迅先生只推薦了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陸侃如與馮沅君《中國詩史》、王國維《宋元詞曲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五種。1946年,趙景深先生在《中國文學史新編》一書中對陸侃如的文學史著作也多有引用。直至問世20余年后,“《中國詩史》還是一部唯一的詩歌史著作。”
在陸侃如看來,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是兩門有著嚴格區別的學科,但在陸侃如所處的時代,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少學者都持相反的態度,他們質疑陸侃如與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簡編》,認為書中對文學批評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陸侃如回應道:“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是兩種工作,似乎應該有所區別;在文學史上對于某些重要的文學理論可以介紹一些,但文學史所能給予劉勰的篇幅和文學批評史所能給予的恐怕不會一樣多,也不該一樣多。”時至今日,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已發展成為兩門獨立學科,再回顧陸侃如的觀點,更足見其敏銳的學術遠見和之于中國現代學科建設的重要指導意義。
身為人師,陸侃如為國家培養了很多專家學人。例如,20世紀60年代師從陸侃如的牟世金,在陸侃如指導下從事《文心雕龍》和魏晉六朝文論研究,這位“龍學家”的著作得到了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高度肯定,當代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曾評價牟世金為“《文心雕龍》的功臣”。新中國解放后最早從事辭賦研究的專家、陸侃如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畢業后留母校山東大學任教的龔克昌先生回憶:“我當陸師的研究生時,常常有意‘刁難先生。大家都知道漢賦生僻字一大堆,令人生厭。我常忽然提出一些生字來‘考他,我總以為能難住他,但他每次幾乎可以不看上下文便隨口作答。問一些比較隱蔽的典故,他也能一眼看穿。我注釋白居易詩文時,有一個句子弄不清,專門跑去問一位專治唐代文學的專家,也不得其解;又去問一位語言文字專家,同樣也說不清楚。但我隨后問陸師,他好像不假思索地就給我解決了。”
作為20世紀中國舉足輕重的著名學者,陸、馮二位先生的收入,相對而言,一直頗為可觀,但他們的生活卻是極為儉樸的。陸侃如的弟弟陸晉如曾回憶道:“在上海教書時,走在街上,人們認為他不過是個普通的窮教師。大哥大嫂在解放前和50年代,對講究吃穿的人,一直是看不慣的。他們自己生活儉樸,內衣補了又補,不肯換新的。家里的用具,如水壺、鍋盆等,大都是修補過的。”他們的錢多用于資助教學、雜志出版、地區經濟建設等等。陸侃如臨終時留下遺言,將全部4萬多元積蓄,其中三分之一留作繼母和弟弟的生活費,三分之二悉數捐給學校,作為獎學金以鼓勵青年學者開展研究,另將全部藏書也捐給學校。
今天,我們深切懷念于改革大潮隱現之初辭世的陸侃如,不僅為追慕一代卓越學人榜樣,為現代中國社會描摹一個堪當文人先賢的精神畫像;同時,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值此國運昌盛、學術繁榮之際,追念對民族解放、國家富強、文化傳承、學術創新孜孜以求于一生的陸侃如,也更頗具告慰的意義。
(作者分別為天津外國語大學副校長、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傳媒學院教師)
責任編輯:鮑家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