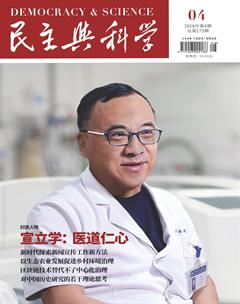一段不該被忘卻的中國植物學研究史
周浙昆
“1941年,在昆明西北郊的大普吉壩子里的陳家營東邊小河旁,有一座破爛不堪的土主廟,那大殿里土主神像旁也就容得下一臺石印機和一張看標本、繪圖的大方桌。繞著這臺石印機,經常有三或四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忙乎‘轉悠著,轉了3年到1943終于‘轉出了一本自寫、自畫、自印而成的《滇南本草圖譜》。” 這段文字摘自于吳征鎰院士在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日為《滇南本草圖譜》重新刊印而作的跋文。這段文字道出了在抗戰時期從事植物學研究的艱辛和老一輩科學家為科學救國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也是一段中國植物學研究的苦難史。“本草”是記載中藥的書籍,堪稱古代中國人最早的植物學文獻,自漢迄清,有上百種之多,其中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最為有名,是中國人利用植物治療疾病的開端,是中國文化的瑰寶,也是重要的植物學文獻。從黃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或多或少是受了“本草”的啟發和影響的。然而,在“本草”中,同所記載的植物學名稱到底對應現代植物學哪一種拉丁學名?另一方面,同一種植物在不同的本草中又會有不同的名字,而同樣的名字在不同的本草中可能會代表完全不同的植物。比如大家所熟悉南瓜在《本草綱目》和《滇南本草》中叫“南瓜”,在《群芳譜》中又叫做“番南瓜”,各地也還有“番瓜”“倭瓜”“紅南瓜”“飯瓜”等不同的名稱,經考證,這些名稱都對應現代拉丁學名Cucubiia moschata。要想知道本草所記載的植物到底為何物,就需要既通古文又知曉現代植物學知識的學者對其進行考證。《滇南本草圖譜》(下稱《圖譜》)就是本草考證的開山之作。
抗戰期間陳立夫主管國民政府的教育部,下令成立了一個“中國醫藥研究所”,試圖利用中草藥解決大后方缺醫少藥的困難,于是就有了對《滇南本草》的考證。這個任務落到了經利彬、吳征鎰、匡可任和蔡德惠等人身上。經利彬早年留學法國,獲里昂大學理學和醫學兩個博士學位,回國后任“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長,1946年去了臺灣,1958年在臺逝世。匡可任1935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攻讀林學,1937年抗戰爆發后,他毅然回國,參加了戰區教師貴州服務團,又到云南騰沖中學教生物,后輾轉到昆明黑龍潭農林植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工作,在黑龍潭認識吳征鎰及其業師吳韞珍,遂轉到中國醫藥研究所,參與了《圖譜》的工作,繪制了很多精美的插圖。蔡德惠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與“兩彈元勛”鄧稼先同屆,畢業時登榜第2名,因師從吳韞珍先生,也參與了《圖譜》的工作。蔡德惠喜好植物分類學,寫字很雋秀,讀書極勤,工作認真細致,曾在西南聯大的標本館外墻上立一土制日規以自勵。不想天妒英才,蔡德惠不幸染上了肺結核,英年早逝。這件事在著名作家汪曾褀1947年3月7日發布于《大公報》題為《蔡德惠》的散文中有記述。吳征鎰在清華大學畢業后留校做吳韞珍的助教,抗戰期間隨校轉至西南聯大任教。當時的醫藥研究所邀請吳韞珍來創辦藥用植物組。吳韞珍不幸因病早逝,藥物研究所尚未開展的工作全部留給了吳征鎰來料理。
這部耗時3年才完成的圖譜,考證了26種在《滇南本草》中記載的植物,其中包括了金鐵鎖、滇常山、白芨和臭靈丹等常見中草藥。作者對每個物種都進行了考證,每個物種都繪制了外形圖和解剖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圖譜》描述了一個新屬——金鐵鎖屬。金鐵鎖是云南白藥的一種重要配方,又叫“昆明沙參”和“土人生參”等名。外形略似蠅子草屬植物,英國植物采集人G.Forrest曾在云南采得過標本。吳氏師徒二人經過詳細的解剖發現,種子盾狀著生,種臍在種子的背面中部,胚珠退化等特征與蠅子草屬不符,應建立新屬。
《圖譜》從標本采集、考證、繪圖和文獻查閱到刻制和印刷全部由作者自行完成。在今天要出版一本僅包含26種植物的圖譜,也許不是難事,但是烽火連天的抗戰期間,經費短缺,資料不足,甚至連基本安全都沒有保障,幾位當時僅是30出頭的年輕人,憑一己之力出版這么一本專著,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這部《圖譜》還發表了一個新屬。搞植物分類學的都知道,發表過新屬的中國植物分類學家在今天也是屈指可數的。《圖譜》原計劃是分冊出版,未曾想第一冊出版以后,藥物研究所即解散了。印制好的《圖譜》吳征鎰院士留下5本后,全部交給了“教育部”而未能對外發行,后均不知下落。嚴格說,按照命名法規,《圖譜》未能公開發行,也未送達圖書館和同行,金鐵鎖新屬就不能算做有效發表。吳征鎰在文革后訪問“邱園”,為了保證金鐵鎖屬的合格有效發表,他把2本《圖譜》分別贈予了“邱園”和北京植物所圖書館,自己留下了3本,見過這本《圖譜》的人應該是屈指可數。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的紀念日,吳征鎰重印了《滇南本草圖譜》。如今,《圖譜》的作者均已仙逝,但是這一段中國植物學研究的歷史不該被忘卻,故記錄之。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鮑家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