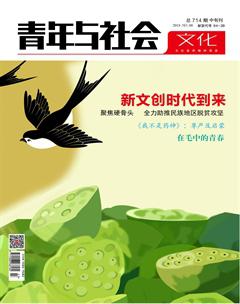曾孝濂 那個曾經把你美哭的老頭,終于辦畫展了
念新洪 讀庫
7月14日,“曾孝濂科學藝術畫公益展”在昆明植物園植物科普館拉開帷幕,共展出70余幅畫作,其中包括不少描繪云南特有植物、珍稀花鳥的作品,畫展將持續至今年12月。這是曾孝濂第一次舉辦個人畫展。
曾孝濂是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家,被譽為“中國植物畫第一人”。他曾和同事共同完成了《中國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中國高等植物圖鑒》等多部科學著作中昆明植物所承擔部分的插圖。在各類志書插圖工作中,他個人大概完成了2000余幅。
“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這句古詩用在曾孝濂的畫作上尤為貼切,作為一名植物科學畫家,曾孝濂的畫作兼具科研的準確性和藝術的美感,栩栩如生、清新動人。本次畫展是曾孝濂在國內舉辦的首個個人專場畫展,也是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80周年所慶系列活動之一。因曾孝濂的大部分畫作原稿已被浙江自然博物館收藏,本次展出的系按照原畫印刷追色的高仿畫作。
“曾孝濂科學藝術畫公益展”共展出70余幅高仿畫作,涵蓋“中國傳統名花”“云南八大名花”“鳥與植物”“云南特有真菌”“云南珍奇植物”“常見藥用植物”“大樹景觀”等多個類別。14日展覽啟幕當天,年過七旬的曾孝濂現場講解了繪畫技藝,并分享了繪畫生涯中的精彩故事和心得體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曾孝濂繪畫作品中的大多數植物都可以在植物園里找到實物,前來看展的觀眾“足不出園”就能對照觀察和欣賞。在接下來的展覽中,主辦方還將分批展出曾孝濂的其他近60幅畫作,并開展系列科普活動。
為中國植物畫傳
1939年6月,曾孝濂出生于云南威信。1958年,曾孝濂高中畢業,1959年,以半工半讀形式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搞植物學。《中國植物志》項目上馬后,領導見曾孝濂能畫兩筆,就把他調入了植物分類室,做植物科學畫,直到退休。
對自幼愛好涂鴉的曾孝濂來說,能從事與繪畫相關的工作,比考取大學還要高興。有皇皇80卷126冊《中國植物志》,先后動用312位植物分類學家,164位畫師,曾孝濂正在其中。在董卿的訪談中,曾孝濂熱淚盈眶:很多畫師為《中國植物志》畫了一輩子,今天,我代表的是這個默默無聞的群體。
曾孝濂不養花,不是不愛,而是沒時間養。植物科學畫,不像早期的本草繪畫,僅憑借藥用部位或者大概的外部長相來描繪,也不是簡單重復相機的功能,原封不動地映照自然。植物科學畫有自己的一套近似程式的繪畫語言,它必須比照標本,精準地傳達植物的科學特征。
昆明的植物特別多,植物所就在植物園里面,條件很好。曾孝濂常常出來找活的標本,從活的植物入手,把這個物種的形態特征做到非常熟悉。“當時我們的領導很好。他們盡量不特別催我們這些新人,不說趕緊做、趕緊交稿。他們知道我們年紀小,就盡量幫助我們。有時候還會跟我們一起解剖采來的花。”就這樣,曾孝濂快速熟悉著不同植物的特征,比如雄蕊的長短,雌蕊花盤的性狀,把每個科的特征熟悉了,也就慢慢掌握了一些規律,再面對干標本時就容易得多。
畫干標本一般要把整個的花取下來放到水里煮開,讓它盡可能去復原,復原后再在解剖鏡下面觀察結構。“植物軟了以后比較接近活的,就稍微好一些。”植物科學畫必須要對著標本作畫,“沒有標本不能畫,不應該畫。我們所有插圖必須有根據,一定要寫上根據某一號標本。不看標本來畫,那是錯誤的”。
曾孝濂為《中國植物志》繪制的插圖就是這樣慢慢積累起來的。“每畫一張圖,都得打草稿,給分類學家看。看完確認了再上鋼筆稿、墨線。表現形式、線條的結構這些需要一點一點積累。”
無論是早期的科學著作插圖,還是后期的花鳥藝術創作,都要做到“無一花無出處,無一葉無根據”。對于很多畫家“不屑一顧”的這種畫法和畫種,他有自己的看法,“我偏覺得味道足”。
他說:“博物畫作品好不好,話語權不在權威的文藝評論家或者藝術雜志,而在廣大受眾手里。博物畫是一個非常具有大眾品格的畫種,它貼近自然,反映自然,既有審美的屬性,又具有鑒別的功能。”
耐得住寂寞歲月
曾孝濂經常告訴自己的學生,做這行要坐得住冷板凳。冷板凳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心靜,這是搞好工作的前提。這意味著一種孤獨、寂寞,而且是長年累月的。
曾孝濂說:“除了有幾年時間在西雙版納做野外工作,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標本館。沒有這種修煉,你的心就不能很專注、排除世俗的干擾,你就會堅持不下去。”
冷板凳另外一個含義是心誠。這考驗的是繪畫者如何對待自己的對象,是否真的很虔誠地對待工作。“你的對象是有生命的,你用最樸實的繪畫形式反映他們最重要的分類特征。”但這需要樂在其中。
除了為植物志畫黑白畫,上世紀70年代,曾孝濂接到過為昆明植物園畫《茶花圖譜》的任務,是彩色畫。那時候彩色膠卷并不普遍,曾孝濂所在植物所沒有,就靠硬畫。“那是最厲害的,我幾乎天一亮起來,到植物園去摘一朵山茶花,跑回辦公室插在瓶子里。趕緊去吃早點,一般七點半才能吃,一有饅頭粥,我隨便吃點就跑回來畫。一直畫到十二點半,吃午飯。五個鐘頭期間,不會喝水、不會上廁所,全神貫注。那個花從植物園摘下那一刻,就會慢慢開,你要畫慢了,就找不著關系。那個花瓣本來朝下的,它會慢慢朝上,所以非常緊張。而且畫這個不能構好圖再畫,必須一個花瓣一個花瓣地畫,從最靠近你的那瓣開始。畫到中午時你會忘記上廁所,但是告一段落的時候,會渾身發抖,我覺得可能是熱量沒有了。”
吃完飯,曾孝濂一般會再摘一朵花,早晨那朵已經不行了。半天畫一朵,下午研究怎么搭配、畫葉子。那樣大概畫了好幾個月。“非常緊張,身體不好就會受不了。但是非常磨練”。經此一役,曾孝濂畫彩畫的能力比早期參加工作時高了一大截。
自己的繪畫語言
曾孝濂主業是畫植物。1960年代,他參加了國務院組織的“5·23”項目,數十家地方和軍隊的科研、醫藥單位組成的攻關工作隊研究如何對抗惡性瘧疾。同期下達的還有“熱區野菜圖譜”和“熱區軍馬飼料”兩項任務,即在后勤保障缺失的情況下,部隊在叢林中尋找到可食植物,有點兒類似“神農嘗百草”。
曾孝濂參與負責的是繪圖工作,在與越南、老撾、緬甸接壤的林區實地寫生。后來此項目篩選出一種療效顯著的菊科植物,有效成分青蒿素經過臨床和病理實驗得以確認。很多年后,屠呦呦憑借此得到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對曾孝濂來說,他總是強調,這樣大的系統工程,自己參與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這樣的經歷對于他的人生、繪畫都至關重要。
熱帶雨林的野外作業任務在哲學層面訓練了曾孝濂。“從無知開始,興奮、驚喜,震驚。然后就有點敬畏,被螞蝗咬了,被螞蟻叮了,害怕。認識多了,又不同。就知道大自然是生命的合唱,這里的物種經過千百年的進化,既有競爭,又相互依存,是大的生態網。身處其中,你會覺得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意識到我要畫它們,不僅要畫得像,還要定一個目標,我一定要表現這個物種的生命狀態,無論畫干標本還是觀賞性花卉、動物,我的重點是盡量地反映它勃勃生機。不光畫得準確,最重要的要畫得生動。謳歌生命,謳歌自然,用我的畫筆。”
大量時間與自然相處,徹底改變了曾孝濂。有幾年出差,“每天在大山里面,天不亮,你就聽那鳥叫吧。就是一個交響樂、大合唱。你分不清也看不清什么鳥。在西雙版納,在易門,林子里天快亮時都一樣。就特別想畫”。
上世紀90年代初,他在香港工作了一年,非常偶然的機會,他買到了一本英國人畫的鳥的科普著作,“當時暗自決定,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出一本鳥的畫冊”。
曾孝濂是一個想到就一定努力做到的人。為了這本鳥的畫冊,他做了很多準備。還是上世紀90年代,當時中國植物志的編委會在北京植物所的動物園里面,他每天到鳥園觀察鳥的姿態、畫速寫、拍照片,為畫鳥積累了很多資料。回到昆明后,他又得到昆明動物所一位鳥類專家楊嵐的熱心幫助。為了摳鳥的細節,他還經常跑去昆明動物所標本館,“因為任何一個活的鳥不會讓你去寫生的”。開始畫的時候,他為不同鳥類配以棲息地,“那是我的優勢。我查閱相關的資料,了解鳥類的生活環境,然后搭配相應的植物”。
在“中國鳥”的郵票里,這一切做到了極致,他用小版張的形式把不同地域的九種鳥濃縮在一個虛擬的空間里。雖然畫面是虛構的,但是每一種鳥腳下的小環境必須相對真實,符合其生活習性。比如紅腹錦雞、黃腹角雉和白尾地鴉都喜歡在地面活動,但是紅腹錦雞喜歡在有巖石的林地,白尾地鴉澤生活在戈壁沙石灘上。鳥類通常以群體或家庭為單位活動,所以小畫幅里放進了群鳥或雌雄鳥、雛鳥一同出現。另外,每種鳥姿態各異,或飛或立或觀望覓食,各行其是。
關于蛇和夢的番外
最后還想跟大家分享曾老先生的夢。老先生這輩子有很多野外作業的經歷,見多識廣,又畫過如此多花鳥。以為他的夢一定像他的畫一樣瑰麗神奇。結果他說,他常常夢到的是蛇,是很多很多蛇。因為碰到的太多。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張樹庭早年一本著作《香港蕈菌》里講過一次野外考察,里面有一個小段落與曾孝濂相關:說來這眼鏡蛇的膽子夠大的。它退后一點后,又舉起頭來做出向我們進攻的姿勢。結果形勢不利而慢慢游到溪那邊。稍息后它又返回來,可能它對來犯者沒有報復而不甘心離去,于是再次下水向我們游來,終因水勢不利而退卻了。在溪那邊休息一會兒后向橋底慢慢爬行而去。在云南曾經見過這東西的曾先生比我沉著,他早已拿出相機把這場面拍了下來,眼鏡蛇留下了永久的留念。
畫面感太強,我便跟曾老先生求證。他說,當時一行人在靠近西貢的林子里,他們到了一個小河溝。他去洗把臉,結果蹲下來,手剛碰到水,旁邊的人就喊起蛇蛇蛇。他說:“那個蛇當時離我30公分,后來我一看是眼鏡蛇,脖子是癟的,一大片。可能它也是怕熱在水里面。當時我在它攻擊范圍里。但是它在水里,我判斷,它要攻擊我,沒有支撐。我猛地退一步,拿出相機拍下來了。當時確實也很危險。它在水里,挺不大起來,但是要再高一點,必然會經過我。當時它脖子已經很癟了,有我手掌那么寬,做出了攻擊姿態。后來聽說,如果我被蛇咬了,離我們最近的醫院也有20公里。那可能就是沒有希望了。”
如此輕描淡寫。“我碰到的蛇很多,但一次都沒被咬過。還有一次在西雙版納,竹葉青也是很毒的,它趴在那樹上,離我手就十來公分,也沒被咬。眼鏡王蛇也碰到過。其實很多同事比我經歷更多。曾經有一次,早晨起來出操,同事找不到皮帶,伸手一摸床上有一條,拿過來一系發現是條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