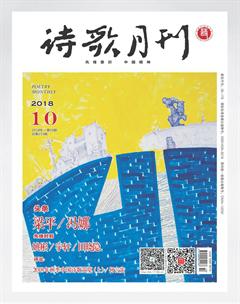“普遍黑暗的年代,也有微光”
谷禾:《世界的每一個早晨》,《山花》2018年第7期
“普遍黑暗的年代/也有微光”,這是谷禾《普遍黑暗的年代》中的詩句。它讓我想起谷禾以往的詩中關于黑暗的寫作,比如《一盞燈從黑夜里遞過來》《仰望星空的人》《在長途汽車上讀扎加耶夫斯基突然停電》,特別是其長詩《少年史》;也讓我想起谷禾同樣酷愛的西姆斯·希尼的詩句——“我寫詩/是為了認識自己,使黑暗發出回聲”(希尼:《個人的詩泉》)。“使黑暗發出回聲”,哪怕是用光,用也許顯得些微的光,也足以洞穿黑暗,回應和抗擊浩大無邊的黑暗。
《世界的每一個早晨》中的十來首詩,幾乎每一首都寫到光。《旁觀者》中,光是烈火,它燃燒在冷冽的冬日和海潮退去、燈塔熄滅的時刻,旁觀者的驚人的冷靜,愈發彰顯出光與火的熱烈與偉力;《在深夜》中,詩人端坐于“漆黑”,觀察與辨認燈的光、水的光,領悟塵世,感受命運白晝一般真切的痛楚。谷禾多次都寫到雪。他寫自己在“天色陰沉”中等待著雪,期待著或許還在途中的雪的光芒——“一個詞的光芒”;而在《雪的消息》中,他欣喜于好友終于從新疆“捎來了關于雪的消息”。我總覺得谷禾詩中的雪與俄羅斯作家、詩人作品中的雪有著深刻的互文,這不僅是詞語、修辭與意象的互文,而且更是精神的互文、命運的互文。因此他在《雪的消息》中,能聯想到安娜和瑪琳娜的命運;在《午后記》中,“命定的雪”不僅能“帶來梵·高的星光夜”,更是讓詩人在對雪的期待與想象中沉浸于某種凝重的氛圍:拉拉、日瓦戈、托爾斯泰……這些俄羅斯文學史上光輝的名字,與詩人的自我發生了一種深切的關聯,某種神啟,如同“一個詞的光擦亮了詩歌”,陡然照徹了整個詩境,使詩人的午后獲得了非凡的意義,也使這一切迎面撞向現實,“遭逢了轟隆隆的北三環路”。當下中國的詩歌界,谷禾是一位非常難得的具有自覺與清醒的現實意識的詩人,他曾說過:“詩歌當然不是現實本身,但詩歌必須根植于現實,并且必是現實的回聲。”他還說過:“詩人不是先知,不是上帝,更不是救世主,他最大的可能是讓自己發光,照亮世界的一個微小角落”,詩人“要用你勇敢的詩去嘗試撞擊黑暗的世界,并傾聽它發出怎樣光明的回聲”。谷禾的主張,不禁讓我想起布羅茨基關于詩與現實的思考,他說“在歷史發展的某些階段,唯有詩歌可以應付現實,它將現實濃縮為可以觸摸、心靈可以感受的某種東西”(布羅茨基《哀泣的繆斯》)。在這樣的意義上,谷禾兄所突出、標舉與想望的光,是否正是這樣的“濃縮”?是的,在谷禾的詩中,我看見了許多光,我看見了“微光握緊的拳頭”,在“普遍黑暗的年代”(《普遍黑暗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