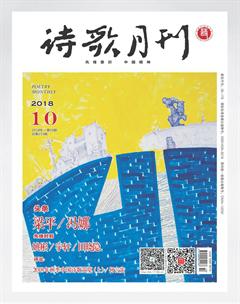“一個在暗中,不斷過濾的自我”
葉麗雋:《野渡》,《人民文學》2018年第9期
在我的印象中,葉麗雋沉默、內斂,不知確否?
——是在一次會議上,我與葉麗雋匆匆見過,亦未交談。但在此前的2013年,《揚子江詩刊》曾經與《文學報》《詩刊》《花城》等報刊搞過一個“六刊一報新世紀詩歌作品聯展”,葉麗雋的詩被重點推出,時任主編子川先生囑我對聯展做一個述評,因此我得以較為集中地閱讀了葉麗雋,發現她的詩作“生命的俗在與停滯經常會在動的自然與動的世界中予以表現,并且與它們內在呼應”。我發現葉麗雋的詩是那么優秀、那么獨特!她的《春水吟》和《我記得這茫茫蘆葦》,都是很多朋友所熟知的名篇,也很突出地體現了她的創作特點。這次讀她的新作,又一次感受到她的詩中個體生命與自然萬物之間的內在呼應。她的自我總是在俗世中,在自然里,生長、“攀爬”(《易弦記》)、“婆娑”(《將飲》)、反芻(《野蕨》),暗自在內心里隱忍、自省(《敗醬草》),渴望著救渡(《野渡》),“凱覦”或向往著某種更加激越的狀態(《春夜微醺》《激動史》)。我驚訝于葉麗雋為什么會有如此突出的自我意識,且將這種意識時時處處地自覺、貼切地呼應于自然?
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葉麗雋的自我總是很弱,謙卑、真實、低調,很少昂揚。但無論是何種情況,她的自我又總是呼應于自然,生命與自然時時處于神秘交流和互為啟示的狀態,正是在這種交流與啟示中,心靈的體驗與人生思考得以豐厚,得以提升。《敗醬草》一詩,簡直就像是詩人自我的寫照——
“……我已遠遠地退后/敗醬草一樣/埋首于人世的低處/在苦澀的陳腐氣中,沉溺并懂得/山野之間,有著本然的救贖/幾乎是一種呼喚呢——懷揣一腔虛火/我惦念著郊外/亂叢之下,那清熱解毒的草木/誠如,再粗鄙的個體,也需要一個隱蔽所/一個在暗中,不斷過濾的自我”。
葉麗雋于自然,極擅寫草木。她在敗醬草這里,發現了自己會心與認同的品格,“退后”和“埋首于人世的低處”,于“隱蔽”的“山野之間”去尋求“救贖”。但是在另一方面,她近乎又以草木為師,法于自然地反諷著自我。她“燎泡上唇”“懷揣一腔虛火”“惦念著”需要“清熱解毒”——這是一個時時“在暗中,不斷過濾的自我”。葉麗雋詩中自省式的“過濾”,使詩人的自我幾乎在每一首詩中都有一次凈化,都能得到有益的增進,同時也呈現出自我生命的真實與復雜。所以在《野蕨》——就是《詩經》所云的那“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那卷曲,脆弱于世/又欲觸及四周”的野蕨中,她既從野蕨那里“回溯”向自己,復又在對“埋藏的自我”的“反復耕耘”中“升騰起火焰”。這樣的“火焰”,也喻示著葉麗雋的自我中明亮的方面,如同《將飲》中的“懸鉤子”,“它們依舊飽滿、紅亮”……葉麗雋常常會心于草木,呼應自然,但她的寫作,又決不僅僅局限于此。在《野渡》《晨曲》《激動史》和《易弦記》等作品中,誠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她的自我同樣會在面對俗世、面對更加廣闊的世界時轉向自身,暗暗地進行對話、反芻和“過濾”,生成一個新的自我——在我對中國女性詩歌的有限閱讀中,很少有人能夠像葉麗雋這樣具有如此自覺的自我意識和具有如此獨特、美妙的自我生成機制。她在一些場合的沉默與內斂,也許正是一種自我的保持,抑或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