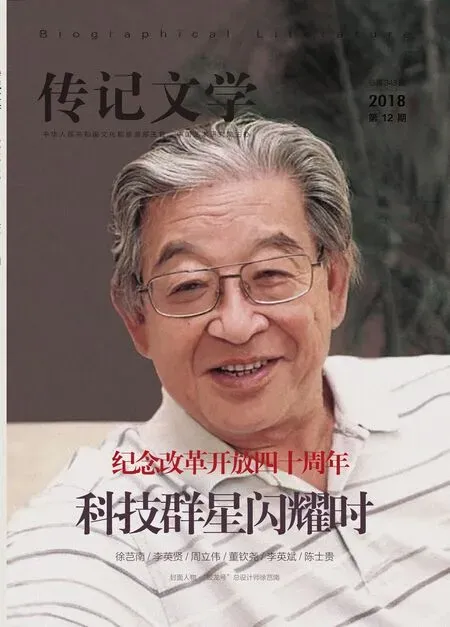天問
——中國載人航天背后的故事
趙 雁
中國航天員科研訓(xùn)練中心

上 圖:2016年10月17日早晨7點30分,中國的載人航天飛船神舟十一號由長征2F遙十一火箭發(fā)射升空。這是中國自2013年完成神舟十號載人飛行任務(wù)之后,時隔三年再次進(jìn)行載人航天發(fā)射
中國天問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誰能極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明明暗暗,惟時何為?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
這是人類認(rèn)識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記載的對宇宙作出最接近科學(xué)的思考,作出這樣驚人之問的竟然是距今約2500年前的偉大詩人——屈原。
打開逸響偉辭、卓絕一世的《楚辭》,撲面而來的是一篇雄偉奇特的科學(xué)巨制《天問》。詩人一口氣提出了172個問題:茫茫宇宙,沒有始末,是傳承而來?天地未成,憑什么來研究?晝夜未分,混混沌沌,誰能弄清?日明月暗,晝夜交替,是怎么回事?太陽月亮高懸不墜,何以能照千秋?天有九重,是誰動手營造?何等樣的偉大工程,最初是誰創(chuàng)造的?鷹的翱翔,鳥的飛行,云的飄動,無不牽起人們對飛行的渴望和幻想。從手持神斧萬象皆開的“盤古開天”到英雄氣概滿懷勇于探索自然的“夸父逐日”;從獨上月宮孤光冷影的“嫦娥奔月”,到凌空飛舞美麗翩躚的“飛天壁畫”……千百年來,這些關(guān)于九天之上美麗的傳說無不顯示出中國古人對太空的幻想與思考。
把飄逸的夢想和古老的傳說變成真切的現(xiàn)實,歷程上千年,直到20世紀(jì),人類才得以在太空安全著陸。
在通往太空的道路上第一個敢為人先的嘗試者是中國人。他有一個非常詩意的名字,叫萬戶。
作為龍的傳人,萬戶是人類第一個倒在天梯下的真正意義上的航天人。他是一個善于思考的智者,仰望天空是他每日例行不變的功課。“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無止境的思索最終化為他探天之路的驚人舉動。
那是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一天,在一座山坡上聚集了許多觀看飛行的人們。只見萬戶兩手各握著一只大風(fēng)箏,坐在一輛捆綁著47支火箭的“飛龍”上。他打算等火箭升空后,就利用這兩只大風(fēng)箏帶著自己在空中飛行。然而,隨著火箭發(fā)出的轟響,“飛龍”拔地而起,沖入半空,不久空中傳來一聲巨響, “飛龍”頃刻間化成一團(tuán)火球,栽在了山腳下。
萬戶帶著他不醒的夢走了。人們永遠(yuǎn)記住了他最后一抹自信而鎮(zhèn)定的笑容。
約500年后的1970年,在英國布萊頓召開的國際天文會議上,月球上一個最大的環(huán)形山被命名為“萬戶”。人們以此紀(jì)念這位人類第一個踐行飛天的勇士。
中國是火箭的故鄉(xiāng),完全有理由在探索太空的道路上捷足先登,然而歷史的發(fā)展進(jìn)程卻讓人大跌眼鏡。中國古代的火箭在世界載人航天史上只遺憾地充當(dāng)了啟蒙者的作用,在經(jīng)過愚昧與腐敗交織、閉關(guān)鎖國、唯我獨大的清王朝的漫長統(tǒng)治后,中國的火箭技術(shù)遠(yuǎn)遠(yuǎn)落在了西方之后。泱泱華夏大國,蕓蕓炎黃子孫沖擊太空的宏愿就此折翼,化作夢中的康橋。
飛天夢從這里啟程
剛剛過去的20世紀(jì),自然科學(xué)的飛速發(fā)展把人類的航天事業(yè)推向了一個又一個巔峰,整個太空悄然間變成了令人如癡如醉和眼花繚亂的飛天試驗場。
1957年10月,蘇聯(lián)成功地發(fā)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人類步入太空初露端倪。
1961年4月12日,蘇聯(lián)航天員加加林乘坐“東方一號”飛船遨游太空,人類第一次用誠摯、熾烈的雙眸飽覽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星球以及星外空間的深邃與秀美。
1969年7月21日,美國航天員阿姆斯特朗的左腳輕觸月面,邁出了人類探索月球的第一步。“這是我個人的一小步,卻是整個人類的一大步。”
從那時起,進(jìn)駐太空已成為衡量一個民族科學(xué)水準(zhǔn)的重要標(biāo)志。之后,一艘接一艘的載人飛船、空間站和航天飛機飛入太空,數(shù)以百計的航天員飛臨太空,他們無可爭議地成了地球派往外層空間的觀察員和特使。真可謂“攪得周天‘熱’徹”!
當(dāng)美蘇兩國在太空搏殺得遮日蔽月之際,地球另一端的中國也在悄悄運籌自己的太空沙盤,但走的卻是一條更加艱辛而曲折的道路。
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廢待興,但中國的領(lǐng)導(dǎo)人絲毫沒有放棄“飛天”的戰(zhàn)略思考。高層的偉大決策,祖國的迫切需要和愛國知識分子的報國熱情緊緊凝聚在一起。海外大批優(yōu)秀科學(xué)家紛紛踏上報國之路,這其中就有中國的航天先鋒錢學(xué)森。
1955年11月底,祖國的東北已是冰封雪裹,異常的寒冷把白山黑水打扮得通體晶瑩,到處呈現(xiàn)出一片寒冬的寧靜,然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xué)院卻顯得熱情涌動。因為這一天有一個特殊的人物要來,他就是剛剛回國不久的錢學(xué)森。這位師從馮·卡門教授的科學(xué)家,早在20世紀(jì)40年代就開始研究火箭,并于1949年推出著名的“錢學(xué)森公式”,提出了航程5000公里的助推滑翔超音速飛行器的建議。作為一名愛國學(xué)者,即使在美國遭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錢學(xué)森也始終不忘自己的祖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年后,終于沖破層層封堵和阻撓,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
院長陳賡大將專程從北京趕回哈爾濱迎接錢學(xué)森。他向錢學(xué)森問的第一句話是:“中國人搞導(dǎo)彈行不行?”
“外國人能干,中國人為什么不能干?”錢學(xué)森反問道。
“好!就要你這句話。”
陳賡像老朋友一樣親切地拍著錢學(xué)森的肩膀。

錢學(xué)森
說干就干,錢學(xué)森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自己的思維神經(jīng)、延長自己的絕對勞動時間,在不到3個月的驚人時間里,拿出了我國航天史上第一份發(fā)展火箭和導(dǎo)彈的規(guī)劃。1956年2月17日,錢學(xué)森懷著激動的心情,把自己對祖國的第一份答卷——《建立我國國際航空工業(yè)的意見書》鄭重地交給了中共中央。這份宏觀和微觀統(tǒng)一、計劃和國情高度吻合的報告,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在最短時間里,國家即建立了導(dǎo)彈研究院。
中國人的航天夢終于在導(dǎo)彈和火箭的打造中緩緩啟程。
正在我們起步的當(dāng)口兒,蘇聯(lián)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上天。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揮動著他那雙曾指揮過千軍萬馬的神奇之手,向中國人民發(fā)出鏗鏘有力的號召:我們也要搞人造衛(wèi)星。
向天門挺進(jìn)
世界航天分式的法則是明確地把無限和恒量的太空作為分子,分母則是一個憑自身因素介入的變量。能否走進(jìn)“天門”,進(jìn)了“天門”能走多遠(yuǎn),完全取決于自己的實力。
1958年8月,中國科學(xué)院決定錢學(xué)森、趙九章等人負(fù)責(zé)擬定人造衛(wèi)星的發(fā)展規(guī)劃,并成立了宇宙生物研究室,主要進(jìn)行以動物實驗為主的宇宙生物學(xué)的研究,建成了動物離心機、振動、低壓、溫度、生化和動物訓(xùn)練等實驗室,開始了我國早期的宇宙生物研究。
中國的宇宙生物實驗雖然完全是靠自己摸著石頭過河,但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有了起色。
在1964年至1966年近3年時間里,中國成功發(fā)射了生物探空火箭,將狗、大白鼠和小鼠等動物垂直發(fā)射到70至80公里高空,用于研究火箭發(fā)射在各個階段對動物機體的影響。
生命的光焰映出了一條中國人走向太空的通衢。
1968年,中國科學(xué)家在“我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總體方案設(shè)想論證會”上,將我國的第一艘載人飛船命名為“曙光一號”。這個名字代表著中國載人航天初露曙光。
軍事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勞動生理研究所針對載人航天總的設(shè)想,擬訂出了《人在宇宙航行中的生命保證規(guī)劃方案》,并得到國內(nèi)航天界的一致支持。由于該領(lǐng)域的研究分散,歸口不一,人力物力不能集中有效使用,國防科委決定集中建立宇宙醫(yī)學(xué)、宇宙生物學(xué)專門研究機構(gòu)。
宇宙醫(yī)學(xué)及工程研究所,即今天的航天員科研訓(xùn)練中心,正式成立于1968年4月1日,由軍事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勞動生理研究所、力學(xué)研究所、中國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實驗醫(yī)學(xué)研究所等單位組成,下設(shè)總體、生命保障醫(yī)學(xué)、生命保障工程設(shè)計、宇航軍事活動效率、救生醫(yī)學(xué)防護(hù)、醫(yī)用電子儀器、選拔訓(xùn)練、醫(yī)學(xué)監(jiān)督等業(yè)務(wù)組,隸屬空間技術(shù)研究院,而空間技術(shù)研究院院長就是赫赫有名的錢學(xué)森。
這個研究所是培養(yǎng)中國航天員的搖籃。
在“文革”無休止的動蕩中,為了尋到安靜的一隅,宇宙醫(yī)學(xué)及工程研究所將辦公地遷到了位于北京西北郊區(qū)昌平十三陵附近一排紅色的磚木平房中,門牌號碼是“200”。
這是一個很神秘的號碼,周邊的人只知道它是一個保密級別很高的研究單位。就在這個神秘的“200”里,許多不尋常的工作異乎尋常地進(jìn)行著。
創(chuàng)業(yè)階段,一切都相當(dāng)簡陋艱難。辦公室里除了一個三屜桌、一把椅子、幾張紙,就一無所有了。他們白手起家,自己搬沙石、抹水泥、蓋房子。唯一使人欣慰的是,這里有一群渾身散發(fā)著青春與熱情的年輕人。他們之中有北大、清華的高才生,也有其他一些名牌大學(xué)的人才尖子。
然而辦公地點仍在不停變化。每次搬入臨時辦公點,大家就把宿舍、樓道、體育館、教室開辟成臨時實驗室,堅持做實驗。在最困難的時候,這個研究所曾在搭建的33頂帳篷中,辦公長達(dá)5年時間。
從“200”進(jìn)發(fā)起飛的人大概有200名之多。今天的許多航天人談起這一串阿拉伯?dāng)?shù)字,都會發(fā)出由衷的感慨:“200”,感謝你!
折翼“714”——一個失落的夢
太空領(lǐng)域的競爭不僅是一個民族科技和經(jīng)濟(jì)實力的比拼,更是這個國家、政府領(lǐng)導(dǎo)人謀略的交鋒。中國的領(lǐng)導(dǎo)人在太空問題上多次作出過前瞻性的重大決策,為中國航天提供了堅實的政策保證和經(jīng)濟(jì)支撐。
1970年7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和中央軍委辦事組批準(zhǔn):“即著手載人飛船的研制工作,并開始選拔、訓(xùn)練航天員”,這就是中國科學(xué)界有名的“714”,這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見諸于文字的最權(quán)威批示。
宇宙醫(yī)學(xué)及工程研究所作為使命的中心地帶,更是不容遲疑地開始著手準(zhǔn)備,等待迎接自己的航天員。未經(jīng)太多風(fēng)雨磨礪的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日后這里會成為世界第三個航天員訓(xùn)練中心,但當(dāng)時科研職業(yè)的敏感還是讓他們感到了自己所從事工作的非同一般。
航天員的選拔與訓(xùn)練、飛船生命保障系統(tǒng)的醫(yī)學(xué)要求與工程設(shè)計研制、地面模擬試驗設(shè)備的建立等,都是重量級的科研課題。
也許是人定勝天的理論,讓大家把問題想得簡單了一些。“曙光一號”飛船發(fā)射的日期最初定在了1973年。
所有的課題都展開了,所有的科研人員都以最佳狀態(tài)搏擊了。
然而,不可能一步登天,載人航天是一個巨大的系統(tǒng)工程。當(dāng)時中國的“長征一號”火箭運載能力只有300公斤,航天測控網(wǎng)還沒有必不可少的遠(yuǎn)洋測量船。由于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薄弱,工業(yè)制造及相關(guān)工藝水平落后,加上十年動亂的影響,“曙光一號”飛船最終塵封在科學(xué)家的草圖和設(shè)想中。從全軍飛行員中選拔的20名預(yù)備航天員懷著對太空的無比向往遺憾地又回到了普通人的行列。
科技之春“863”——蘇醒的航天夢
20世紀(jì)80年代,世界航天大國都在重新排列自己的發(fā)展模塊。1984年1月6日,美國總統(tǒng)里根發(fā)布了《國家安全決定》第114號文件,正式下令擬制新的“星球大戰(zhàn)”計劃。在這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戰(zhàn)略防御計劃中,美國人瞄準(zhǔn)了日新月異的航天技術(shù)、定向技術(shù)和微電子技術(shù)等高新技術(shù)。在他們看來,一個新的太空軍事時代正在悄然而至。據(jù)此,他們制訂了旨在對付蘇聯(lián)可能發(fā)動的大規(guī)模核襲擊而以天空為基地的實施全導(dǎo)彈攔截的綜合防御體系計劃。他們認(rèn)為掌握了“制天權(quán)”,就奪取了未來戰(zhàn)爭的勝利,并為這個價格昂貴的計劃撥款25億美元。
面對美國的“星球大戰(zhàn)”計劃,西歐各國卻有另一種惶恐。他們敏銳地嗅到美國“星球大戰(zhàn)”計劃絕不僅是軍事防御層面的,它還是一個高技術(shù)發(fā)展計劃。如果自己不主動融入這場即將來到的新技術(shù)的洪流,將被歷史無情地拋棄。
1985年,法國總統(tǒng)密特朗首先倡導(dǎo)建立“技術(shù)歐洲”的“尤里卡”計劃。此計劃得到西歐19國的一致贊同,在多次討論“豐滿”后,通過了總投資20億歐洲貨幣單位覆蓋電子技術(shù)、現(xiàn)代通信、生物工程、機器人、新材料等62項新的高技術(shù)合作發(fā)展計劃。
日本也不甘落后,率先在亞洲做出反應(yīng),提出“今后十年科學(xué)振興政策”。
中國科學(xué)家的神經(jīng)觸覺是敏銳的。此時此刻,四位科學(xué)家懇切地向中國領(lǐng)導(dǎo)人建言要跟蹤世界先進(jìn)水平,發(fā)展我國高技術(shù)的建議。
他們是時任中國科學(xué)院技術(shù)科學(xué)部主任、中國科學(xué)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大珩;時任核工業(yè)部科技委副主任、我國核物理學(xué)界的泰斗王淦昌;時任航天部空間技術(shù)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我國航天學(xué)家楊嘉墀;時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委員、我國無線電電子學(xué)家和衛(wèi)星測控專家陳芳允。他們上書的時間是1986年3月3日。這封信得到鄧小平的高度重視。他曾在1979年2月訪問美國,在參觀美國的航天博物館時登上美國人的航天飛機,當(dāng)了一回“太空人”。火箭故鄉(xiāng)的人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與世界的差距。中國人要奮起直追。他以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戰(zhàn)略家的遠(yuǎn)見卓識親自批示:此事宜速決斷,不可拖延。
1986年4月,中國數(shù)百名科學(xué)家會聚北京,討論《國家高技術(shù)研究發(fā)展計劃綱要》這一歷史性計劃。
國務(wù)院組織了200名著名專家學(xué)者反復(fù)論證。這份被稱作“中國的尤里卡”計劃的“863”計劃,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了一個發(fā)展中大國的國情,堅持了“有限目標(biāo),突出重點”的方針,非常實際地選擇了從生物技術(shù)、航天技術(shù)、信息技術(shù)、激光技術(shù)、自動化技術(shù)、能源技術(shù)和新材料7個領(lǐng)域作為突破口,從15個主題入手通向發(fā)展目標(biāo)。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kuò)大會議,批準(zhǔn)“863”計劃,并決定撥出專款100億元實施這一計劃。而航天技術(shù)領(lǐng)域則占其中的40%之多,中國的載人航天事業(yè)終于迎來了發(fā)展機遇。
“863”計劃使得中國科技在經(jīng)歷了“文革”的“休克”之后重新蘇醒,進(jìn)而迸發(fā)出讓世界刮目的神奇力量。
1987年2月,在國防科工委的組織下,成立了“863”高技術(shù)研究與發(fā)展計劃論證航天領(lǐng)域的專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集中了20多位國家級航空航天專家,下設(shè)兩個專家組:一個是大型運載火箭及天地往返運輸系統(tǒng)論證組,一個是載人空間站系統(tǒng)及其應(yīng)用論證組。
中國載人航天如何起步,剛開始專家們的意見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認(rèn)為,中國載人航天應(yīng)該從飛船起步;而另一部分人提出,要搞航天飛機。
復(fù)雜而繁重的論證從1987年始,進(jìn)行了長達(dá)5年零10個月的時間。中國的頂尖級科學(xué)家為此付出了超常的智力思考和體力消耗。
在航天器的選擇上,專家意見分歧很大,幾種聲音難辨高低。有專家希望一步到位,直接研制在美國也處于藍(lán)圖狀態(tài)下的航天飛機,有的則希望研制飛船。
正在論證深入進(jìn)行時,高層突然召集“863”航天領(lǐng)域?qū)<椅瘑T會開會,會上提出“重新認(rèn)識載人航天的意義”。
載人航天耗資龐大而且它的直接經(jīng)濟(jì)效益的確不及我國發(fā)展已日趨成熟的應(yīng)用航天,但載人航天在體現(xiàn)人類探索精神、提高國家聲望、開闊人類眼界、強化國防實力、增進(jìn)科技進(jìn)步等方面意義卻是直接經(jīng)濟(jì)效益無法比擬的。它可以通過技術(shù)轉(zhuǎn)移等多種途徑產(chǎn)生更為可觀的二次效益、三次效益。在載人航天深入發(fā)展、太空工業(yè)化時代來臨時,它創(chuàng)造的經(jīng)濟(jì)效益將遠(yuǎn)遠(yuǎn)超過應(yīng)用衛(wèi)星。財經(jīng)學(xué)家用科學(xué)嚴(yán)謹(jǐn)?shù)挠嬎憬Y(jié)果顯示,載人航天投資占中國國民生產(chǎn)總值(GDP)的份額并不算龐大。這樣的結(jié)果消除了許多人橫在心中的隱憂。
騰飛“921”——航天夢成功著陸
在經(jīng)過充分論證后,激烈的爭執(zhí)在“紫禁城會議”上趨于緩解,載人航天器選用飛船的呼聲占據(jù)了多數(shù)。
1991年3月28日,中國空間技術(shù)研究院正式成立了飛船論證組,“航天飛機學(xué)派”與“飛船學(xué)派”的爭論暫告一段落。
經(jīng)過認(rèn)真論證,專家們逐步達(dá)成共識,航天飛機造價昂貴,技術(shù)復(fù)雜,而中國當(dāng)時也不具備生產(chǎn)航天飛機的技術(shù)條件,載人飛船既可搭乘航天員,又可向空間站運輸物資,還可作為空間站軌道救生艇用,且經(jīng)費較低,更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的載人航天事業(yè)應(yīng)該從飛船起步,最終建成中國的空間工程大系統(tǒng)。
有人說科學(xué)是“爭吵”學(xué),這話不無道理,因為真理總是越辯越明。
飛船的方案也是“吵”出來的。當(dāng)時專家提出飛船的方案有兩類,一類是三艙方案,一類是兩艙方案。即便是三艙方案也有軌道艙在前還是返回艙在前的兩個選擇。兩艙方案雖然構(gòu)型簡單,但安全性較差。所以討論之下,未被采用。
有人說,返回艙應(yīng)放在最上面(現(xiàn)在神舟飛船的返回艙在推進(jìn)艙上面最底部),因為一旦飛船發(fā)生意外,可迅速從逃逸塔逃逸,而且也節(jié)省了發(fā)動機的功率。但這樣做有它明確的缺陷,返回艙的大底要開一道門,航天員才能進(jìn)入軌道艙,而從飛船密封角度講,大底是不能動的。
飛船返回時還曾考慮用翼傘實現(xiàn)降落,也經(jīng)多方論證后下馬。
航天專家們不怕“吵”,甚至熱衷于“吵”,只要能“吵”出最佳方案,他們就愿意。1991年年底,飛船方案也基本“吵”熟了。
在1991年開始轉(zhuǎn)入倒計時的幾天里,“863”航天領(lǐng)域?qū)<椅瘑T會的專家聚集北京后海邊上的廠橋基地,緊張地草擬飛船技術(shù)要求。5年多的努力終要修成正果,飛船的任務(wù)、指標(biāo)、技術(shù)要求等用精確的數(shù)字描繪得愈來愈清晰,幾代航天人的飛天夙愿在他們手中將搭建得見棱見角。
1992年1月8日,中央專委再一次聽取專家委員會匯報后,決定中國載人航天從預(yù)先研究轉(zhuǎn)入工程技術(shù)、經(jīng)濟(jì)可行性論證。以王永志為組長的可行性論證組,集中了200名專家,用6個月的時間從經(jīng)濟(jì)可能性、技術(shù)可行性、技術(shù)發(fā)展必要性等方面進(jìn)行了系統(tǒng)論證,編寫完成了載人飛船的立項論證報告。
中國是在美俄之后40多年才開始研制載人飛船的。從加加林乘坐的蘇聯(lián)第一代“東方一號”載人飛船,到經(jīng)過完善改進(jìn)后的第三代“聯(lián)盟號”飛船,之后繼續(xù)改型,研制了“聯(lián)盟T”和“聯(lián)盟TM”載人飛船,俄羅斯的載人飛船技術(shù)被公認(rèn)為是世界上最成熟、最先進(jìn)的。
中國載人飛船開始研制的時候,正當(dāng)“聯(lián)盟TM”飛船問世不久,中國的科技人員就以“聯(lián)盟TM”飛船為趕超目標(biāo),采用了由推進(jìn)艙、返回艙、軌道艙及附加段組成的三艙一段方案。這個方案的確立讓中國載人航天從開始就占據(jù)了制高點。
中國的飛船設(shè)計起點高,適用性強,可一船多用,而且設(shè)計了更先進(jìn)、更完善的逃逸和救生系統(tǒng)。
中國載人飛船首創(chuàng)軌道艙的留軌利用。軌道艙兼有生活艙和留軌試驗艙的功能,返回艙返回地面后,軌道艙可繼續(xù)在空間運行,進(jìn)行空間科學(xué)探測和技術(shù)試驗。同時,軌道艙還可以作為今后我國發(fā)展空間飛行器交會對接技術(shù)的目標(biāo)飛行器。
這意味著,一艘船的效益更加顯著。不但縮短了研制周期,降低了發(fā)射頻率,節(jié)約了大量經(jīng)費,還為后續(xù)關(guān)鍵技術(shù)攻關(guān)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是中國科學(xué)家探索出的一條跨越式發(fā)展道路,也是符合國情的中國特色。
1992年8月1日,時任國務(wù)院總理李鵬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第七次會議。中央專委的領(lǐng)導(dǎo)同志聽取可行性報告后,一致同意這個方案可以批準(zhǔn)立項,決定報中央審查批準(zhǔn)。由于事關(guān)重大,每位中央專委委員都鄭重地在報告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2016年10月19日,神舟十一號航天員景海鵬、陳冬進(jìn)入天宮二號實驗艙內(nèi)通過攝像通信系統(tǒng)向全國人民問好
1992年9月21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kuò)大會議,討論通過了《國防科工委關(guān)于開展我國載人飛船工程研制的請示》,決定實施載人航天工程,以決策時間命名,代號為“921”工程,并確定了我國載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江澤民說,今天就做個決定,要像當(dāng)年抓“兩彈一星”那樣去抓載人航天工程。要堅持不懈地、鍥而不舍地把載人航天工程搞上去。他強調(diào)指出,這個事要“靜靜地、堅持不懈地、鍥而不舍地去搞”,“要抓緊,抓而不緊等于不抓”。
中國載人航天由此掀開了嶄新的一頁。幾代人的飛天夢由此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行動,中國載人航天計劃成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