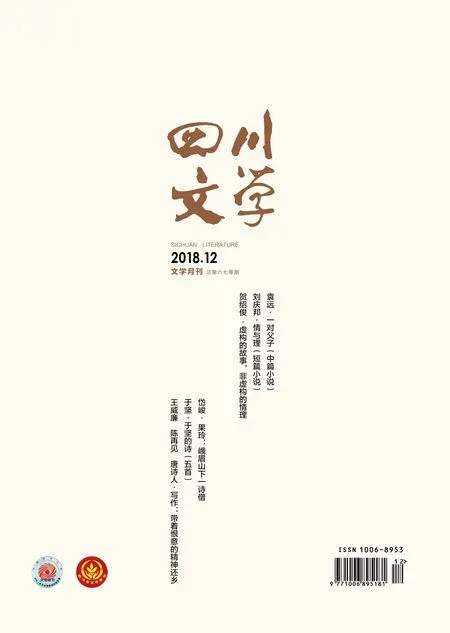果玲:峨眉山下一詩僧
峨眉山屬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為普賢菩薩道場。東晉以降迄今,朝山拜謁觀光游覽者甚眾,香火不絕。民國抗戰西遷,峨眉山地位突顯,曾為軍政要員避暑之地,如鄒魯、吳稚暉、居正、馮玉祥等,接踵而至。1935年,蔣介石為統一西南軍政,曾在峨眉山辦軍官訓練團;1939年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此接受蘇聯新任駐華大使潘友新(Paniushkin)遞交國書;同年秋,故宮南遷文物七千多箱,經上海、南京、西安等地,輾轉萬里,存藏于此。峨眉山也是戰時文化圣地,為躲避空襲,四川大學文理法學院曾遷此地;避寇入蜀的文人墨客也以登臨是幸。
報國寺是峨眉山門戶。彼時,果玲是報國寺方丈、峨眉山佛學會會長,曾接待過上述袞袞諸公。果玲好詩,出版過《果玲詩鈔》,與詩詞名家向楚、龐俊、曹經沅、邵祖平等時有唱和,亦投蜀中詩壇祭酒趙熙、林思進、方旭、周岸登等門下問學。他也收過一位“洋弟子”,那就是當今唯一懂漢語的諾獎文學評委馬悅然。“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戰時風云,把果玲吹上高天,也因改天換地,墜落溷穢。
1982年,臺北“國家”書店出版發行《歷代名僧詩詞選》,收錄民國詩僧弘一、果玲、曼殊(號博經)、敬安(號八指頭陀)等四人詩作。弘一、曼殊蜚聲海內外,八指頭陀名聞遐邇,唯獨果玲鮮為人知。是書介紹:“果玲,民國初四川人,俗姓方。自謂桐城之后,落發于報國寺,趙堯生推薦為‘峨眉山下一詩僧’。惟大陸陷匪后不知所終,其詩亦少流播,僅見抗戰勝利后所作之感賦四首而已。”2005年,巴蜀書社出版《近代巴蜀詩鈔》,收錄1840年至1949年間蜀中詩人202家,凡五千余首,其中收錄“僧果玲五首”,作者簡介寥寥數語:“果玲,峨眉僧,生卒不詳。與趙堯生、林山腴、方鶴齋相友善。有《果玲詩鈔》。”
筆者為寫此文,曾向流沙河先生請益,蒙指點曾聞訊樂山方家一壺諸先生,皆未得其詳,甚至未知其人。樹有根水有源。果玲者何人?緣何神龍見首不見尾?
“中央和尚”
報國寺是位于峨眉山腳的第一禪林,建于明萬歷年間,初名“會宗堂”,毀于晚明“張獻忠之亂”,清中期重修。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圣上以佛經“報國主恩”之意,敕名“報國寺”。佛寺背倚峨眉山麓鳳凰坪,左臨鳳凰湖,右攬來鳳亭。寺周古木參天,一道清泉,從北至南,婉轉流淌。上個世紀30年代初,和尚果玲擔任住持,農禪并舉,報國寺日漸中興,山門、彌勒殿、大雄殿、七佛殿和藏經樓依山而建,壯麗巍峨。馮玉祥曾寫過一首打油詩:“我到峨眉山,住在報國寺。先見大和尚,法號果玲氏。廟在山腳下,游人多必至……”他在回憶錄中介紹:
這廟里有個和尚叫果玲,他是安徽桐城人。一九一二年他搬著他父親的靈柩從西康來,走到這附近,正趕上殺趙爾豐的時候,他不能走了,沒有辦法,出了家。后來又出去當兵,當書記,當參謀,以后又回來當和尚。前些年中央的軍隊趕共產黨到峨眉山來,所有的人都跑了,不敢露面,他是當過兵的和尚,當然不害怕,他就出來幫著軍隊燒火煮飯,找桌子板凳。辦峨眉訓練團的時候,他又招待過蔣先生,從此大家都恭維他,他就當起報國寺的方丈來了。
馮氏筆下,似有演義成分,頗類佛門英雄起于亂世。其時,日本全面侵華,野心昭然,天下將亡,僧侶也不能安坐。在上海,有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在湖南,有萬均法師等組織的湖南佛教青年服務團;在重慶,有樂觀法師組織的慈云寺僧侶救護隊。當時,峨眉山極樂寺長老也提議成立僧警隊,從各寺抽調青壯僧人50多名,著灰布僧裝,持木棍,分組巡山。有智有勇的果玲,自可一顯身手。而其真正騰達,則是馮氏所說的蔣辦訓練團時期。
蔣政權自1927年初立南京,寧漢分治。“中央”僅能控制江浙皖贛數省。四川軍閥連年混戰,防區割據,南京政府鞭長莫及。“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呼聲高漲。1934年,蔣汪合作,中原大戰結束,南京政府基本實現全國統一。在中日全面戰爭一觸即發的態勢下,南京政權擬定四川為全國抗戰基地。“四川王”劉湘進剿紅軍慘敗,至南京謁蔣,表示“四川為中央之四川,本人負川省善后責任,一切唯中央之命是聽。”經過一番討價還價,1935年中央軍參謀團入川。
是年8月4日至9月21日,川滇黔諸省上尉以上軍官及地方政教人員四千余人,分兩期會集峨眉山,參加輪訓。蔣任軍訓團長,劉湘任副團長,陳誠任教育長,24軍軍長劉文輝、45軍軍長鄧錫侯、貴陽綏靖主任薛岳、20軍軍長楊森、23軍軍長劉邦俊、21軍第一師師長唐式遵、新編第六師師長李家鈺等分任團附。團部設報國寺。蔣與夫人宋美齡下榻近處新開寺,那里曾是外國傳教士的夏日避暑區。每周三天,蔣氏獨住報國寺吟翠樓處理公務。據當時曾上峨眉山采訪的成都記者車壽周所見:
斯時正值“峨眉軍訓”開辦,人馬嘈雜,新開寺古剎之下,盡是鋼盔軍士荷槍站崗,吆喝連天,把一座清幽雅靜的名山鬧得不亦樂乎。黃灣一帶,簡直成為兵山一座,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車壽周,后改名車輻,與筆者是忘年交,2013年初故去。時為成都《新新新聞》報記者,受報館委派,采訪峨眉山軍官訓練團新聞花絮,經報國寺臨時郵局姜姓局長引薦,認識了方丈果玲,采訪得以順利完成,文章見報,后收進宇宙風社于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出版之《談風》雜志第十八期。從發表日期判斷,距離軍訓開團時間近,在場參與及目擊者是可能的讀者,故此內容大致可信,以下將多處征引。
蔣介石辦訓練團,是基于“安內”與“攘外”這一大背景。8月13日,蔣作《革命軍的基本要素》演講,主要內容為:在團所聞大道,應精切體驗,即知即行;篤信三民主義,必能增加革命力量,所向無敵;認識領袖,信仰領袖與服從領袖之必要;要做總理系統之下一個真正的革命軍人;凡違反三民主義者即革命軍之敵人;有紀律然后有組織,有組織然后有力量;精誠團結,實現主義,完成革命。——要旨不外“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大言高論,以其昭昭使人昏昏。也足見“革命”一詞甚為時髦,但如梁任公所言,革命而可以止革命,則國家之福;革命而適以產革命,則其禍福待審。
訓練團開辦的某一天——
蔣公來也。身著黃絨呢軍服,手拿黃呢博士帽,除前頭頂微禿之外,精神是蠻好的,笑容可掬,后面隨了幾十名大將,一點也不威風,斯文胎胎,令人入睡。同時,確忙煞了果玲,穿起黑綢袈裟,招待指導。
“我們太麻煩你了,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直管告訴我。”蔣公向他和顏悅色地說道。
“不,不麻煩。為了國家,理當如此。”果玲恭而且敬地回答,陪著參觀了七佛殿,及寺內重要地方一周。
當時,我們在客廳退堂中(即郵局臨時地方),姜君忙穿禮服,站在退堂旁邊恭迎。果然來了,這位蓋世英雄距我們不過五米之遙。而且聽著他指到匾上吳稚暉寫的篆書“峨眉天下秀”說,“這是吳老先生寫的,很好。”蔣公打著藍青官話。當時我心中微微作跳,畢竟是蓋世英雄啊。也不如想象中的可畏,臉是白白的,兩頰微陷,發略斑白,若謂書生面孔,誰曰不宜?即出客堂,在三番軍樂中打駕上新開寺辦公處去了。果玲走來,捏著汗顏地向我說:“非常客氣,非常客氣!”一面說一面卸袈裟,一面招呼我坐。
此時,果玲方登臺入戲。果見他長袖善舞,巧結善緣,然事雜緒多,也難免左支右絀。
軍訓中千百將士,應付自如,無不嘆為八面玲瓏的“千手千眼佛”。有時伙夫找他借個地方安置造膳炊具,有時某將軍請他選一點地方作為私人斗居……一天到晚鬧得人頭昏。而他毫不介意,來一個答一個,早上五點鐘前就被人催醒,晚上一兩點鐘尚在處理零碎事物。論當年大觀園修葺時的王熙鳳賣盡氣力,也怕要遜點色吧?如此說來,他是鐵打的金剛不成?不,有時他也向我嚅囁道,“報國寺要果玲才累得下來呀!”……果玲是個深深懂得幽默的和尚,他往日的清凈,以至于軍訓時的嘈雜,寺院的東毀西撤,難道他真的無動于衷么?不過他說不出來罷了!于是,他只好倒在床上做起詩來:“河山乏凈土,寺院半成灰。補救無長策,枕經臥碧臺。”
其時也有趣聞。上世紀90年代,某一地方政協文史資料介紹,當年某日,蔣宋等人登山游覽。果玲導前,余等各乘藤轎,在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及侍衛簇擁下,出報國寺右行,過伏虎寺、雷音寺,穿龍江棧道,過鉆天坡,一路逶迤。抵洗象池一帶,古樹參天,猴群出沒,伸手索食。侍從有備,也不免驚慌,把餅干花生什物拋完后,猴群仍不閃道。一只大公猴公然躥到蔣的藤轎前,伸出毛茸茸的雙臂。侍從已拔槍相對。蔣忽然摘下帽子,對猴王連連揮動,“去!去!”猴王瞪著圓眼,轉身呼嘯而去,群猴也競相躲進山林。“委員長威臨天下,美猴王畏懼三分。”有隨從恭維,蔣氏也覺受用。此事經媒體渲染,越傳越神。其后,中央通訊社記者徐怨宇上峨眉山,找到果玲,一探究竟。果玲說:“猴子乃‘山居士’,不會無故傷人。冰天雪地之時,僧人也會投以食物。久之,猴見光頭師傅總要頂禮。所以,猴王給委員長讓路,并不為奇。”講述者為湖北省政協文史專員,且姑妄聽之。
總之,一個普通山僧,因沾溉廟堂之氣,身份由此改變。
(當時,入蔣的臨時官邸)無論如何大官均需先行請見,由侍從室指定時日方可。獨果玲不然,他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曾經把峨眉山最好吃的雪魔芋豆腐贈給蔣公吃過,甚至蔣公連聲稱好,還說再要。同時,他對于伙夫勤務兵也說得來,視如一體,不分高下。以致軍訓開課時,“中央和尚”之名,已傳遍峨眉山了。
“峨眉軍訓”完結,蔣公特地給他建了一坊石碑,以示果玲之有功于國。當時曾有不少的軍官請他還俗任事,都鑒于他的大才可用。但他不允。后來蔣公亦言,在日后黃山之上建一座廟與之,他還是不受。
記者之言,是否有據,無從稽考。但果玲一直以蔣臨別時給報國寺所題“精忠報國”匾額,及送給自己的那幀便裝簽名照洋洋得意。
玲瓏即禪機
果玲身世,各說不一,撲朔迷離。諸如果玲,號曼魂,俗姓方,祖籍安徽桐城,生于四川越西,出生年月不詳。 出家前,有人說他在大學教過國文,有人說他系行伍出身,有人說他當過記者……民國二十一年(1932) ,他出家峨眉山報國寺,拜圣泉上人為師,次年到重慶華巖寺受具足戒,后又回報國寺。……
唯有《漢源縣志·人物志》考證翔實。據其所道,釋果玲(1894-1950),俗名方家禧,字梓福,漢源縣河南鄉人。畢業于越西縣高等小學堂,曾在越西縣北區小學任教。24歲那年,飛來橫禍。因喪偶被妻家以命案控告,人財兩空,家破人亡,遂投奔嘉定陸軍第八師第十六旅蔣安廷部。蔣旅長以同鄉之誼,授果玲旅部秘書。未幾,劉文輝解除八師,蔣安廷解甲歸田,方家禧自樂山乘舟往重慶找出路。殊所投不遇,錢財告罄。某日街頭徘徊,忽遇一僧,竟是原八師結拜好友葉某。二人敘談,不甚唏噓。經葉引薦,方家禧暫棲華巖寺。方丈見其博聞廣識,也視為掛單之行腳僧。遂也上殿敬香,經堂聽講,齋堂用膳,翻閱經卷,漸悟禪理。
其時,科舉已廢,以廟興學漸成新風,華巖寺也勢不可當。楊森駐守重慶,其寵妾三姨太,每逢朔望,必至華巖寺上香禮佛。方家禧披上袈裟,扮作僧人,迎候三姨太,相機進言。三姨太應允進枕邊言。其后,華巖寺廟產無虞,楊森下令將其定為勝跡,尤加保護。華巖寺僧眾,對方家禧越漸信服。他本無心為僧,但在方丈苦口勸說下,終褪去藍衫,披剃出家,當了和尚,法名“果玲”。其后,果玲遷單峨眉山報國寺,先為知客,1932年為住持。至此,開啟峨眉山的果玲紀元。
1934年秋,峨眉山朝山路上建起一道單跨木牌坊,住持果玲托請川籍要人榜書“名山起點”四個字,報國寺成朝山游覽必至的一大禪林。
1935年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來峨眉山,果玲央請賜贈墨寶,吳稚暉題贈對聯:“佛法本無邊;天心出自然”。此聯遂成為懸掛報國寺山門的金字招牌。同年,得辦訓練團之機,果玲一夜成名。
1936年4月,教育家、近代職業教育創始人黃炎培游峨眉,在日記中寫道:“1日……六時半,至山下報國寺宿。和尚果玲頗文雅,仁尚知客……2日 星期四陰雨 為報國寺僧果玲寫聯:沙彌自覺方宜剃,余樂游程亦見環。”
1937年,普超大和尚辭去峨眉山佛教會會長職,果玲接任,更名“中國佛教會峨眉名山區佛教會”,獨立對外,且管控全山佛教事務。
1938年秋,果玲在奉呈下榻此地的國民黨元老鄒魯的詩里寫道:
鄒海濱先生于8月14日住宿報國寺。翌晨,領眾早課,銀河在望,圓月生衣。下殿一鐘,天始發白。木魚梵唱,未知曾警老人清夢不?抒懷奉呈。
興發大地若沉舟,為祝如來護壯猷。(蔣總裁駐節本寺浹旬)
斷續鐘聲警客夢,團圞月色上僧樓。
山間制梃余荒壘,方外無刀抱杞憂。(僧人原佩戒刀,后乃不準)
漫把烽煙傳太急,終輸萬眾起同愁。

俗緣卻盡趣橫生,寫出瀟湘竹幾莖。
斗室頓教風習習,壁間疑有鳳來鳴。
民國元老狄君武游峨眉山報國寺,“寺僧果玲指吟翠樓謂,廿四年蔣委員長曾宿此”,狄氏遂作《峨眉報國吟翠樓題壁》,詩云:
一寺精忠寫百憂,山間制梃有深謀。
蜀中弟子休相問,夜發兵書吟翠樓。
此時果玲,常見得色。經歷是改變命運的契機,也是難卸的行囊,正如佛家之無常,一切隨時空變異。
1939年2月下旬,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聞父染病臥床,告假返鄉。乘郵政總局與中國航空公司開辟的水上飛機,回到樂山沙灣老家。探望病榻上的父親后,郭氏在家人陪同下,去羅河坎墓地祭奠母親。次日,應“峨眉縣青年抗日聯合會”之邀,到岳王宮小學演講,郭沫若向鄉親父老闡述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道理。第三天上午,他在川大助教任柳村陪同下,在峨眉山腳游覽。聞訊在此等候多時的果玲,邀請郭廳長“若是不棄,請到小廟歇腳”。郭沫若進到報國寺,見和尚談吐不俗,頗生興味。果玲介紹:“前幾年,委員長辦軍官訓練團,就下榻本寺吟翠樓。此處風景清幽,先生愿否去喝杯清茶?”郭氏稍事猶豫,也就上了吟翠樓。但見遠山含黛,近樹蒼翠,窗前掠過鳥影,寧靜中猶帶生趣。坐定,茶敘。果玲早備有文房四寶,懇請題字。郭沫若略一思忖,揮筆寫下一藏頭聯:“果決方能精進,玲瓏便是禪機”。雖是應酬,總歸是“字以人貴”。
戰時峨眉山,云海洶涌,名流政要,不絕于途。如國府經濟部長翁文灝(1938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939年6月23日至9月12日),中央黨部組織部部長、中統局長朱家驊(1942年8月25至29日),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1942年8月30日);國民黨元老吳稚暉(1942年9月15至17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1944年7月24日),國府軍委會參謀次長白崇禧(1944年4月24至27日),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王陵基 (1945年11月23日)……作為“名山起點”的大和尚,鞍前馬后能“果決”,迎來送往必然“玲瓏”。深諳江湖事,亦為苦命人。
按說,既為“中央和尚”,可走政治路線,攀附上位,果玲卻偏偏好風雅、重斯文。這些也都體現在他的小世界報國寺:
寺前門上懸掛“半輪山月,大悲海云”聯,為趙熙手筆,秀勁可喜。第二門上懸陳誠將軍“報國寺”橫額及蔣委員長手書“精忠報國”四字,旁并鐫之于石,遒勁有神,名山得此,相形益彰。下懸“浮生若夢境,到此愧鐘聲”木刻,瀟灑飛舞,為杜偉所撰書。檐前懸天草六盆,如垂燈狀,青翠欲滴。寺左為客堂,聯曰:“四山滴翠環初地,一路聽泉到上方”。室中架上置民廿四年秋,委座贈該寺住持果玲和尚玉照一幀。板壁并懸吳敬恒、居正諸氏及梁鼎銘氏馬畫。正中橫懸甲戌年中秋趙熙題贈果玲法師詩,木刻頗佳,詩云:“老來問法到南能,國家愴涼感幾興,獨向明月彈綠綺,峨眉山下一詩僧。”
衲子亦詩僧
那些年,高小畢業,當過小學老師,就是名副其實的知識人;于是對知識與同類,也就有了理性的渴求與情感上的親近。
上世紀30年代初,南京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方文培,帶領兩名助手,來到峨眉山,作動植物考察和標本采集。他們先拜訪報國寺果玲和尚,說明來意,獲其支持,在峨眉山考察了一個多月,采集一千多號植物標本,共一萬多份,其中在九老洞、新殿、華嚴頂發現的木瓜紅,在清音閣黑龍江畔發現的花佩,是兩個植物新屬;在雷洞坪和接引殿發現的冷箭竹,是首次發現的世界上一個植物新品種。
1939年秋,川大生物系主任方文培隨校遷徙,再到峨眉山,與報國寺方丈果玲已然老友。在此四年間,方文培得到果玲扶助,一有空就上山考察,確認峨眉山植物,至少在1000種以上。他選出有代表性的兩百多種,編成《峨眉山植物圖志》,1942年由華英書局出版,引起海內外學者注目。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向他祝賀,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授予他一枚銀質獎章。其間,果玲曾動員僧眾為方教授采擷制作植物標本,如報春花、杜鵑花、珙桐花、木瓜花、毛花槭、黃肉楠……制作雖不盡合乎標準,但還是讓方教授心存感激。在其科考論文中,曾多處提到對果玲的敬意和謝意。
果玲到底是以詩僧名世。古人道,“自古詩人例入蜀”,“周觀天下,但恨不能至益州耳”。凡到四川的文人雅士,多半會朝峨眉,于是峨眉山也相當于半部巴蜀詩史。報國寺是峨眉山的大廟,寺內名家詩石刻題記,自是琳瑯滿目。
1938年,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陳鐘凡游峨眉山,寫有《峨眉紀游》十七首,其中《薄暮下山,至報國寺遇果玲上人》寫道:
佛為山頭奏鳳笙,高僧山腳笑相迎,
參差暮色隨人至,島可山房事事清。

果玲寫詩且多產。1939年2月,盧冀野主編的《民族詩壇》第二卷第四輯刊有果玲的絕句《奉和伯毅先生見贈原韻》《讀羅家倫先生殲敵諸作后即次其老山絕句韻》。
名流風度好登臨,佳句吟成濟世心。
話到峨眉制梃日,果然報國屬禪林。
峨峰九月語人稀,天轉文星炤衲衣。
行草書成殲敵句,禪心已定忽高飛。
曾下榻報國寺的國民黨元老居正,對其有微詞,稱“果玲頗能詩,雅而近俗。”居正此語,莫非是指果玲的“詩外功夫”?
果玲俗姓方,祖上為“湖廣填四川”時自安徽桐城遷來。故與成都“五老七賢”之首方旭(字鶴叟)攀宗親。方旭自川東道上來,有詩稿《鶴齋詩存》存世。其中有“六州鑄錯因思蜀,千萬買鄰難避秦”句,寫出萬端滄桑。鶴叟贈果玲的詩有“峨眉方家有果玲”句。1934年,還正書自撰聯:“秀語奪山綠,澄懷悟水源。”上款:“果玲和尚雅玩”,下款:“鶴叟年八十五”;款下鈐白文“桐城方旭之印”,朱文“鶴叟八十后作”。于是果玲俗家系出名門,有了旁證。
其時,蜀中詩壇祭酒公推益州林思進和榮州趙熙。
果玲對林思進執禮甚恭,問候殷勤。1939年6月11日,日機轟炸成都,造成慘重損失。各行政事業單位紛紛離城外遷。聽聞國立四川大學(下稱川大)有動遷之議,果玲便去函力邀老教授林思進來寺棲居,稱已掃榻恭候。林氏贈詩答謝,序曰:“四川大學移講峨眉,予初欲從往,果玲長老亦除精舍相待。尋念年衰遠涉,暑雨祁寒,都非所堪,行計頓輟。因作小詩寄長老謝其意。”詩曰:
峨眉秀天半,擬訪仲陵居。
佳處留茅屋,山僧有報書。
云山夢昔繞,筋力恨今無。
遙想齋鐘罷,清吟對木魚。
趙熙(字堯生,號香宋),曾為前清翰林御史,民國肇始,息影林下,世稱“堯老”。有人道,“峨眉報國寺僧果玲,能為詩,而好(堯生)老人之詩。為老人私淑弟子,力任刻石之事。”每逢清明前后,果玲必寄奉茶禮。庚辰(1940年)春,趙熙收到新茶,贈詩《果玲惠峨眉茶》云:“雨水新芽寄草堂,峨眉山翠一囊香。不留蘭若充詩料,剛助花朝宴海棠。小吏捉人鄉戶減,貧家入市紙錢慌,玉川何忍耽明月,聊趁春分謝寶坊。”
1939年秋,川大遷到峨眉,校本部設報國寺,文學院法學院設伏虎寺,理學院和化驗專修班在萬行莊。低山區鞠槽、保寧寺、善覺寺等權作師生臨時住宿點。峨眉山大和尚果玲以東道主身份協助安置,參與治安維護諸事宜。
川大教授周岸登,號癸叔,晚清舉人,曾任廣西全州知州、江西廬陵道尹。二十年代末辭官從教,1935年轉川大文學院,講授詞曲與金石學。果玲趨前拜師,虔誠討教。川大教授彭靜中曾寫道:
(周岸登)教學之暇,有住所報國寺僧果玲,時來請教拜師。先生說峨眉天下秀,出游山中者,住在山中者,古往今來,不知凡幾。真似陸放翁之“恨渠生來不讀書,江山如此一句無!”汝能詩題峨山,真是子福。遂教果玲作詩之法,后漸能吟詠。
川大文學院教授向楚、龐俊、李思純等,同為師輩。親近這群“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學者詩人,果玲始入門墻。
戰時多難,人們以詩詞唱和為寄為樂。果玲曾寫“茶韻詩”,以期拋磚引玉。榮縣趙熙作《和果玲懷林山公》詩:
舍人不耐市聲嘩,霜閣閑煎黛黛花。
亂世立身原有節,老來無睡不宜茶。
多君好句無僧氣,自古名流佞佛家。
過分召災懸戒品,近來江埠亦奢華。
趙熙門生、璧山人江庸(1878~1960年,字翊云,晚號澹翁),是留日的著名法學家,續《果玲上人見懷并呈香宋師,七言律詩,押麻韻》 :
一塵不讓寺門嘩,只看珙桐幾樹花。
禪榻未親煨芋火,霜柑先餉露芽茶。
橫溪閣近詩留壁,迎翠樓高客當家。
咫尺靈山原易到,何愁集分與龍華。

詩心梵籟兩無嘩,想見諸天盡雨花。
著我差宜三畝竹,勞君頻致上方茶。
橫流何地容安撫,窮子多年總憶家。
為語洪椿坪上客,要留高會續龍華。

寺深夜靜百蟲嘩,松籟杉寒桂著花。
天挺峨眉標獨秀,詩盟白水當清茶。
秋來伏虎山多雨,老羨蝸牛殼是家。
大好三分明月處,卜居方擬送年華。
向楚居報國寺附近的“蝸牛殼”,與果玲寮房近在咫尺,常通魚雁:
初抵報國寺,果玲上人贈詩,依韻奉酬。
海潮音好即蘇韓,左挹浮邱右拍肩。
夜色呼燈親送客,秋心入桂欲薰禪。
名山今著向平子,慧業前生賈浪仙。
趁讀桐城方外集,逃空漸覺遠塵緣。
和果玲上人九日雨中懷人韻
雨中山興阻重陽,客鬢吳霜又蜀霜。
對酒寺樓深入夜,誅茅拓徑等開疆。
待餐秀色需晴霽,好種秋花稱淡妝。
一樣禪林清凈地,初來聞過木樨香。
向楚移講杏壇,仍被選為第一、第二屆省參議員。趙熙贈詩,有“參知何政事,夜望隔云層。濯錦還為客,言詩可招僧”的句子,以之警醒。
1940年秋,趙熙門人、烏尤寺僧人遍能來謁報國寺。他也尊周岸登、向楚等為師。于是,眾詩友相邀出游,逸興勃發,逶迤而行,賞景賦詩。彼時,遍能年齒最少,周岸登已逾古稀。果玲遂提議以“能”(遍能)、“登”(周岸登)為詩韻。遠山生煙,霜林染醉,觸景生情,為之大快。即使高山遇雨,也絲毫未減“能登”之樂,也因此成就一段巴蜀詩話——
向楚“由鉆天坡上洗象池,雨中和果玲上人韻。遍能禪師約同果玲上人、周癸叔主任同訪峨眉諸勝”,詩云:
鶻沒天低處,梯云最上層。山卻工雨景,游伴得詩僧。
濟勝憑何具,窮高苦未能。閑思秋嘯月,容我辨孫登。
再酬果玲
一雨迷山綠,連云作畫層。迄無收雨勢,聊共看云僧。
攬勝留三日,題碑謝九能。象池今夕醉,高臥比陳等。
山高接云霓,放眼天更寬。周岸登次韻《希特拉》:
創開中外史,首出霸王層。有社方為國,無妻不是僧。
拿翁慚狠鷙,該撒謝功能。三會慕尼黑,何如相艾登。
希特拉今譯希特勒,該撒譯凱撒,相艾登即二戰時英國副相羅伯特·安東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詩翁感時戲作,俗不傷雅,視野宏闊,博得眾彩。

山如蜜脾滑,蜂子上花層。 畫出鉆天路,詩偕報國僧。
文心高北斗,崖口造南能。 險似征蠻否,提戈踏白登。
云衣縫疊疊,苔履綠層層。 路厭秋多雨,崖高樹若僧。
老來工健步,方外重修能。 謝客慚山賊,詩如歲不登。

民國二十九年(1940),釋果玲等撰《能登集》石印本在成都問世,輯詩一百三十首。其中趙熙四十一首,向楚十四首,果玲五首,周岸登七十首。詩集傳世,震驚文壇,流韻深廣,堪稱戰時文壇盛事。
兩年后(1942年春),川大國文教授邵祖平讀到果玲所贈《能登集》,依韻作《報國寺監院師果玲招飲留宿寺中帶月山房》:
新詩脫手贈能登,過院欣逢退院僧。
河酒三鍾言有味,寒林一徑氣初澂。
早親名士耽神駿,晚注經文近佛燈。
我憩上方等行腳,半輪分得是圓冰。
林思進也有《果玲上人退院,有詩索和》佐證:
近得山中信,聞師退席閑。 閉門好覓句,拄杖只看山。
妙悟林巒外,清才粲可間。 一瓶一盞凈,未羨紫衣還。
是“欣”是“戚”,或“辭”或“受”?冷暖自知。度其原委,與近詩壇、冷佛堂,薄僧眾當不無關系。而今后果玲因此“一瓶一盞”,“凈眼觀緣”,“晚注經文”否?慣之成習,猶三尺之冰。
1942年深秋,趙熙在江庸、曹經沅等門生簇擁下,終于再上峨山。果玲派人去接,向楚、龐俊、李思純等在報國寺山門守望。老人欣至,蓬蓽生輝,酬酢賦詩,仍以“能登”為韻。
趙熙作《送果玲歸峨眉》:
送子還山去,蕉心書百層。
世衰無舊學,吟苦即名僧。
便道經嘉定,因君憶遍能。
珠宮來海色,佳玉藉文登。
曹經沅作《漢嘉道中次能、登韻》:
交臂烏尤欠一登,回看峨頂雪層層。
重來我是籠紗客,久別山如面壁僧。
入彀群才歸長養,盪胸健句自騫騰。
飛牋且與匡君約,買棹東還指日能。
1943年春,四川大學回遷成都。當年《川大校刊》載,“川大遷回成都,峨山各大寺院住持均極惋惜。報國寺住持果玲能文工詩,與川大教授時有詩文往返,尤為依戀。伏虎寺住持于餞行席上稱,川大遠去,山寺失一大保護人,此后情況若何不敢逆料……每一念及,無不揣揣于懷也。”
佛子也有“傷別離,求不得”之苦么?
“救救和尚”
果玲有詩,“禪身未到菩提岸”。按說,一入僧門,當持戒修身,聽晨鐘暮鼓,守青燈黃卷,唯悉心禮佛。而果玲沉溺詩詞,樂于社交,頗有“野狐禪”味道。
報國寺僧人法名字輩,取自臨濟宗派行詩十二首中的第七和第八首:“能仁圣果”,“常演寬宏”。比如,果玲的徒弟是峨眉山金頂寺的方丈常鼎,常鼎的徒弟是演慧,演慧的徒弟是寬能。采訪過果玲的記者車壽周寫道:
他對于一般和尚的批評,是說他們在學和尚,徒具和尚外表而已,對于佛的深層研究毫無,自己本身又不從事生產,年來川中軍閥大提廟產,弄得不能謀生,只好走向“西方”去了……
報國寺中有小沙彌數十,淘氣得很,據果玲的意思,遲早要遣散他們,或送回老家,他說這種強奸似的強迫出家,根本就是違背了佛的意旨。退一步說,他們的一切果玲都可保險無虞,唯獨“性”字,他是無法解決。
關于佛的研究,他認為非大學畢業不可,這是一部專門學問,修身養性的工具,不是消極的,否則釋迦牟尼也絕不會放下王子身份去度眾生。
1942年,徐鼎銘游峨眉山住宿報國寺。“飯后稍事休息,即訪演鴻法師,知峨眉山全山現有和尚百余(小僧不計)散住在山中各寺。報國寺只分住三十余人,寺租三百余石。小沙彌來源多系各方貧孤送寺教養者,寺中自設小學,教以普通文字,通順后即學誦經,至二十歲以上,乃施以考驗,及格后方得受戒,收入佛門。否則即可退去。”
寺廟大和尚即一家之主,可以賞罰予奪。報國寺其余和尚“禪(禪宗)凈(凈土宗)兼修”。方丈果玲修禪宗,“饑來則食,困來則眠”,率性而為。
果玲早已鴉片成癮,常一榻橫陳,吞云吐霧。1935年,記者車壽周曾走進方丈室:
趁午飯平靜中,入果玲方丈室閑談。琳瑯滿目,牙箋類列,除各大家詩存外,佛經要算第一。從他“安禪怕上藏經樓”一句詩來看,這么多佛經他是難得瀏覽的。室中有濃香撲鼻,窗外青山秀麗,蟬鳴鳥語,雖然殿上吵鬧,而他這一室中又卻如世外桃源。床上放有黃仲則詩集,煙燈一盞,霎時云霧大作,與窗外青山陡起的嵐障大相輝映,抽煙之聲嗦嗦,又同松嘯林吼為對律。果玲之豪放不羈有如此,說不定他是要吃油大的?不久,某旅長入室也來湊鬧熱,我乃他去,何苦那么不識相呢?
佛家慈悲,倡眾生平等,“五戒”第一即不殺生。果玲卻以不殺人為戒殺之根本。“不吃黃鱔,也不吃牛肉。可是他豬肝炒得特別好!”或以眼不見為凈。
“不邪淫”為僧律“五戒”之一。貪淫之人,則“駛流河中”,“死墮惡道”, “割截燒滅”,“萬劫不復”。而人乃肉體凡胎,不免有七情六欲,香火傳奇。車壽周曾試圖探尋曼魂(果玲筆名)出家之因:
丈室孤燈黯欲無,殘箋揀得代新書。
山君若問山僧況,秋風秋雨病曼殊。
的確,他有才不得與時,比曼殊是很恰當的。至此,不由得不叫我去尋找他為什么要出家,但我又不好向他直截了當地問。往后,我在他的一本《自懺四律》中找到第四律:
前身艷福未雙修,一局殘棋泣苦囚。
絮果蘭因齊悟徹,情天恨海共沉浮。
傷心莫向菱花照,淚眼嘗從柳葉偷。
孽債重重難懺悔,安禪怕上藏經樓。
這位詩人、幽默者、果玲和尚,他過去的生活,在蛛絲馬跡中大抵是使我們明了了。
1939年,國民黨主席林森下榻峨眉山。據其“消夏日記”:
六月二十六日 晨八時,上山起點,……行四里許,入報國寺,住持果鈴能詩,又聞多某秀才捉刀。相貌類李一平,惟眼現鼠光。佛教分會會長白面僧,頗秀雅。俗言此二僧與二尼結緣,諒系謗謠,污我佛子。
流言蜚語,也飄進程天放的耳朵,這位在峨眉山食息四載的川大校長回憶:
報國寺的住持果玲是峨眉最出名的和尚,因為蔣委員長曾駐節報國寺,又因為中央要人來游峨眉的也必經報國寺,所以他認識的達官貴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曾題字送他。果玲因為有了早年的名氣,不好意思公開吃葷,可是背里一樣吃豬牛雞鴨。他并且沾染了鴉片煙癮,天天要吞云吐霧。為了滿足性欲,他還和報國寺一個佃戶的妻子同居。這樣的和尚可以做住持,還有什么清規可言?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馮玉祥的一段故事。馮玉祥是在民國三十年夏天來峨眉游覽的,也住在報國寺。因為他身體太重,普通的滑竿根本載不起……馮玉祥游山不成,一肚子不痛快,所以回到重慶后就寫了一首詩,借和尚來出氣。那首詩相當長,我只記得中間兩句:“峨眉山,真繁華,衛生麻將唪啦啦。峨眉山,其稀奇,和尚占了佃戶妻。”
此事,馮玉祥自有言說。1941年3月9日,馮氏下榻報國寺“帶月山房”。次日,應程天放之邀,對一千多川大師生作“做大事,不作大官”的報告。當日晚,出席川大安徽同鄉會歡迎宴會。
有一天,安徽同鄉大學教授湊了八九位,一家做一碗菜,那就八九碗了。這位果玲和尚也是安徽人,他就添了一碗豆花,還請了程天放先生陪客。吃飯的時候,聽說重慶有電報來,要開六中全會,程先生問我去不去。
我說:“是的,不但去,我還要提個案子。”
他們就問提個什么案子。
我說:“提一個救救和尚的案子。”
他們說:“怎么講呢?”
我說:“和尚凡是愿娶女人的那讓他娶女人,不愿意娶的就隨便,這樣豈不救了和尚。”
果玲在旁邊說:“真是好案子!真是好案子!救了和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我說:“案子好是好,要是從報國寺回去提這個案子,恐怕別人說我受了果玲大和尚的運動吧。”
馮玉祥號稱“基督將軍”,1915年,他在北京亞斯理教堂受洗。他以16世紀德國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精神,反思佛教之弊,是耶非耶,見仁見智。那首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打油詩《救救和尚》,曾在佛教界引起軒然大波,原詩摘引如下:
峨眉山,真是奇,廟宇破敗無人理;
峨眉山,和尚住,窮的窮來富的富;
峨眉山,真有趣,和尚彼此生閑氣;
峨眉山,真堂皇,許多和尚臉發黃;
峨眉山,和尚安,不談抗戰談修仙;
峨眉山,有七層,和尚不妨娶女人;
峨眉山,李花白,和尚娶妻有著落;
峨眉山,桃花紅,娶妻省得胡鬧騰;
峨眉山,茶葉綠,有妻才有好約束;
峨眉山,水不死,釋迦牟尼有妻子;
峨眉山,石頭青,和尚有妻才正經;
峨眉山,和尚好,國家大事多不曉;
峨眉山,有佛光,穿愚無告我心傷;
不可罵,不可怪,
須把和尚當作子弟愛,
和尚是國民,都不是外人,
能有好教育,便可成萬能。
和尚是同胞,我們不能袖手瞧。
我們是四萬萬五千萬,
有的走錯了路,我們豈能袖手瞧。
比馮玉祥稍晚,西南聯大校委會常委梅貽琦、教授羅常培、鄭天挺等,也曾到報國寺,意在考察川大辦學經驗。7月12日,梅貽琦日記寫道:“五點半到報國寺,住廟西客室,名曰帶月山房。……方丈果玲頗示優待,惟此人終覺俗氣太重。善談能作詩,蓋以結交要人之具耳。頗有‘五十以前不宜出家,因內心沖動之故’,亦為其自身之外家作一辯護者。”7月13日,“早點在果玲處食豆漿稀飯……午后小睡,院中小亭上小和尚二三人磨墨伸紙,更番來請,謂系果玲囑請題字,堅辭拒之。”
同行語言學家羅常培有游記見報,雖為隱曲,但藏頭聯還是指名道姓。
說到峨眉的和尚,阿彌陀佛……就我這次所得到的印象,縱然沒有像某先生所說:“峨眉山有峰皆秀,無僧不俗”的地步,卻沒有碰見幾位教理宏達,戒行謹嚴的高僧……我所遇見的,有附庸風雅,借勢招搖的“詩僧”;有不甘寂寞,妨害別人家庭的淫僧;有“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滿嘴主席長,委員長短的勢僧;有在游客付香資時斜睨著鈔票上數碼,因為下雨便留你打牌的俗僧;有把山峰的名兒背得滾瓜爛熟,比說相聲的張壽臣小蘑菇還要嘴快的貧僧;有借著經營名勝為名,實際推銷茶葉的商僧:要想盡相窮形,恐怕更仆難數。
馮煥章先生游峨眉歸來,曾在大公報發表一首“救救和尚”長詩,可以替我作個佐證。我且引幾句最精彩的在下面(此略,見上引)。
由這幾句詩看起來,我們不難窺見峨眉山和尚的一斑了。他很希望有人作佛教的馬丁·路德,拿寺廟改學校,讓和尚能夠努力生產,自食其力,與其聽他們掩耳盜鈴的胡鬧,寧可解放一點,倒省得妨害別人的家庭。
我們剛到山下的那一晚,有一位很有名的和尚,聽說我們從重慶來,還以為我們已經看見這首長詩了呢,他就說:“和尚也是人,要想推行佛法非改善現在的僧伽制度,調整和尚的生活不可。告訴幾位檀越說,照我自己的經驗,五十歲以前出家實在苦極了。”……承他很殷勤的磨了兩三盤墨,讓我們題字,我很想送給他一副對聯,聯語是:“果否通佛法,玲瓏善交游”,匆匆忙忙的終于沒好意思寫出來。

“那個人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屠戶!”老和尚果玲很有涵養,但那時他非常生氣。因為聽說密宗法師能海要到峨眉山的萬年寺講經。我告訴我的老師(報國寺的方丈果玲)我愿意去聽。老和尚不要我去,但是我沒有聽他的話……“我從萬年寺回報國寺之后,老和尚果玲有兩個星期不理我。”
“救救和尚”的佛教改革倡議,筆者既遠廟堂也非檻內人,安敢置喙。然竊以為寄望佛門產生馬丁·路德似的新教領袖之觀點,未必不是書生之見,在黑暗如磐的戰時中國,這些洞見亦為偏見,不過是螢火過眼。移至今日,仍不得暢言。
1945年,四川省政府批準設立“峨山管理局”,辦公地址設報國寺,首任局長彭伯喜。果玲重回峨眉山主持佛教會工作。翌年春,邵祖平作《次韻和果玲詩僧還峨眉》詩以賀:
廿四花風風已闌,定巢雙燕壘初安。
吟依暖翠煙生岫,夢繞清江雨濕欄。
萬態天魔酣醉舞,一龕韋杵卓云寒。
知君又作名山主,定卜林深鳥語歡。
“大吃大杯”的洋徒弟
“云在天上,人在地上,影在水上,影在云上。”這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教弟子背過的一首詩。詩境禪意或與他那段峨眉經歷不無關系。
出生于瑞典南方的馬悅然,1946年考進斯德哥爾摩大學,跟隨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學中文。兩年后(1948年)獲美國洛克菲勒獎學金,到中國去做蜀方言調查。當年八九月份,他先在重慶、成都學西南官話,后去樂山研究當地方言,也即古蜀語。樂山縣長給果玲寫信,介紹馬悅然到峨眉山住在報國寺,并給果玲當徒弟。
馬悅然到達報國寺那天,是1949年的大年初一。“那時峨眉山一共有120座佛廟。報國寺是最大的廟宇,容有40個和尚。”但從來沒住過外國人。
每日早飯后,果玲到馬悅然的房間給他講授兩小時課。“每天早晨讀《四書》、漢詩、《唐詩三百首》、宋詞,也讀簡單的佛教經典。晚間坐禪,果玲教他幾次打坐,意馬心猿的洋弟子,始終未能到達“覺悟”的彼岸。“我永遠記得小和尚們每天晚上用清脆的聲音高高興興地唱晚上儀式的頭一首很憂郁的經文:‘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目。但念無常,慎勿放逸。’”馬悅然最著迷木魚伴奏下的諷誦儀式。誦、白、唱是僧人的基本功,但他始終進不了那種虔誠之境。
老和尚還試圖教洋弟子書法,但習慣刀叉的手對竹管毛筆一籌莫展,雖如此,卻依然對中國書法心存敬畏。他曾寫詩贊美唐代懷素草書:“飲水寒猿何處尋,禪僧禿筆矗高墳。草仙三昧傳千古,臥虎騰龍妙入神。”果玲讓洋弟子以化學方法分析不同地點的水。在老和尚看來,不同的水質會影響居民的發音。或許就是俗話說的“一方水土一方人”。
“報國寺日常的飲食樸素簡單,主食白米飯跟白菜,早晨吃開水蛋、稀飯,走山路上金頂寺可以吃到一碗熱騰騰的豆花湯。在報國寺生活的日子,悅然吃慣了中菜,住在樂山的一個好朋友不時送來老婆自制的豆瓣醬,拌著一點醬料,一餐可吃上四五碗白米飯。”面對牛高馬大的“馬洋人”,小和尚始懼后喜。“有空的時候,小和尚們喜歡在水田里摸黃鱔……小和尚們跪在陌上,把手放進渾濁的水里。他們的手真快:一摸到黃鱔就把它抓住放在他們帶來的籃子里頭。摸到五六條黃鱔以后,小和尚們來找我,請我到廚房去叫廟子的大師傅給我炒來吃。”
晚上一起吃飯,果玲和尚喝茶,馬悅然就喝點酒。土匪來了,二十幾個人闖進廟子,門上墻上站著兵,腰里別著槍。這群土匪是跟洪雅縣另一幫匪子干架輸了才進廟子的。馬悅然跟他們坐在一起喝酒,很談得攏。后來,果玲覺得馬悅然每天學習很用功,要是有客人來廟子吃飯,必定請他一道上桌。比如樂山縣長也好寫詩,過一陣子就來報國寺拿詩來給果玲改。果玲請廚房做些可口的素菜,他自己做一道拿手的炒豬肝。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廟里小和尚各自早歇了,方丈房間有一個客室甚寬敞,大家上了煙床,互相點煙,抽鴉片。
果玲師父幽默感很強,他一邊喝酒一邊夸獎他的學生:“你這個人啊,大吃大杯(大慈大悲)。”滿腹經綸的果玲和尚也對外國別樣的生活與飲食感興趣,最好奇的食物是他畢生還不曾吃過的面包。
悅然承諾他要下廚烘焙面包,給老師父嘗嘗正統的西餐。悅然寫信給母親,請求母親回復一則詳細完整的食譜,他自信能夠烤出一缽樸實無華帶點土地香氛氣味的面包。母親很快寫來一則詳盡的家信食譜,盼望他一舉成功。
他也自信滿滿地在廚房大展身手……使用充滿鍋鏟鑊氣十足的炒鍋完成一次面包制作的大創新儀式。果玲老和尚跟當家的常彥法師一起享用“面包宴”,端上桌的“面包”還帶著豐富的湯湯水水,老和尚一勺一勺嘗起來說,“啊,面包是這樣吃的。”
馬悅然所作的方言調查須采集聲音標本,但報國寺沒有電,從香港帶來的磁性鋼絲錄音機只能在成都用。于是,馬悅然帶著在樂山與峨眉挑選的發音助手專程到成都錄制,其中包括果玲,他順便去華西醫院補牙。到了成都,馬悅然把錄音機通上電,啟動開關,那些助手緊張得立刻成了啞巴。果玲在一旁引逗他們說話。當馬悅然最后把聲音播放出來,方言助手大驚失色,說他是耍妖道的洋鬼子。
回到報國寺,一個暗夜,失眠的馬悅然出門溜達,忽然間發現秘密。原是寺外尼庵的尼姑來與果玲的徒弟、報國寺監院常彥幽會。馬悅然抽著煙斗,盡量控制自己搖蕩的心旌,思考著常彥與情人悄聲耳語的感情傳遞方式。琢磨了很久,他終于明白:“嗚呼哀哉!我清清楚楚記得我那天晚上獨坐在報國寺大天井里,很渴望自己有個美麗的情人,證明我關于耳語的聲調學說!”馬悅然終未提及師父的隱私,或許真的不知,或許是“為尊者諱”。大半年后,馬悅然離開報國寺,步行到成都,路上走了五天。這一走再回來,已隔了三十多年。
當時在成都,馬悅然博得了四川姑娘陳寧祖的愛心。1950年馬悅然被迫離開中國,陳寧祖隨之而去。他們一起回到瑞典。馬悅然一輩子就在中國文學的寶山上跋涉,翻譯了部分《詩經》《楚辭》及唐詩宋詞元曲,然后是《水滸傳》《西游記》……上個世紀80年代,當中國的國門再一次打開,他帶著夫人寧祖重訪報國寺。山門前,遇到了當年拉三輪車送他離去的那位車夫。車夫也一眼就認出了他,稱他“是老和尚果玲的徒弟。”可誰都說不出果玲的“究竟”。
再后來,馬悅然將這一段經歷寫成隨筆《另一種鄉愁》。流沙河曾談及讀后感,“小和尚之活潑可愛,果玲法師之儒雅可親,而又排異自守,與乎能海法師在五臺山之拍案示寂,形象個個四棱四現,栩栩如生……其間有大幽默存焉,有大智慧在焉。通觀書中知先生之為人十分溫和,平生絕無壯烈之舉,所以行文平實,無鼓動之腔,無藻飾之辭,卻又別有氣韻,娓娓道來,汾汾可聽,使人悅然久之。”
1996年陳寧祖去世,埋骨異鄉,兩人攜手走過46年光陰。2007年12月3日,馬悅然偕續弦妻子陳文芬再訪成都,參加故友吳一峰 “百年畫展”。筆者與之有過一次訪談。其后,馬悅然重回峨眉山,一到報國寺山門,就半客半主地向隨行介紹,“寺廟門口有一棵很大的黃桷樹。曾經是一排水池,我們在這兒洗東西。”他的目光落在消失了的水池里,低聲說:“寺里有一個果玲大師,他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可以背誦《左傳》,他教我接觸和賞析中國古代詩詞,我從此開始對中國早期的詩歌感興趣。”83歲的馬悅然有足夠的判斷力,也不再會為尊者諱。他走進客房部10號房間,掃視一周,“這就是我當年住過的屋子,以前這些窗子都是用紙糊著的。外面還有一個桌子。我喜歡一個人坐在桌子邊喝酒,喝的五加皮,那味道真好!”當年在寺里住了7個多月,房費和餐費總共才25元。他還去拜訪報國寺一位90多歲的老和尚,想打探師父果玲的下落,但“白茫茫大地真干凈”。馬悅然成都行最可慰藉者,是托人在四川省圖書館善本部復印了一本1938年出版的《果玲詩鈔》。那印跡模糊的復印本,在馬悅然的藏書室中,定會有不尋常的位置。
山色溪聲更好詩
“未成經律未成禪,狂掛名單七十年。”果玲已等不到那一天。不久,五十六歲的果玲遇到政權易幟的暴風驟雨。

1950年以后的出版物,抹去了果玲的痕跡。1980年代起,地方志與地方政協文史資料偶有提及,卻大都說他附庸風雅,欺世盜名。如趙熙所題:“老來問法到南能,家國蒼涼感廢興。獨向月明彈綠綺,峨眉山下一詩僧。”有人在《郭沫若峨眉三日記》一文中寫,民國二十八年(1939)郭氏游報國寺,見到此詩刻匾,笑道:“峨眉山下一詩僧,詩僧未必是果玲?”有人在《于右任書聯諷果玲》一文中寫,民國二十四年(1935)夏,于右任在報國寺見到此詩,即寫了副對聯諷喻:“立身苦被浮名累,涉世無如本色難”贈予果玲。而據趙熙之公子趙元凱訴,此詩乃作者寄贈報國寺住持果玲之作。再說,趙熙詩贈果玲的詩作又何止一二?
果玲到底是攀龍附鳳,胸無點墨,還是腹有詩書,下筆成誦?且聽前賢說。
謝無量《題贈果玲》:
趙州言語示生路,臨濟宗風只活埋。
百草千花相藉死,冰盆才見水仙開。
馬一浮《和果玲詩》:
僧俗仙凡一例癡,星云燈幻吾方知。
游人更笑題新句,山色溪聲更好詩。
商衍鎏《贈報國寺果玲上人》:
詩心宛似禪心細,水月空明貯一囊。
萬壑松風千嶂遠,峨眉秀采贊公房。
何魯《題贈果玲》:
曾自峨眉絕頂回,千泉萬壑走奔雷。
惟余一事此惆悵,不見驚鴻照影來。
題贈者,還有袁煥仙《和峨眉山報國寺果玲能登韻》,程潛《宿報國寺訓果玲上人》,饒宗頤《薄暮下山,至報國寺遇果玲上人》等。
或曰,上例多為名人酬酢應景。詩人衡裁,但憑作品。果玲詩作大多與時俱廢。筆者采擷僅限《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近代巴蜀詩鈔》等選本,及趙熙、林思進、龐俊、向楚、曹經沅等人詩集附錄,而管中窺豹,聊勝于無。
病不開堂道益尊,偷閑卻憶長公論。
小園花草親身種,丈室詩書任意溫。
間答名流九州信,偶招將士八年魂。
時平又值秋登日。喜見郊原樂滿村。
未成經律未成禪,枉掛名山二十年。
憶得云從風虎會,曾參鬼泣魔神篇。
拈花妙唱空中假,臨水機鋒始頓圓。
悟澈乘除消長義,觀心記取早忘簽。
花盈小院稷盈疇,瓜熟芋香大好秋。
賸有林泉棲野鶴,了無風雨遇閑鷗。
經行聊讖前生業,寺事全交后起籌。
敢道安禪空毀譽,惟將晚景讬君侯。
頻年蛇蟄欲存身,漫說修持凈六鏖。
細雨空庭吟落木,清風小院自披榛。
多承蓮幕諸賢護,小別蒲團一段因。
久懷岸堆林秀戒,閉關仍禱裕斯民。
山居遣懷
三載峨眉獨嘯吟,閉門古寺又春深。
異鄉花草故鄉淚,出世風裁救世心。
偶逐云霞過別岫,閑邀鷗鷺到空林。
敢云來去無牽掛,落絮游絲每撲襟。
夜過黃岡赤壁 七言絕句 押蕭韻
東坡居士客無聊,前后賦成與世超。
冒月乘輪過赤壁,怕公把我當參寥。
七夕感舊 七言絕句 押鹽韻
袈裟半袒坐層檐,仰看星橋香懶添。
猛憶那年今夜月,如花人對讀楞嚴。
其二 七言絕句 押微韻
寶馬香車愿已違,生天成佛事還非。
遙憐此夜空閨月,獨拜雙星望我歸。
題曼殊小說集 七言絕句 押元韻
一集遺編未細論,袈裟我亦滿啼痕。
可憐山寺枕經客,禪榻雙依倩女魂。
次韻奉懷小魯先生新疆并呈纕公
天山非復舊邊疆,應向城西卜草堂。
簾幕高風推杜陸,棠陰政事讬龔黃。
未因簿領妨詩筆,可有鶯花慰客觴。
莫道參寥真懶散,屢將佳況詢歐陽。
狀寫風物,果玲有《七律 山房落成感紀長句 押青韻》,詩曰:
月榭云廊幸落成,半年辛苦在松扃。
引來白水分三處,收得青山會一亭。
料量工人同曉雨,唱酬詞客數春星。
禪身未到菩提岸,兩字虛名誤果玲。
報國寺西北五里左右的龍門洞,是與清音閣并舉的峨山“水勝雙絕”。果玲《侍麗丈游龍洞》,詩云:
若問龍門景,詩人七度來。
瀑布飛項背,奇石熟風栽。
乘筏探幽洞,撫藜望削崖。
臨流不忍去,相與重徘徊。
峨山風景,處處留有果玲所撰楹聯:
半溪流水響;滿院朱蘭香。(伏虎寺)
河間狂客來歌鳳;海內才人起臥龍。(神水閣)
投起針來,果能羅什譯經寸金易化;
吃了飯去,不學彌勒大肚滴水難消。(題清音閣)
雙橋有水隨高下;九老無形自古今。(清音閣)
觀云幻宇宙;看月帶星球。(仙峰寺)
偶共詞人登絕頂;且邀明月上層樓。(洗象池)
舉頭便近峨眉月;濯足非遙大渡河。(金頂)
倘若,峨眉山全然抹去果玲的文字,能不“稍遜風騷”?1939年,詞人盧冀野曾檢閱《抗戰以來之中國詩歌》,他寫道:
作者便想到幾位僧侶(不但是佛教徒,而且是受過戒的和尚),他們在戰時也寫著慷慨激昂的詩句。第一,要數太虛法師。這個名字是最熟悉的,他寫詩愛詩,尤愛寫六言的絕句詩,他的詩很像佛偈,不過用作抗戰的贊頌,內容與佛教的經典迥然不同罷了。此外,有果玲,和融海兩法師,也是太虛的同調。果玲駐峨眉山,報國寺。這“報國寺”是多么耐人尋味的名稱!每一枝詩人的筆,的確正在還他們報國的心愿!
有一非常時期,既“因言廢人”,也“因人廢言”,于是人言皆誤。抬望眼,黃蘆白茅,一片蕭瑟,令人浩嘆。檢點果玲與峨眉,既“因地傳人”,也“因人傳地”。縱他大節有虧,小節有失,回眸詩壇,寧缺果玲乎?